女性主义文艺批评思潮的出现,与当下一个重要的时代潜流密切相关:话语被认为具有维护和强化现实的强大力量,这会伤害到在现实中处于下风的弱势群体,而我们对这种伤害正在变得越来越敏感。

《漫长的季节》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从五一假期开始,相当一部分国内观众的注意力被《漫长的季节》牢牢吸引。在豆瓣上,这部从1997年、1998年和2016年三条时间线出发讲述东北往事的网剧在收官时评分高达9.4,这意味着它已进入“神剧”行列。
然而在最初的一边倒好评后,舆论场中出现了“#漫长的季节爹味#”的批评声音。批评者认为,《漫长的季节》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不够充分且存在诸多刻板印象,在浓墨重彩地渲染男性主角们的伤痛和友谊的同时,让女性角色的伤痛隐没于故事的背景,用“女性互害”取代女性联结,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剧情发展逻辑。

性别视角正在成为许多中国观众的文艺作品鉴赏工具。在《漫长的季节》之前,今年春节档的三部热门影片《满江红》《流浪地球2》《无名》都曾面临女性角色刻画乏力的质疑。女性主义文艺批评思潮的出现,与当下一个重要的时代潜流密切相关:话语被认为具有维护和强化现实的强大力量,这会伤害到在现实中处于下风的弱势群体,而我们对这种伤害正在变得越来越敏感。
《漫长的季节》“爹味”批评的核心观点是女性角色主体性的模糊与刻画的他者化,它背后的重要主张是对“不平等”的敏感——90年代东北下岗潮的时代灰尘平等地落在了每一个人头上,但剧情视角顺滑地代入了男性命运,让观众得以最大程度地与男性角色共情,与之相对的是女性视角的匮乏和观众与剧中女性角色的疏离。
这种对不平等的高度敏感虽然激起了不少剧粉的反感,但它已毋庸置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心理特质。在《敏感与自我》一书中,德国《哲学杂志》主编斯文娅·弗拉斯珀勒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人类文明进程伴随着人们“对自我日益增强的惩戒和敏感化”。而要理解平等与不平等对我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追溯人类的进化史。

人类发展经历了三种社会组织形式,即人类出现以前的优势等级(这是在动物世界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处于支配地位的一个雄性位于最高层,决定社群中稀缺资源的分配)、史前时代奉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以及等级制度分明的农业与工业社会。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收入不平等》中指出,在人类出现的20万-25万年间,人类社会在95%的时间里一直奉行平等主义。诸多人类学研究揭示了狩猎采集社会存在“反支配策略”,每当族群中有强能力者试图掌握支配权,其他成员就会联合起来反抗,捍卫独立自主。不平等的加剧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更确切而言,是种植谷物后逐渐出现的税收制度所导致的结果。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对不同社会环境的灵活适应性:
“在进化史中,人类曾经遇到各种极端的社会环境,一端是推崇‘强权即真理’的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另一端是充满关爱、分享互助的社会。我们并没有一劳永逸的适应某一种环境,相反,表达遗传与进化出来的心理让我们同时具备了两种人性,可以根据所处社会系统的需要被触发。”
这两种人性的一种事关不平等,强调竞争和超越,另一种事关平等,强调协作、同情心和相互信赖。它们构成了人类动机和行为的两股重要推动力量,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特别是一个人的尊严是否及能否得到尊重。按照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这两种人性也可被称为“优越激情”和“平等激情”。

“优越激情”是民主时代以前等级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根基,“平等激情”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社会出现的强劲动力。进入近代,平等主义开始占上风,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在书中援引人类学研究的观点指出,狩猎采集社会所采用的那种反对支配、维持平等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历史先声,“人们反抗独裁,努力建设法治社会,寻求一种足以让自身免受暴君和独裁统治迫害的民主体制。”
社会转型与人类情感结构的变化相辅相成。弗拉斯珀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越来越大,人口密度越来越高,人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环境里,自我控制带来的敏感性因此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润滑剂。至18世纪,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提出,敏感性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
弗拉斯珀勒将18世纪称为“共情的世纪”。她援引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在《发明人权》一书中的发现指出,18世纪中叶,以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Clarissa)为代表的书信体小说广为流行,西方人被这种以第一视角讲述的故事所蕴含的真挚、直接的情感世界所深深打动。书信体小说培养了人们与陌生人的命运共情的能力,在书信体小说的鼎盛时期之后,美国和法国分别于1776年和1789年将“人人平等”写入法律,并非巧合。弗拉斯珀勒认为,在“敏感性文学”(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的大力推动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新感觉方式,成为人类文明前进的重要推手。与敏感性文学交相辉映的是,共情成为18世纪哲学家关注的重要话题,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到卢梭,都对此有长篇累牍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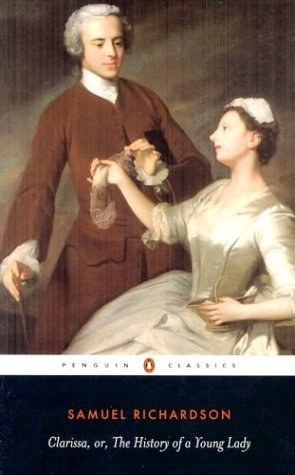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欧洲人对文明线性发展无限信心,同时也在心理学领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对暴力的感知从“计数”转向了“讲述”,受害者不再仅仅是那些丧失生命的人,也指那些幸存下来、但身体或心理遭受严重创伤的人,受害者对其体验、震撼和梦想的讲述越来越成为“受害者”的本质(这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重要出发点)。
20世纪70-80年代后,学界又出现一种把“创伤”概念的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外部环境上的趋势。受越南战争的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出现,而人们对“创伤”的理解越来越主观化——能够触发创伤的诱因不断延展,大到战争、近亲死亡,小至电影、小说或一个词语,几乎任何东西都能使人产生创伤。这也导致了“(创伤)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的说法如今在社交网络上非常常见。历史学家斯文娅·戈尔特曼认为,这一趋势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受害者的确得到了发声的权利,他们的痛苦在舆论场中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分辨怎样的人才算是受害者。

时至今日,言说和揭露创伤已成为弱势群体抗议结构性歧视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手段,全球反性骚扰运动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做法的强大力量——受害者公开言说自己的痛苦,可以使之成为共同的、公认的痛苦,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弗拉斯珀勒提醒我们注意,对弱者之痛苦的高度敏感,实际上源自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之承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落差,“正因为社会越来越平等,敏感性反而越来越被点燃。”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仅从经济维度去理解平等。福山认为,如果说20世纪的政治格局由经济议题界定左右光谱分布,那么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光谱更多是由身份界定的,与物质自利同样重要的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对自身尊严得到公开承认有了强烈的渴求。在他看来,这是当下身份政治的核心。
文艺作品开始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战场,在文艺作品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对此越来越敏感,他们开始要求被承认,被更完整、更立体的呈现,否则就视之为对其的伤害。在梳理敏感性进程时,弗拉斯珀勒指出,学界的“语言学转向”是当今的这种语言敏感性的一股推动力量。语言学转向涉及一些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理论假设,“语言符号具有现实效果,即语言不单指向现实,还创造着现实。”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符号(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语言结构主要由成对的对立构成,比如“男人”与“女人”、“黑”与“白”、“上”与“下”。其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消解和重新思考语言的固定结构,他认为意义可以通过对符号的别样使用而变迁。
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将德达的符号解构理论革命性地应用于性别问题,她在《性别麻烦》中开创性地提出,“男人”和“女人”只要始终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出现,就会固定人们对性别的认知,性别因此不是“自然”的,而是“行事的”(performative)。弗拉斯珀勒分析称,如果身份是由语言塑造的,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语言也可以破坏身份,或者从一开始就否认一些群体的身份,并在实际上剥夺他们的生存权。语言敏感性的出发点因此在于,如果语言在我们对世界、对自我的感知中发挥如此根本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改变语言——从措辞到叙事方式,让边缘化群体(比如女性)被看到、被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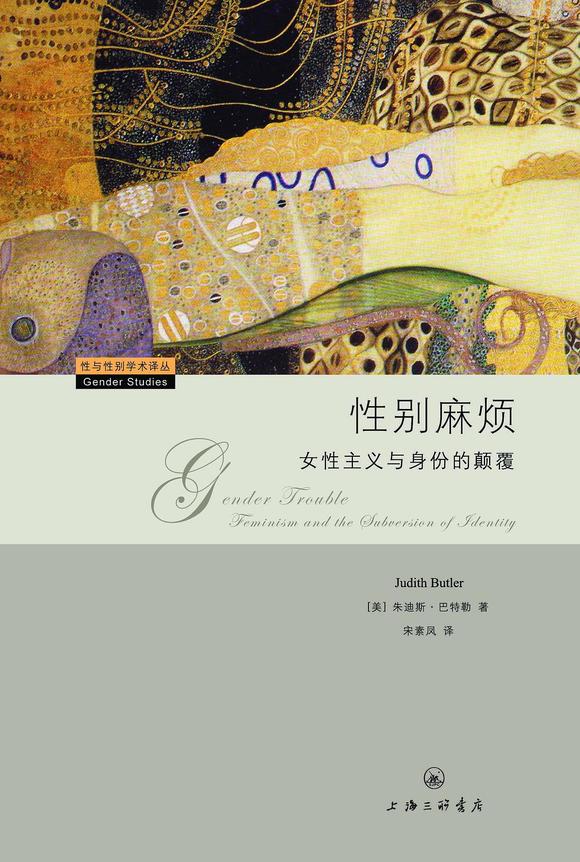
以上构成了女性主义文艺批评思潮的智识背景。用弗拉斯珀勒的话来讲,如今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普遍提倡共情,提倡用回撤代替对峙,用敏感代替坚硬,用理解代替隔阂。”然而她认为,共情是有局限性的。
这种局限性既表现在他人经验主观性的不可及——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去采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人——又表现在过度共情会有丧失视角的危险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求在一个叙事中面面俱到地顾及到所有人的经验、立场与感受,这个叙事可能就不再对事物有任何自身的看法。她援引弗里茨·布莱特豪普特在《共情的阴暗面》中的观点指出,“人的客观化”会导致“人的稀释”,导致一种自我否定,“(客观的人的)身份其实是‘没有身份’,这种人通过失去或搁置自我而变得有能力去共情。”
在女性主义的范畴内,共情涉及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立场理论”。根据立场理论,由于男性在父权制社会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想法是片面和反常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在被压迫的处境中,反而能对世界的某些领域发展出更客观和深刻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一直在激辩的论点。
弗拉斯珀勒认为,敏感性的提高固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它并不天然等同于进步性,把敏感性美化和绝对化会使其成为退步性。这是因为,当我们过度强调敏感性时,我们给避免立场冲突造成的伤害(比如避免文艺作品中的男性视角对女性受众的伤害)赋予了过高的价值,有滑向一种以邻为壑、“我们VS他们”的身份政治的危险——我们不再相信不同的群体有跨越彼此的差异,发现共同点的可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立场冲突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是有益的。如弗拉斯珀勒所注意到的,建设性的对话建立在“你”和“我”视角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共情和挑战的交锋的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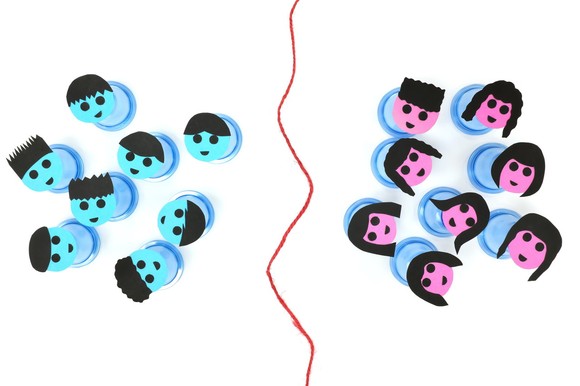
在弗拉斯珀勒看来,18世纪至今,敏感性已被赋予了太多价值,是时候重提以尼采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思想脉络了——韧性产生于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伤痛,人能够“从伤口中产生力量”:
“(敏感的自我)期待着来自世界的各种保护,却不期待自主地去做什么,必须有针对性的加强韧性,这对于人们行使自主权至关重要……韧性(反抗力量)寓于艺术中,寓于人类的创造欲望中;韧性寓于语言泛指的失败中;韧性寓于文明进程本身蕴含的古老的史前史中;韧性寓于每个人的脆弱性中,它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宝藏。韧性不是敏感性的敌人,而是敏感性的姐妹。它们只能一起掌握未来。”
参考资料:
【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敏感与自我》.上海三联书店.2023.
【英】理查德·威尔金森,凯特·皮克特.《收入不平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中译出版社.2021.
《逆风吐槽<漫长的季节>,这漫长的爹味》,萝严肃
https://mp.weixin.qq.com/s/KclGJlc_4duHyyKEd-L2HQ
《编辑部聊天室 | 电影中有令人不适的部分,就不值一看了吗?》,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