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关键词:九零后作家、现实主义小说、刚果女性、清朝的法律与性、20世纪观念史、向京、观鸟、宇宙的起源……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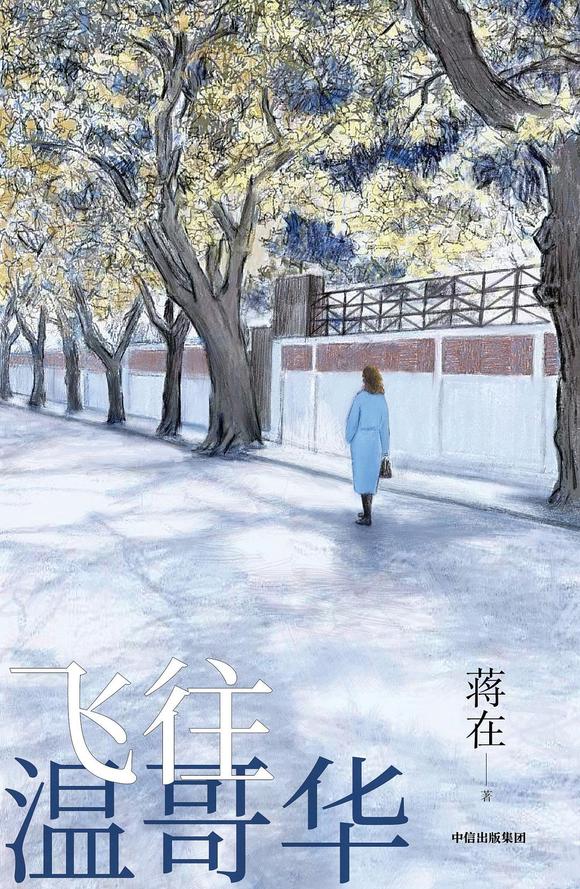
蒋在是九零后,但是根据《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说法,她的小说里“活着经典文学的趣味和传统”,这一传统来自西方的契诃夫、莎士比亚以及乔叟,印证着这名年轻作家的“老灵魂”,以及她长年生活在异国的全球经验。
《飞往温哥华》是蒋在的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故事多有一种属于成年人的悲剧特性,充满了贫穷、自私的爱、死亡这样的无可奈何又触目惊心之物。比如同名作讲述了一对早年离异的中年父母,为了陪伴患有抑郁症的儿子而来到加拿大;另一篇则写涂口红、翘着兰花指的男孩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强硬地生活着。正如作家张莉对蒋在小说调性的评价,是“冷静、峭拔的语言之下流动着属于青年人的柔软体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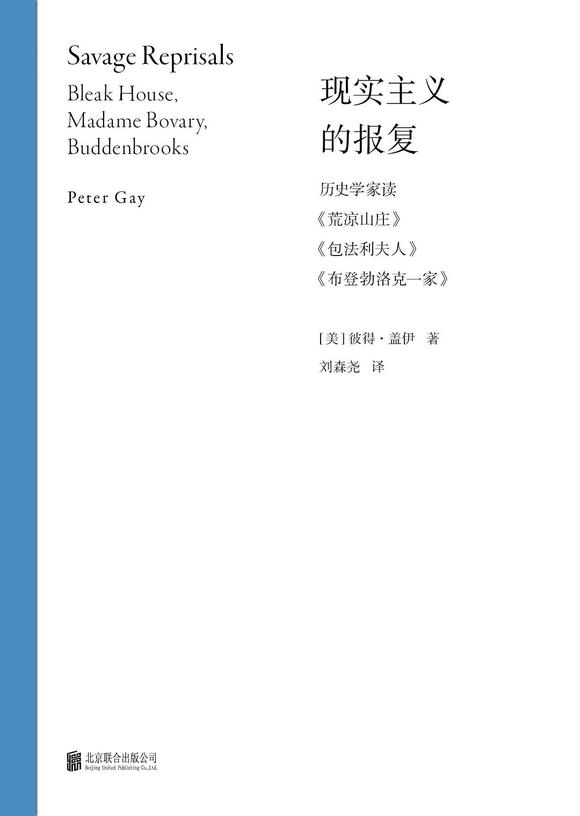
现实主义小说呈现的是真实吗?又或者像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所谓的历史也是一种虚构呢?在《现实主义的报复》中,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化身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穿梭于文学、历史和作家传记之间,探讨小说如何成为“对世界举起的一面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并不如实地反映现实,而是“扭曲的”、带有作家本人自身立场的局限性。
盖伊发现,1850-1910年的三部里程碑式的小说《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虽然都可以被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却都隐藏着作家深刻的报复心理——狄更斯被一场失败的诉讼所激怒,于是在作品中讽刺了英国法院系统的愚蠢;托马斯·曼通过抨击资本主义,对他富有的父亲进行了复仇;福楼拜对笔下的女主人公既厌恶又同情,那句顿悟般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则饱含着他对平庸的中产阶级的痛恨。盖伊认为,小说并不等同于历史,但如果研究者采取的方法得当,小说也可以成为发现历史真相的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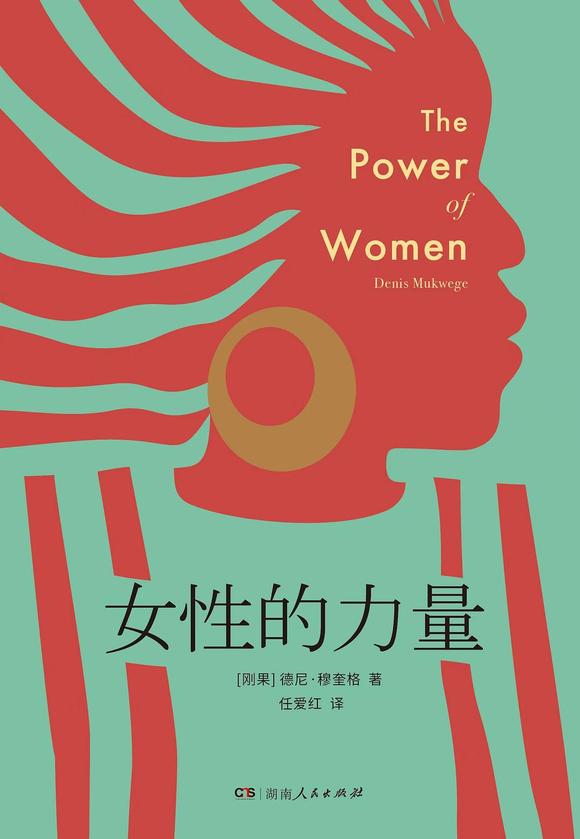
在刚果,每年有40万女性遭到性侵,骇人的数字背后是这个国家长年累月的战乱、腐败的政府与极度不平衡的社会结构。妇产科医生德尼·穆奎格从小就意识到了当地妇女面临的危险。1999年,他创办了潘齐医院并收治了一个被卢旺达士兵轮奸的女性,在此后20年间,穆奎格成功救治过5万多名女性,被大家赞誉为“奇迹医生”,并于201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入选《时代》杂志“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本书经由穆奎格之口讲述了这些女性的故事,她们如何在极端暴力后艰难存活、出于被污名化的恐惧而隐瞒病情,顽强的意志力又如何刺破了虚伪的男性气概面具。正是这种女性的力量支撑着穆奎格走过两次刚果战争,甚至是多次遭暗杀的危机。穆奎格在书中提醒我们,虽然刚果的厌女情况非常极端,但性暴力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打破沉默才格外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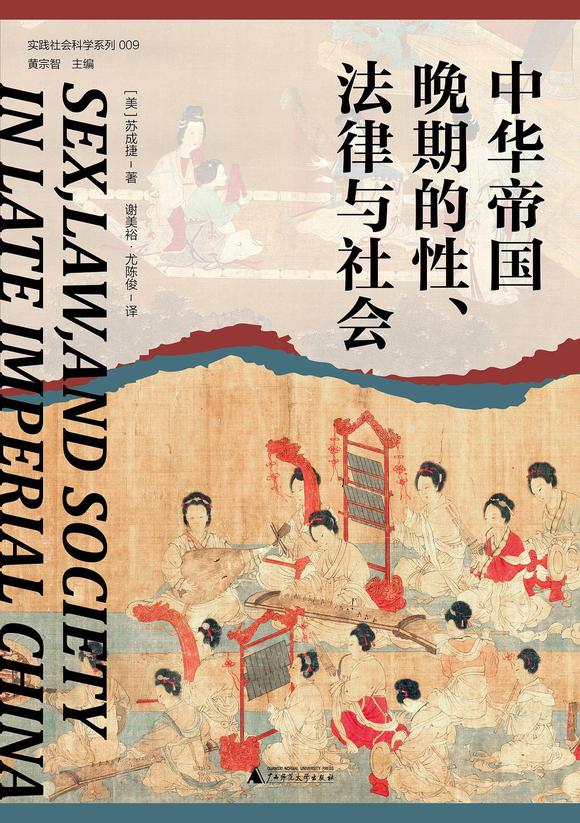
提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人们不免会联想到清朝对于性行为的压抑和严苛管控,而在本书中,历史学家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跨越了性别史、法律史和社会史三个领域,用详细的史料反驳了这种简化的观点,并用比较史的眼光分析了性行为管制、寡妇守贞、同性恋法律与卖娼等问题,也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妇女歧视等现象。
这部法律史的经典作品初版于2000年,影响过数代关注性别研究的学人。它的目标首先是实证性的,即厘清明清时期对性的立法,但除此之外,苏成捷也希望将其放置于宽阔的社会情境中审视,比如种种规制如何与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和实践发生关联。这既要求作者理解法律史文献、民事诉讼档案中的真实案例,乃至《金瓶梅》《牡丹亭》等文学作品,也需要作者具有剪裁史料的能力。正如《闺塾师》的作者、历史学家高彦颐评价的那样,苏成捷巧妙地拥抱了“语言转向”这一趋势,使得他在处理那些难以捉摸的“性”话题时拥有了关键性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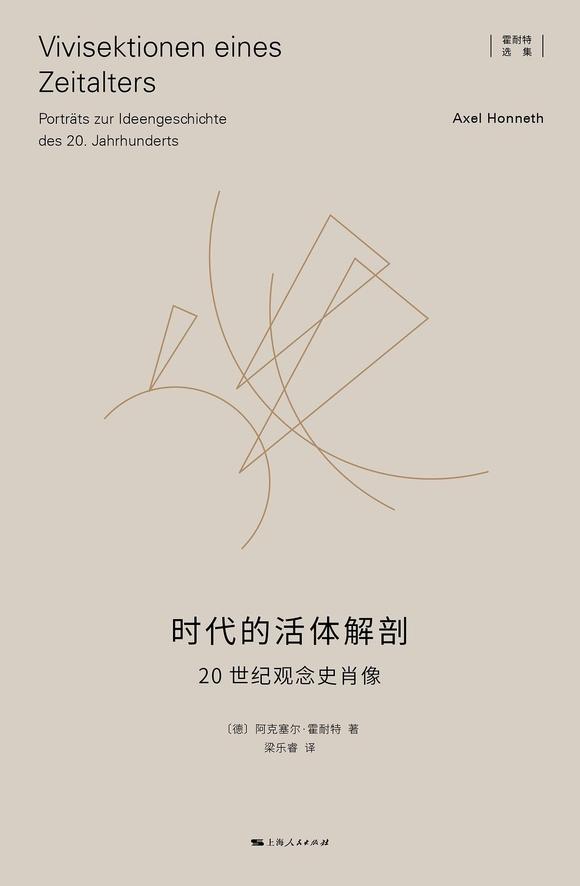
阿克塞尔·霍耐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重要理论家,也是哈贝马斯教席的继任者,本书是其尝试为20世纪观念史进行诠释的著作。在霍耐特看来,我们有必要将这一观念史看成是“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然而,为其做出贡献的诸多学者的言说却被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把它们翻找出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批判性的正义理论体系,便是标题“活体解剖”的含义。
在书中,霍耐特剖析并总结了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奥雷尔·科尔奈、罗宾·科林伍德等20世纪学者的学术贡献,认为他们都脱离了乌托邦式的渴望,试图为时代面临的难题提供诊断与答案。本书也是“霍耐特选集”中的一本,该合集选取了作家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出版时获得了霍耐特本人的支持,他亲自撰写了2万余字的总序,为国内读者详细介绍了他的学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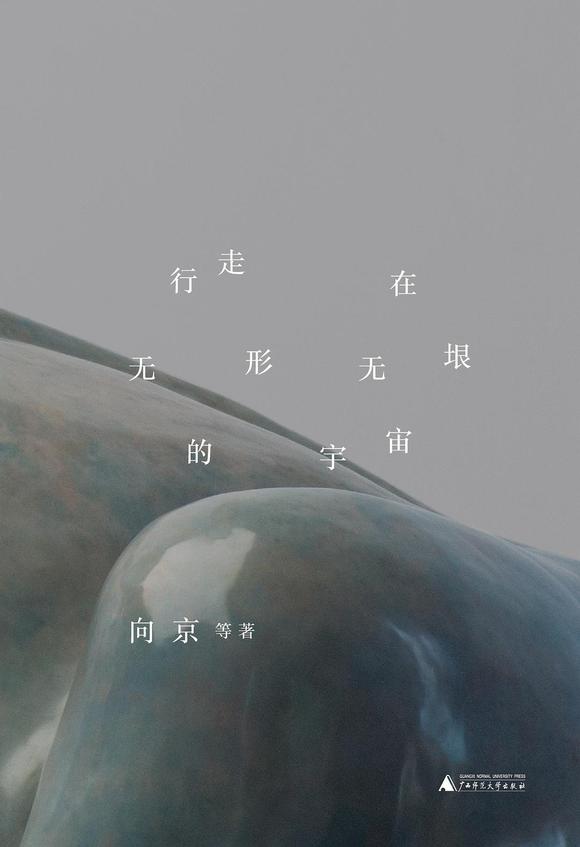
“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是德国学者阿克曼对当代艺术家境况的描述:不再有上帝的帮助,也失去了审美系统的支持,艺术家们只能依靠自己。在这部访谈集中,当代女性艺术家向京邀请了戴锦华、陈嘉映、林白、朱朱、阿克曼等各领域学者,并且打乱访谈的顺序,模拟出了类似的无垠宇宙。
出生于1968年的向京在访谈中坦言,她经历过众多精彩的时代,但今天这个时代带来的冲击格外剧烈。以往的她倾向于站在灵肉二元的立场上,用雕塑来验证自己形而上的思考,疫情成为了促使向京转变的导火索,2019年她彻底结束了雕塑的创作。在这些谈话中,向京想要理清的正是自己长久以来的那些困惑:是否存在一种女性主义的创作?观念艺术就一定是进步的吗?为什么不能用“过时的”语言去回应所谓“当代的”问题呢?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得到许多关乎传统、当代、女性、艺术以及社会思潮等话题的真知灼见。

在波兰俗语中,“抓住两只喜鹊的尾巴”比喻同时做很多件事,想要一箭双雕。那么“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又是什么意思呢?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自幼喜欢观鸟,足迹遍布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多瑙河三角洲,这本书是他在旅途中写下的12个与鸟相伴的故事:照护迁徙的迷鸟,去乡间寻访白鹳,在城市公园里聆听布氏苇莺的鸣唱……作者还将对鸟类的近距离观察和历史文化结合,试图找寻文艺作品中鸟的身影,在书的结尾介绍了渡渡鸟等灭绝或濒危鸟类,或者讲起“笼中鸟”的典故:二战时身陷囹圄的英国军官无事可做,却执着于观察红尾鸲。以其温柔的自然关怀视角,本书获得了波兰最负盛名的文学奖“尼刻奖”,中译本直译自波兰语最新修订本。

宇宙诞生于上帝不小心打的喷嚏,还是造物主苦心孤诣设计的结果?又或者它的起源只是从“无为”和“无序”的规则中得来的?道家子弟可能会同意这个观点,本书的作者、英国化学家与科普作家彼得·阿特金斯也这样想。
阿特金斯以著作《重临创世》(Creation Revisited)奠定了其在科普写作领域的地位,在本书中继续聚焦于他最关注的那个问题:宇宙究竟从何而来?他曾在早期著作中就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起源做出解释,本书则转向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宇宙的运行规则。读者将会读到力学、热力学、电磁学乃至基本常数的起源,以及数学揭示现实深层结构的可能。虽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人类仍然无法完全理解自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宇宙的起源非常简单,一切根本没有那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