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和女性,雇主和员工、富人和穷人、官僚和平民,结构性的不平等如格雷伯所说,一直在产生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真正相信“人人平等”这一现代价值观的人,应当在上述每一个不平等结构中都逻辑统一。

编剧史航。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83期主持人 | 尹清露
4月23日,出版品牌“一页folio”创始人范新被曝性侵未遂。28日,豆瓣用户“青年编辑们”发出投稿,一名女孩指控编剧史航曾对其进行言语和肢体性骚扰。此消息在微博上广泛传播后,另有多名女性相继站出来讲述了被史航性骚扰的经历。截至昨日,已经有26名女性以不同形式表明自己曾遭史航性骚扰,时间跨度从十几年前到近几个月不等。在同一时间段内,青年作者宗城、南京先锋书店“陈总”等人也相继被不同女性指控性骚扰。
本次的性骚扰事件不断发酵,史航试图以聊天记录截图证明这是男女双方的“你情我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女性正鼓起勇气站出来讲述自身遭遇。史航性骚扰事件当事人之一小默5月3日发出的文章就是力证,她具体而有力地回忆了自己受到侵害的事实、过程与感受。
在社交网络上,包括文化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女性有感而发,分享了自己曾被拉入某圈子或饭局,为了不使前途受阻而只能假意陪笑或被揩油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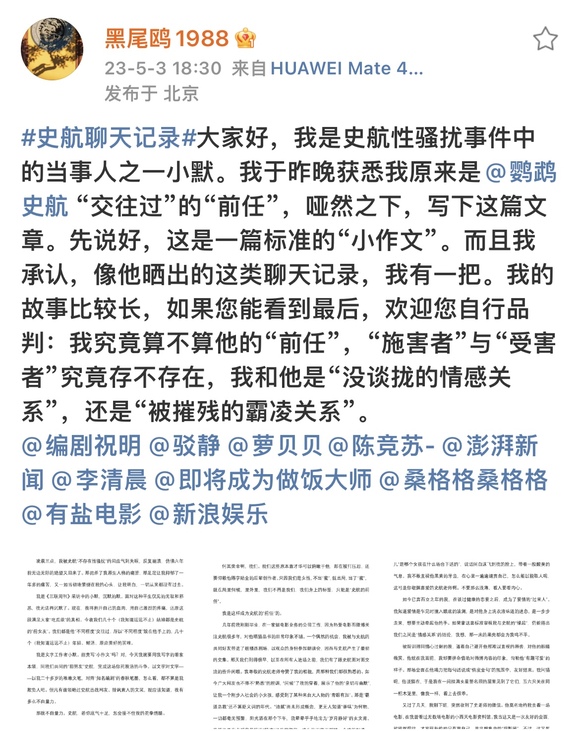
需要警惕的是,施害者这套“你情我愿”的说辞仍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许多深陷困境的女性要突破重重迷雾,才能厘清骚扰与控制并非所谓“你情我愿”。而这些占据文艺舆论场高位的男性在身体实施侵犯的同时,也会利用“文艺”的巧言令色对女性的自我实施围剿。此前编辑部聊天室聊到“疯男人”主题时曾提到,一些男性往往会用知识权威,以及经过扭曲的话语来掩盖不齿的行为,比如史航在事后辩解称这只是与相识女性的“门内的情调”。
在今年引进国内的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自传性小说《同意》中,五十多岁的法国著名男作家G给女学生们写热情洋溢的情书,认为“这爱情如同爱洛伊丝与阿伯拉尔的一样圣洁”,而斯普林格拉则“感到自己有义务报以同样的热情”。G把自己加害未成年女性的事实包装成言辞正义的畅销书,再次加固了这套男性叙事的流通,在剥夺了女孩身体之后再次剥夺了叙事的权利。
在本期聊天室里,我们聊到了自己直接或间接遇到的文化圈性骚扰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董子琪:文艺圈的饭局有时候挺难捱的,而且从采访到饭局的切换也很不自然,就好像就在刚才大家还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到酒桌上,就迅速划分成了男与女、吃客和食物两个阵营。我甚至能从劝酒这件事上感受到针对和敌意,哪怕是以“敬美女”的名义(那时候你没有名字,只是美女,大美女、小美女、资深美女),也会重新划分敌我。凡是劝我多喝酒的,基本是那个阵营的;不劝我喝酒、默默吃菜的,可能还算是伙伴。
又想起上次王安忆和余华对谈当中的一个小细节。王安忆说,当年大家在青年时期志同道合地走在了一起,因为都喜欢聊文学,但后来这些聚会的场合她就参与得很少,因为作为女性需要忍受许多黄段子。这段话我没有收到稿子里去,因为和整个怀旧、颂扬文学往昔的气氛不符。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就算是王安忆,这位连余华见到都要喊前辈的作家,在聚会里都只能充当黄段子的听众吗?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对一位著名作家的采访。记得当时我反问他一个问题,大概是他说人生有很多选择,真的如此吗?他回答说,那你也可以不做记者,去做洗头妹啊,为什么不呢? 中间他还对我打比方说,如果不是在这里相遇,而是在酒吧,我们就是单纯的男和女,我可以撩你,你可以不理。我知道这只是比方,但这种界限模糊的比方难道不是充满恶意的?
潘文捷:我采访过事先就知道有过性骚扰行为的男性。其中一位是前老板(男)的朋友,某领域的大佬。办公室对这事人尽皆知,所以让我和同事结伴前往。然而对老板来说,哪怕发生了这类事情,他还是重要的人脉,还是会对他以礼相待,还是会要求我们去采访。
我的朋友中常常有性骚扰行为的受害者,但我也在想,万一什么时候,我的朋友性骚扰了其他人,我会是什么举措呢?如果对方是多年好友,甚至我们之间有过利益交换,这时候会如何应对呢?在这次事件中,范新、史航的友人纷纷出来为他们发声,甚至宗城也能张口说让一些合作过的编辑来证明他的清白。直到站出来举证的女性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惊人,那些说辞才显得格外可笑。
但也并非只有国内如此。去年,3名女学生控诉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人类学教授约翰·科马罗夫性骚扰,之后,哈佛大学并没有开除他,而是禁止他在下一学年教授必修课程。即便如此,还是有38名教授公开签名表示对约翰·科马罗夫的支持,理由是:“我们签名人知道约翰·科马洛夫是一位优秀的同事、顾问和忠诚的大学公民,他在过去的5年里为数百名博士提供了培训和建议,包括不同背景的学生,他们随后成为世界各地大学的领导者……我们对哈佛对他的制裁感到沮丧,并担心它会影响我们为自己的学生提供建议的能力。”
可是,一个人是不是优秀的同事、朋友,在职场上有多大的能力,和他有没有性骚扰别人完全是两码事。范新、史航、宗城等人与朋友们的交情很好,又如何能说明他们对待下属、对待女性也是一样呢?

尹清露:很能理解这个困惑。我记得某位男性朋友曾经在被指控职场性骚扰以后,希望我能理解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希望我能说出“这是女性给别人泼脏水的常用手段”,我说不出这种话,想必他觉得我很冷漠。我觉得,在男女对性骚扰的心理经验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虽然不一定要对朋友“割席”,但至少要承认这件事上他就是做错了,是无法原谅的,这难道不正是尊重朋友的态度吗?因为我尊重你,所以你要对做过的事负责啊。
潘文捷:如果文化领域有更多的女性领导、女性KOL,事情大概会好很多。然而,在2018年,纽约大学女性主义学者、66岁女性教授罗内尔被指控性骚扰自己的学生。之后,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51位学者签署了递交给纽约大学行政部门的“背书”联名信,支持罗内尔,签署“背书”信的许多学者自己毕生都在批判权力结构。
虽然朱迪斯·巴特勒在之后进行了道歉,但我们又要如何理解他们当时的举动?任何人站在权力高位的时候,都有滥用权力的风险。当真正的批判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中、用在自己和朋友身上,又是如此之艰难。
林子人:这一轮性骚扰事件曝光后,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她说,他说”的舆论撕裂。虽然失望于性别意识提升似乎是(年轻)女性在大踏步前进、而许多男性依然席地而坐无动于衷的现状,但我也并不意外。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思考官僚制的“结构性暴力”本质时从女性主义理论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发现,当女性开始向工作、举止或着装方面的“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时,性侵犯的发生率急剧攀升。暴力的重要性在于,“它或许是唯一一种即便没有沟通也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形式。”大多数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不断付出努力维系,需要沟通、理解和妥协,但暴力可以跳过这一切复杂程序,直接为某种人际关系定性。
性骚扰就是一种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按照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观点,性骚扰的真正含义是,把女性从职业、主体性、智识水平这些原本构成一个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的因素中剥离开,降低还原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属性,向她们宣称“你终归只是一个女人”。通过这种男性权力的夸耀,加害者得到作为男人的身份确认。上野甚至认为,男人对女人说“你好漂亮”也是性骚扰,因为这亦是一种男性掌握压倒优势的社会性别实践——对女性的性价值进行估价。这样的“称赞之语”表面上看是对女人的恭维,但其实依然是在确认男性的优势性别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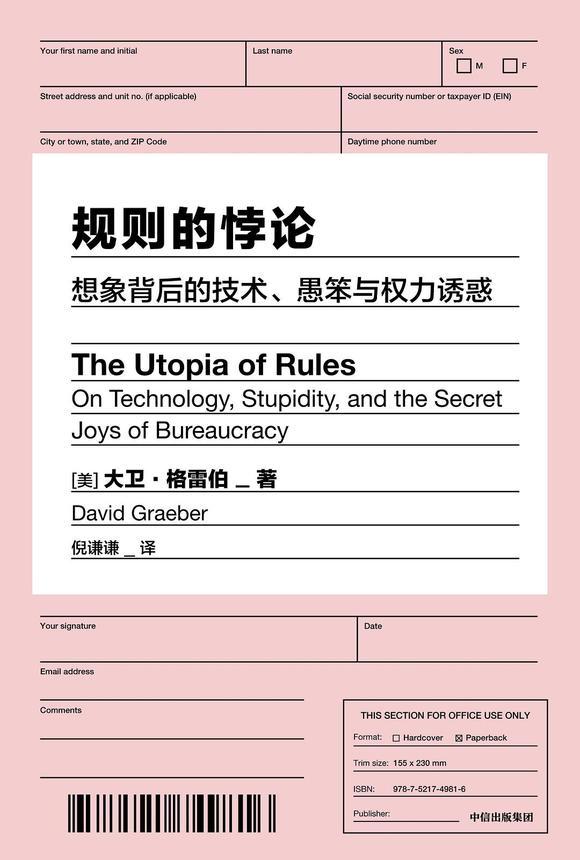
格雷伯指出,结构性暴力情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认同结构。在性别问题的语境下,这种一边倒的想象性认同的方向是女性对男性:
“无论身处何地,女人总是被期待去不停地想象如何从男性视角看待这样或那样的情境。可社会几乎从不期待男人为女人做同样的事。这种行为模式的内化程度之深,导致许多男人很抗拒换位思考的提议,仿佛提议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
男性或许真的很难用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性骚扰相关讨论中女性群体的集体共情和义愤填膺究竟源自何处,但一味质疑受害者“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报警”、坚持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奋起反抗也真的是挺可笑的。即使是身为一个男人,在社会中也会有许多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的时刻,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在所有这些情境中都反抗了吗?饭局上被领导灌酒时你说不了吗?公司要求无偿加班的时候你离开办公室了吗?遇到颟顸的官僚作风时你是怎么做的?
男性和女性,雇主和员工、富人和穷人、官僚和平民,结构性的不平等如格雷伯所说,一直在产生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我能理解这种“慕强”心态掩饰的其实是恐惧、羞耻和某种庆幸,但真正相信“人人平等”这一现代价值观的人,应当在上述每一个不平等结构中都逻辑统一。
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圈的男性被曝性骚扰虽然不令人意外,但格外令人心寒的原因——他们饱读诗书,熟谙理论,或许还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但性骚扰暴露了他们的言行不一,揭示了他们心底的真正想法——“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尹清露:关于官僚制的结构性暴力子人说得很清楚了,我还想补充两个地方。首先,格雷伯认为我们在今天不怎么提官僚制了,是因为它已经越过政府部门,全面渗透进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也被混为一谈。男性上位者对女性的权力性侵害也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它造成的结果就是权力结构更加密不透风,就像美国某报纸在回应哈维·韦恩斯坦强奸案时说的:“韦恩斯坦等人仅是金字塔顶端的作恶者。而顺着金字塔顶端到底端,无权无势的普通女性也不能幸免,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另外,在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共同体中,权力上位者(男性)无需费心去理解下位者(女性),“女人心海底针”这类说辞就是通过神秘化女性,免除了理解她们的义务。与此同时,女性却被期待从事大量“阐释性劳动”,比如在每一轮性骚扰事件中,女性都必须换位思考,反复用男人听得懂的话解释“为什么性骚扰是不对的”。格雷伯也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指出,女主人的角色总要投入旷日持久的精力,来维持丈夫高傲的自尊心。

不过,真正给我启发的是接下来这段话:“在工业领域,通常是上位者包揽了更富于想象力的工作(例如设计产品和组织生产),而当社会生产领域出现不平等时,最终是下位者主要承担了运用想象力的工作。”格雷伯也提到,人类世界并非自发形成的,它的存在缘于集体的生产创造,“我们凭喜好想象事物,然后将其变为现实。”
那么,由于女性更了解男性,女性是否有可能把本来用作阐释和维护的想象力,变成生产性的想象力呢?这次的当事人小默就是这样做的,小默觉得自己有点“讨好型人格”,那篇文章文风也颇为幽默风趣,充满了自我调侃,只不过这种调侃曾经是男性文人赞许的品质,现在则被转译为我们的武器,一举打破了文化圈男主导的那种叙事习惯——看似对聪明女孩青睐有佳,实则只把人家当成“大飒蜜”、觉得揩油也算是男性长辈关爱后辈。
回到男女在面对性骚扰时舆论场撕裂的问题,我也在想,诸如小默的例子是否能稍微弥合这种撕裂。我前面提到的那名男性朋友也看到了小默的发言,并微博艾特我表示看懂了,认为这些话让他审视了过去自己做过的不得体行为。我一方面有点欣慰,另一方面也再次无奈地觉得,为了让你们听懂,女性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