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与对大学性骚扰事案的调查和调解,上野千鹤子学习到了一个事实,即性骚扰的加害者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

来源:视觉中国
按:近日,包括出版品牌“一頁folio”创始人范新、青年作家宗城、南京先锋书店某员工在内的多个文化圈人士被指控有性骚扰行为,其中关于编剧史航的指控在舆论场中引发强烈关注。
4月26日,接受出版行业匿名投稿的豆瓣账号“青年编辑们”发布一则帖子,“怎么还没有人出来锤SH,我身边有两个女性都曾被他动手动脚、性骚扰过。”随后在评论区和转发区多人指出“SH”即为史航。截至今日,已有23位女性爆料讲述被史航言语、肢体性骚扰的经过;史航于5月1日和5月2日在个人微博上回应称,性骚扰指控不实,“我和几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包括有过稳定关系的前任。我从不回避自己是俗人,但从不希望将自己与相识女性间的‘风流交谈’和‘门内的情调’暴露在公域之下,这不是偷换概念,也不是所谓的‘危机公关’。我从未违背女性意愿,亦从未利用过所谓的强权地位侵犯任何人。”

在该事件的持续发酵中,如何定义性骚扰再次成为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当涉嫌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讲述自己的经验时,涉嫌的加害者及其同情者认为“那是双方同意的”,两者之间存在的认知差距是显著的。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认知差距?性骚扰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权力结构?
2017年,伊藤诗织在纪实作品《黑箱》中实名举控自己曾遭遇日本著名记者山口敬之强奸,在日掀起了反性骚扰运动的浪潮。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增订版》中特别为此增加一个篇目讨论性骚扰问题。她指出,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来说,难以排解的不快甚至屈辱不仅是因为人权被侵犯,更是因为男性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实践,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优越的性别地位,宣布女人不是被当作同事、职场人、工作伙伴得到评价的,而只是一种“性价值”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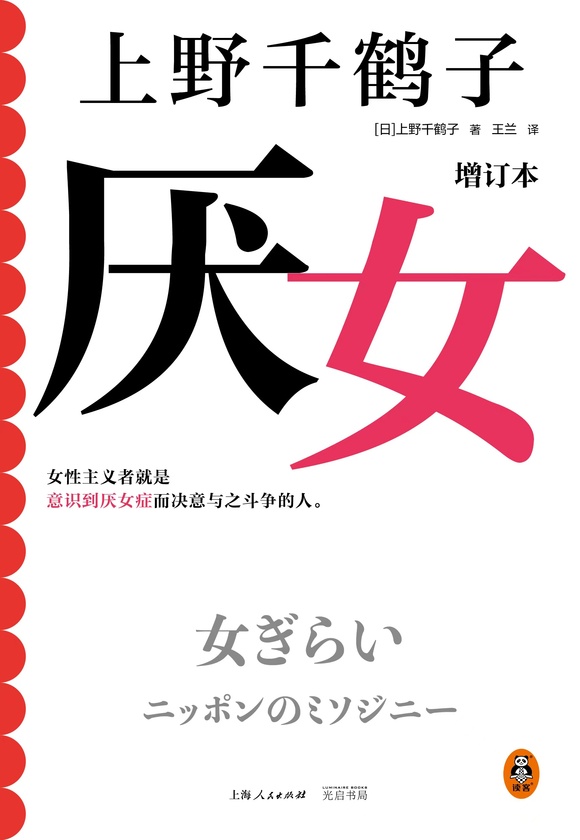
上野发现,性骚扰的加害者具有一些共通点。第一,他们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第二,他们对受害者的意愿极其迟钝,“即擅长将对方的笑容和暧昧态度,全部理解为对自己的好感,将环境场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上野认为,性骚扰举控数量的增加反映的是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公共生活,且不再轻易退出职场,用性骚扰作为男性的“职场润滑剂”的同时使得女性“继续工作变得困难”的做法就越来越难以被女性忍受。她呼吁,要求受害者发声、规避侵害是苛刻冷酷的,更重要的是让让“高危人群”的男性努力“不要成为加害者”。
文 | 上野千鹤子 译 | 王兰
性骚扰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从美国引进的。那时,美国已经相继出现性骚扰诉讼,其中尤其是针对日资企业,例如住友商事美国分公司、三菱汽车美国分公司等的诉讼案件,赔偿金额非常高昂。于是,在美国展开业务的日本跨国企业,逐渐懂得了“性骚扰代价昂贵”。当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美国女性不能做的行为,迄今为止对日本女性则是司空见惯。我还记得,当时有在纽约的日资公司工作的日本女性抱怨说:男同事们对美国女性小心翼翼,回过头来面对日本女性时,很“自然”地就松懈了。男人的所谓“自然”行为,就是傲慢蛮横、不顾女性心理感受的举止。当地录用的日本女性职员,一直忍受着公司总部派来的男职员的性骚扰,她们诉说:“美国女性举控性骚扰,后果却由我们来承受。”
20世纪80年代,有个名为“思考劳动与性别歧视问题的三多摩之会”的组织,实施了一次“性骚扰万人问卷调查”,暴露出性骚扰的真实状况。1989年,日本第一起性骚扰案件在福冈起诉,同年,“性骚扰”一词获年度流行语大奖。一时间,各类男性期刊多有讥讽嘲弄,诸如“说句‘长得漂亮’也是性骚扰吗?职场气氛变得紧张死板”之类的标题,频频映入眼帘。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性骚扰”一词,其实是由男性媒体的“嘲弄的政治学”而传播开来的。
1997年,关于职场性骚扰,发生了一次范式大转换(paradigm shift),即“改正均等法”将性骚扰的防止与处理规定为经营管理者的责任。通过这次法规改订,接受“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对象,从容易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变成了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中层以上管理职位的男性,实现了180度的大转换。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内容,让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学习如何避免受到性骚扰或者遭遇后的应对方式,变成针对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男性管理职位及高层干部,告诉他们,什么是性骚扰,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加害者。由此,防止性骚扰教育的教材和讲师,需求顿时高涨,市场迅速扩大,甚至被戏称为“性骚扰产业”。在我工作的东京大学,教授会全体成员也每年必须接受一次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一般而言,高层职位者成为性骚扰加害者的可能性较大,而其中最大的,则是独揽大权无人牵制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之类。各地方基层行政长官也不例外。这些都是“高风险人群”,他们需要接受防止性骚扰的教育。
1997年的法规改订,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风险管理方式。迄今为止,企业的组织防御方式,是保护性骚扰加害者,排除受害者;但如今,已变成尽快排除加害者。
防止性骚扰的法规,出自被分类为劳动法规的《均等法》并非偶然,因为,性骚扰就是一种工伤。从前,性骚扰甚至被称作“职场润滑剂”。新闻行业工会的女性记者们,将性骚扰视为“工作的一环”一直接受下来。长期以来,性骚扰被视为女性劳动者为了履行职务而应当忍受的成本之一。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山形交通公司的性骚扰事件中,我们得知,旅游车司机对女性导游的强暴,曾被视为一份“职业利益”。
性骚扰的定义,分为“环境型”和“报偿型”两种,不过,二者都是“滥用由职务地位获得的权力”,通过“违背受害者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使受害者“继续工作变得显著困难”。职场里的等级制度,赋予了上层者发令指挥的权力,但这只能限于工作范围之内,如果越权到私人领域,就是职务权力的滥用。我们已知的事实是,在职务上被赋权的人,有瞄准不能(或很难)说“不”的弱势立场者,乘虚而入的倾向。职场中的弱势立场者包括:部下、劳务派遣职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加害者的行为绝不是由于无法控制欲望的冲动,而完全是在针对容易下手的对象行使手中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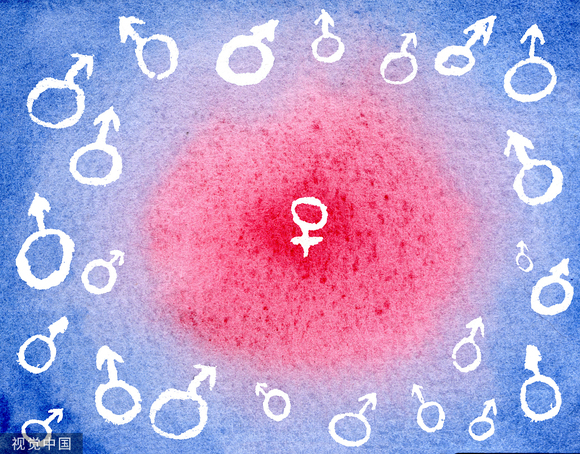
在性骚扰知事横山诺克一案的审判期间,作家曾野绫子在《每日新闻》的专栏里(曽野,1999)曾这样批评受害者:“当时不说不,事后才举控,很卑劣。”再也没有比这种言论对性骚扰问题更无知的了。性骚扰,正是针对“不会说不”“不能说不”的对象下手的行为。在横山的事件中,一方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知事,一方是临时参加选举活动的播音员,在这种关系之下,被关闭在选举活动车的密室之中的女性,怎么可能说“不”?
在对性骚扰下定义的条件中,有一项是“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此时,判断是否“违背本人意愿”,完全取决于受害者一方。性骚扰的加害方对此规定很不满,他们说:“同样的言行,明明有时对方还很高兴呢。”可是,表面看来是一样的性接近,当然也会有“被欢迎的”和“不被欢迎的”,这很正常。什么是“被欢迎的”?什么是“不被欢迎的”?这只能由当事人来下定义。这个法理,让人想起日本可以夸耀于世的“公害基本法”。过去,在漫长的公害诉讼中,受害者一直被迫承担对受害的因果关系的立证义务。但随着判例的积累和反公害运动的发展,公害基本法得以成立,在这一点上实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由受害者承担的对因果关系的立证义务,变成了由加害企业承担的对因果关系的反证义务。如果再次使用“对场景的定义权”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对性骚扰的场景的定义权”,掌握在弱势者的受害者一方。
在性骚扰的定义中,还有一项是“使继续工作变得困难”,这也十分重要。这首先意味着,女性进入职场,职场里有女性,已经是理所当然。同时,这还意味着,对于女性,工作不再是随时失去都不可惜的意义轻微的临时之计。女性持续就职期间的平均数据,呈逐年增长之势。当职场成为女性不能放弃的重要场所,那么,“使继续工作变得困难”的要素就会难以忍耐。女性自然地会寻求对工作环境的改善,让继续工作成为可能。由我看来,在性骚扰举控件数增加的背后,是职场对女性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事实。
《均等法》继1997年改订之后,2007年又再次改定。这次改订的要点,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均不再限定性别。女性也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加害者,男性也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另外,无论何种性别,属于性少数派的群体都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均等法》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禁止惩罚条款,所以一直被批评为漏洞很多不具实效的一部法规。但是,通过这两次改订,企业对性骚扰变得敏感,这一点不妨给予肯定。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设置了受理性骚扰的投诉窗口或负责人,不过,尽管如此,如果性骚扰发生在不同的组织之间,或者与非雇佣者之间,依然还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课题。前者比如营销人员受到客户企业的员工的伤害,后者比如独立职业者受到签约方的性骚扰。劳务派遣员工在工作现场受到的性骚扰也可归入此类。劳务派遣员工受害时,是向劳务公司举控还是向工作现场举控,结果又会不同。向工作现场举控,会有被中断合同的风险;向劳务公司举控,则很可能被强迫忍耐。伊藤诗织的事件,可以说是发生在有所属组织的人与独立记者之间的性骚扰。对于没有组织保护的劳动者,救济他们的机制至今尚未建成。
通过参与对大学性骚扰事案的调查和调解,我学习到了一个事实,即性骚扰的加害者有共通点。
加害者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相反,性骚扰受害者容易落入的陷阱是,以为只有自己不幸碰上,于是选择孤独沉默。矢野事件让我们看到,受害者的忍耐,是在知道别的女性也遭到同样的伤害之后才终于结束的。而且,加害者一方完全缺乏加害意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隔阂。加害者意识不到,他们眼中的“这点儿小事”,却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在此之前,加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即擅长将对方的笑容和暧昧态度,全部理解为对自己的好感,将环境场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对受害者的那些没有明确地语言化的拒绝信号,加害者是极端迟钝的。在一个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受害者即使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应该是用身体发出了拒绝信号的。看着性骚扰的加害者,我真是想说:“受到惩罚的,就是你的迟钝。” 而这一点如果被人指出批评,他们还常常反过来恼怒发火。
不过,对性骚扰加害者的困惑,我也有能够理解之处。他们之所以是惯犯,就是因为“我只是在重复跟以前一样的行为嘛...... ”从前被容忍的行为,如今不再被原谅,男人们为此而困惑。对此,我们本来没有理由去同情。对,是的,你一点儿也没变,但社会观念已经变了,女性的意识已经变了。迄今为止的女性或许能忍耐的言行,年轻一代已经不再忍了。这还不单是代际间的变化,也与女性的职业意识有关,随着晚婚化和就职率上升,女性不再轻易放弃职场。从前,女性遭遇了不快,或许就默默地离开职场;但现在,她们不再沉默,而是选择举控。

20世纪80年代末,当性骚扰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著名政论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曾说“女性进入职场,就好比一个女人裸着身体闯进男人的澡堂”,所以,不管遭遇什么都只得忍受。可是,职场既非“男人的澡堂”亦非私人空间。如今,一切职场皆有女性,同时,职业之于女性也已经不可或缺。
所以,“妨碍履行职责”的性骚扰,必须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工伤”来处理对待。
性骚扰这个问题,实质到底在哪里?性骚扰构成侵犯人权的不法行为,这在法理上已经成立。那么,被侵犯的是什么人权?“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所侵犯的,是在各种人权中被称作“性的自我决定权”的那一种。可是,真的仅仅如此吗?对于性骚扰,“侵犯人权”一语尚无法言尽其中包含的不快之感,这里还有更深的缘由。
性骚扰是一种社会性别的实践行为。对于拥有工作和从事研究的女性,性骚扰的行为,就是将她们降低还原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属性,向她们宣称:“你是个女人。”“你终归只是个女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是一种男性权力的夸耀。然后,通过这种夸耀,他们得到作为男人的身份确认。这就是性骚扰问题的核心。
女人是什么?就是“非男人”的群体。对于作为主体的男人,作为客体的女人,是为满足男人欲望而存在的群体。所谓女人,就是为激发男人的欲望而存在的诱惑者,因此,她的价值以“看你多能让老子发情”来衡量。相反,“不能让老子发情的女人(丑女、大妈)一文不值”。女人总是被男人的视线估价。
女人是何时成为女人的?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对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下过一个精彩的定义。即所谓思春期,与年龄无关,是“从少女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对象的时候”开始的。
如果有人要问:“说句‘你好漂亮’,也是性骚扰吗?”我会回答:是的。当男人将各种女性用美丑来比较时,他是将自己置于“估价者”(评判者)一方。赋予女人价值的,是男人;被男人赋予价值的,是女人。也许有人会说:“女人不也在对男人估价吗?”可是,男人对女人的估价,是一种集体行为并且集中在性的价值方面,在这一点上,男性一方掌握了压倒优势。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实践,男人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优越的性别地位,由此向“非男人”的群体宣告:“明白你的身份!”

相反,女人什么时候不再是女人了?不再“让男人发情”的时候,成了“大妈”的时候。2018年4月20日,当在野党女性议员们向财务省发出抗议时,自民党议员长尾敬在推特上说:“这些女士离被性骚扰远着呢。”这种话语正是性骚扰。因为他表达的观念就是,女人只有能激发自己的性欲望时才有价值,所以他的发言就是社会性别的话语实践。
顺便提一句,所谓性骚扰的受害者年轻漂亮的说法,在现实中是彻头彻尾的神话。事实上,女性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与年龄、容貌、体型无关。残障人设施里患认知障碍的智障女性、养老院里卧床不起的高龄女性,都会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在女人被男人视线估价的社会里,性骚扰咸猪手的目标仅限于“年轻漂亮的女性” 的神话,具有反复强化这个男权机制的效果。
本书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这就是厌女症的机制。与强奸行为一样,性骚扰加害者的行为,并非由于性欲,而是由于厌女症。因为,厌女症就是男人将自己与女人区别开来、确认自己为“非女人”的机制。性骚扰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容易掉入的陷阱是,“举控性骚扰的受害,会被认为是在炫耀作为女人的魅力”。与此相反,对性骚扰的举控,男人还有一种抵赖逃脱的手段:“你就当真了吗?也不看看自己长成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常见的男人对女人分离支配的手法。前者是对美人灌输选民意识,后者是对丑女宣布没有性的价值。被分离隔断的受害者,于是相互孤立,保持沉默。可这只是一枚硬币之两面。男人等于是在宣布:女人不是被当作同事、职场人、工作伙伴得到评价的,而只是一种“性价值”的存在。这个社会,甚至让女性发出“我一次也没遇到过咸猪手”的哀叹,让她们必须为自己没有女人的性价值而感到羞耻。性骚扰,将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厌女症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
在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性别不对称的机制之下,制裁性骚扰,仅为一时止痛之计。让人恶心的腐臭,必须从根源上清除。结构性地反复产出性骚扰的父权制体系才是诸恶之源,可推翻父权制非常困难。迄今为止,都是女性在举控性骚扰,但性骚扰本来应该说是“男性问题”,所以,只能由男人来解决。
直到最近,终于出现了与女性为伍的年轻男性,他们说“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在新宿ALTA大楼前的“#我不再沉默0428” 集会中,看到年轻男性手握话筒与女性并肩而立的场景,我被感动了。与三十年前那些对女性的性骚扰举控极尽冷嘲揶揄的男人相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在他们的发言中,也有让我忧虑之处,即“如果受害者是自己的恋人姐妹,你能容忍性骚扰吗”之类的话语。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为了让学员留意不要成为加害者,讲师会让他们想象“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呢”或者“要是自己的妻女也遇到同样的事呢”。
大家也许会想,这种发言有什么问题吗?其实,问题多多。因为,这种发言的前提就是:女人的性,不仅应由男人保护,而且归属男人所有。“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便不敢轻举妄动,这不是在尊重女性的人权,而是畏惧其所有者“上司”的权力。如果因为“被害人是自己的恋人姐妹”而义愤填膺,那也是对没能尽到对自己所属物的监护责任而升起的所谓“男子汉”的愤怒。
迄今为止,女人的性被用作男人之间的交易资源。如果监护失败,男人会感到愤怒屈辱。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侵犯,不如说是对(被认为是)女性所属的男性集团的侮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更能激起愤怒。当男人明白自己无力保护女性的时候,他们采取的行动有三种:抛弃、奉献和排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大陆撤回时,曾向苏联士兵“奉献”女性;被美军占领后,对为占领军服务的慰安妇(她们后来被称作Panpan) 的做法,则是“奉献”之后再“排斥”。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将这种男人称为“保护勒索男”,指“以保护为名,强迫女性依赖自己并限制其行动的男性”。将查尔斯的这种说法介绍过来的,是佐藤文香。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象力还停留在“假如受害者是自己的妻女”的程度,那证明我们并未走出父权制的领地。对于“保护勒索男”,女性应有的回应是:我的性我做主,才不稀罕你的保护!回顾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女性主义不是一直在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一直在主张“性的自我决定权”吗?性的自我决定权,就是女性对父权制性支配的终极拒绝。正因为如此,对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侵犯,就成为社会性别支配的核心。
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有的老师说:“既不要成为加害者,也不要成为受害者。”可是,不成为受害者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而且,要求受害者发声,则更为苛刻残酷。我们需要的,是让“高危人群”的男性努力“不要成为加害者”吧。对,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厌女:增订本》中《增订一:诸君,勿污晚节!——性骚扰问题,实质何在?》一文,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