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90年代,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变化也折射出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变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辈对“老人”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二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十篇:《重返九十年代之留学潮》
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电话另一头是美国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卡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打电话?
布热津斯基报告说,此时他正在北京,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有什么坏消息吗?
布热津斯基:不是坏消息。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留学。
卡特:你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
这是《人民日报》记者温宪2013年11月10日在采访美国前总统卡特后发回的报道内容。经过一番酝酿之后,1978年6月2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这个消息如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然。但正是此项决定以及之后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落实,使得中国先是在80年代出现了大量公费留学人员,随后自费留学人员也不断增加,并在90年代迎来了留学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有机会走出国门的是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提及,1978年,中国有13名副总理级别的干部累计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此外还有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在傅高义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
而推动学生出国留学也与改革有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认为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邓小平认为科学和教育是头等大事,科学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他第一次谈到这项工作时说:“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邓小平曾有过留学法国的经历,他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感受。
1978年6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人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他指出︰“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办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6·23指示”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
除了派遣留学生,中国也开始出现自费留学生。据新华社报道,1978年,整个上海只有8个人申请自费留学,但1979年,自费留学人员超过千人。1981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的基调得到了确定:国家在政治上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对自费留学的限制逐渐放宽,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要坚决大胆放开”的政策取向,这使得1985年以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更为迅速。
在《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一书中,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俞敏洪谈到,1980年,他到北大西语系读书时,同学中“还几乎没有出国的”。而从1982年开始,他的大学同学中开始零星有人出国读书。在他本科毕业的1985年,全班同学都抱着“考着玩一玩”的心态,参加了没有经过备考的托福考试,不过此时大规模的出国潮还未出现,同学们“几乎全都被分配到了国内的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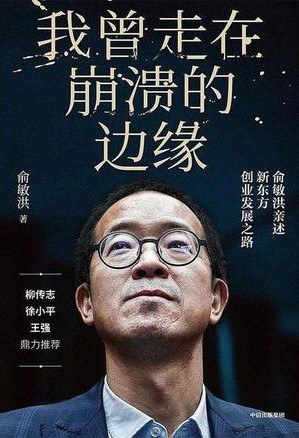
当时间越来越靠近90年代,俞敏洪发现身边出国的朋友渐渐多了起来。1988年,看着朋友中陆续有人出国,他也产生了想要出国深造的想法, “不出国进行深造的话,我会在未来的世界失去机会。”然而获得国外学校的奖学金并非易事,俞敏洪需要自己挣出学费。他先是参与了一些培训机构托福和GRE课程的教学工作,随后发现,这不如自己开培训班来钱快。于是,在1990年,已经是北大正式老师的他向学校提交了辞职报告,着手创建培训班。
清华大学新闻网2008年的一篇题为《留学的历史定位:划时代的留学潮》的文章中谈到,1981年,美国首次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以北京为例,当年参加者为285人,1985年上升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的考生有4万多人。文章称,到了90年代,为了报名,“常常要通宵排队,但仍有未如愿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绩则越考越高,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补习班则越办越火。”
不过,国家的出国留学政策并不是陡然放开的,而是经历了一些反复。1968年出生在陕西延安安塞县的李延龙如今在美国做药物研发方面的工作。他回忆说:“1985年上了大学以后,在班主任的熏陶下,我逐渐开始改变想法,隐隐约约觉得出国可能是一条好的出路。”好景不长,1989年侨属关系政策实施,规定只有亲属在国外生活的学生才可以出国留学,出国的道路平添重重阻拦。当年大学毕业的李延龙无奈只能先去了一家位于石家庄的制药厂工作。然而药厂工作微薄的收入让他觉得不论自己再怎么努力,前路都很渺茫。他供职的研发小组经过不断实验终于将当时一款售价达5000元的免疫制剂的成本降了下来,然而,这一成果所收获的经济收益几乎与小组成员无关,“拿到手里的工资一年只有一千多块钱,连体面的生活都过不了”。
事情不久之后就有了转机。1990年,美国出台的《1990年移民法》,提高了入境移民的最高限额,每年增至约70万人,且美国公民的近亲亲属不受配额限制,被称为是历年来最宽松的移民政策,美方摆出加入全球人才争夺战的姿态。而中国政府为避免人才外流,曾一度对当时想要出国的人员增加了限制措施。
今天回过头看,《1990年移民法》引发的留学潮波动只是个小插曲。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并肯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常态化的留学政策逐渐形成。出国政策逐渐松动,提出公派“按需派遣”,自费“随时申请”。李延龙也加入了当时自考托福和GRE的大军, “当时在石家庄没有考点,我要去北京航空学院(指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考试。费用也很高,报名费加上差旅费,差不多花了我大半年的工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城市的学生已经可以在新东方等出国中介的帮助来实现留学梦,身处边远地区的邢建军则根本不知道有新东方和中介机构,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学好外语,想要抓住公派留学的机会,实现人生的蜕变。
决定要留学时,邢建军已经是青海畜牧兽医学院(后与其他学校合并成青海大学)的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回想起自己出国的动力,他坦言:“那时候的想法都很朴实”,就是改善生活。有个同事公派到澳大利亚待了一年,带回了微波炉,大家看了都觉得神奇。他琢磨着拿着奖学金,再自己打打工,省点儿的话,收入比在国内的工资还要高。
在90年代初,邢建军周围已经有一些人选择告别铁饭碗,辞职去了海南和深圳,当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为小企业主挣到了钱,但邢建军决定扎实学习英语,等待时机出国。他学习英语的材料是中央民广播电台每个周日的《星期日英语》节目和一本叫《英语学习》的杂志。此外,他还想看《China Daily》,但三百多块钱一年的定价对他来说实在太贵,就一群人哄着学校图书馆订购了来。报纸订来后,邢建军常常在图书馆抓时间阅读,有时候一看就看到管理员要下班的时间,管理员干脆让他拿回家看,他就抓住机会,晚上在家一边看报一边查字典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邢建军选择的是公派出国的方式,也就是政府间的合作项目。那时候公派项目派遣的都是有工作经历的人,他所在的偏远地区也有一些照顾性的政策,因此他所在的单位有去欧洲的项目名额。“当时我们到欧洲,一张飞机票要1万多,我一个月才挣一百多块钱工资,这钱,如果公家不给出,哪里来?”
出国前,邢建军的父亲已经患病,出国后,夫人也已经停薪留职在家带孩子,这意味着他成为了一家人生活的全部经济来源。在意大利,他和很多国人的生活都过得非常简朴:“能省就省,房子住得远,租金要便宜,各方面都要精打细算,比如要到卖折扣商品的穷人超市里买东西。”在超市里邢建军最常买的是洋葱、鸡蛋、西红柿,因为煮意大利面是生活的标配。而猪肘子、猪蹄子意大利人不吃,价格就会比其他肉类便宜得多,所以每每到了周六,一起出国的几个中国人会一起凑钱买个猪肘子,煮煮炖炖,就上最便宜的啤酒、葡萄酒,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每逢周末,邢建军还要去当地中餐馆打工当“三厨”,主要工作就是把冰箱里提前冻好的蒸饺放笼屉里蒸,或者下油锅里炸。偶尔他也会和朋友们去酒吧里喝一杯。之前在国内的教育观念里,人们会觉得酒吧是色情场所,五六块钱一听的可口可乐在国内也过于奢侈。他到了意大利的酒吧,指明要喝罐装的可口可乐,旁边就有人说,你喝这破玩意干啥?
1994年4月20日,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日子——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全球互联网,从此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在邢建军的描述中,1994年,意大利早已“有了internet(互联网),也有了email(电子邮件)。在学校,电脑都是苹果Macintosh”,因为“人家都已经有word、excel了”,邢建军从国内带的DOS操作系统的书一页都没有翻。他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打开电脑学习。“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心态,知识改变命运,我从青藏高原出来,和国内一些地区差距已经很大了,而这些地区和国外的差距就更大。那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学出来,就可以拿到学位回国做个博士后,进而能进北京,能解决老婆和孩子的户口。”

从邢建军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当时西方一些国家的先进和发达,成为了许多国人眼中不言自明的出国原因。而对这些国家的羡慕和仰视,中间也暗含着对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焦虑。微波炉、可口可乐、苹果电脑,这些来自西方的事物也不仅仅是普通的商品,更象征着现代化的承诺。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谈论“现代化”,就好像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不过,“现代化”的这套历史叙述从何而来?《“新启蒙”知识档案》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到,这原本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发明出来的。在冷战的背景之下,为了与前苏联“世界革命”发展模式对抗,美国创造了一套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范式,也就是“现代化理论”。在这套理论中,所有的国家都被拟定了一条导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世界时间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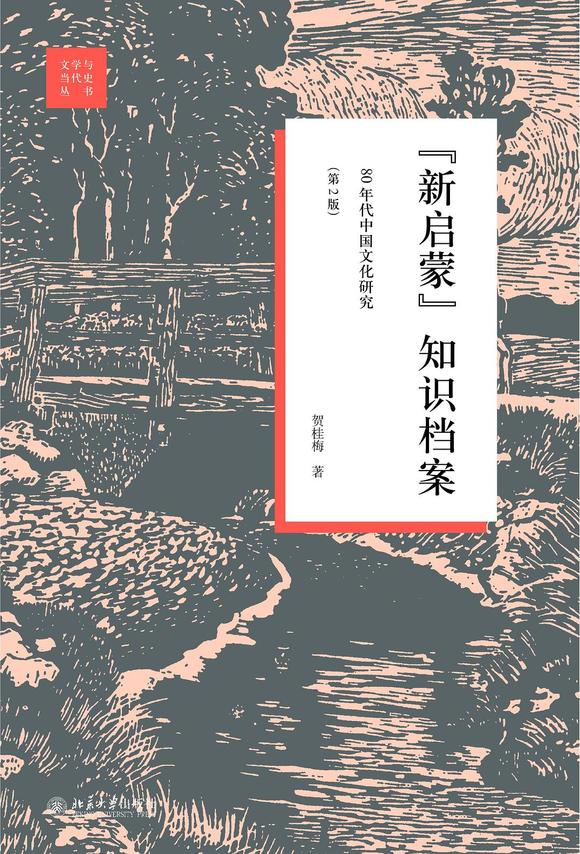
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市场从对中国进行封锁和遏制到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体意识也生成了。贺桂梅看到,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自我憎恨式的视角,“即70-80年代转型期的全部社会问题都来自中国内部,而全部希望则来自于中国外部”。
由此可见,在上世纪8、90年代前后国家推动及个体进行出国留学的选择,是为了学习西方一些国家的先进和发达之处,但除了来自海外的吸引,人们能够选择留学也和国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国家统一招生、统包学生所有费用以及统一分配的“统包统配”制度曾经缓解了新中国建设急需人才的矛盾,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统包统配制度下,高校办学积极性难以发挥,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也少有选择权。人才的使用根据的是编制的需要,但不一定是本人的才能。用非所学、人才闲置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1987年,北京第一次举办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见面的供需洽谈、双向选择会。不过所谓的双向选择,依然是一种过渡性方案,受到很多政策的影响。例如,用人单位每接收一个毕业生,就要考虑到干部编制、工资指标、外地生进省(区、市)指标等因素,缺一不可。在北京,高教局每年给高校的“留京指标”约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10%。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举措。频频有人向相关部门反映:“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为什么北京的孩子就天经地义地留这儿工作?为什么就不让我留下?”生源的流向依然受限,类似的疑问依然存在。
虽然在体制内拥有铁饭碗的就业愿景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但向往着流动的就业者逐渐多了起来。据刘明华在《世纪旋风:人才“大逃亡”》一书的记载,在90年代初,中国科技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介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中30%有流动意向,但人才流动率仅有2.6%。“中国人的长期不能动,已使很多人产生不愿动的惰性。领导喜欢安于现状的下属,而安于现状不可能激发一个人的活力。”当时间迈入90年代,流动从某种程度变成了时代的呈现方式,跳槽、辞职、下海等等择业和流动的方式,让人们拥有了丰富经历、展现价值的机会。

1992年,刘震云创作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讲述了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机关单位,过上了平庸琐碎甚至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小说里,在体制中“送礼”和“走后门”成为托人办事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主人公也逐渐安于现状,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同一年,胡咕噜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读书,“那时户口制度还很严苛,大学生毕业都包分配,即便自己寻找到了更喜欢的岗位,依然要被各种户口和指标锁死。与此同时,我们目睹的是下岗的上一辈人迅速被社会遗忘,日益感到人们各自为战。当我开始要面对未来选择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这些方向混杂的洪流。”
胡咕噜提到了崔健1994年的专辑里一首叫做《彼岸》的歌,这首歌一共有四句:“这里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共同面对着同一个现实/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胡咕噜每次听这首歌,想到的都是,中国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共同命运,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集体感。“我出国的原因可能是在下意识摆脱它们。”他说,中国人有“被一种被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越年龄、地域和阶层,是一种“老百姓”的身份,是一种他想要摆脱的中国人的集体情绪。“在九十年代,让我想起这种感觉的除了春运,还有97年香港回归和98年大洪水这类事件。“

《彼岸》这首歌中,崔健在街头访问路人,问了若干问题,其中一个便是“你想出国吗?” 胡咕噜最早听说“中介”这个词时,是指出国中介而不是房地产中介。1998年他在新东方上课,听校长俞敏洪发表励志性的演讲,因为接受国外考试中心的成绩单和学校新建需要稳妥的通信地址,他还在新东方的办公室租了一个实体邮箱,只为了等和出国有关的那几封信。他还记得那个办公室就在北大南门对面的写字楼里。
1999年是邢建军归国的年份,他通过留学实现了进京的梦想。同一时间,胡咕噜正准备离开北京。和邢建军不同的是,胡咕噜自述出国的缘由是寻找在世界中的位置和适合自己的生活。不同于90年代出国潮早期更多人是公派身份,此时自费留学(不走政府间的合作项目)渐渐成为主流。但是所谓的自费,并不是字面意思上说的自己掏钱去上学,而是选择自己联系学校,考GRE、托福,拿到offer和奖学金资助,再去留学。“每年几万美元的学费在那时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天价,美国高校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让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留学变得可能。对个人而言,美国无论是在科技还是文化上都是我愿意探索的一片土地。”
胡咕噜最早认识的打定主意要出国的人,是他的一位热爱理论物理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每天晚自习结束后都要到小卖部买一瓶冰镇的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过生日时会要求胡咕噜到海淀图书城南口的麦当劳请自己搓一顿,他们还一起解读了《加州旅店》的歌词。“我们都是不算追求物质生活的人。那时美国虽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发达国家,但科技和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更有趣些。在这两点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在年轻人心中应该是有好感的。”
“我的同学里,选择出国留学的人确实都更个人主义一些。他们看起来不是在学校里就已经想着攀爬社会金字塔的人,而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我一样不愿意被分配之类的流程早早固定自己的人生。”“个人主义”这样的表述在社会主义中国曾长期带有贬义色彩,但在90年代的语境里,却已经有所不同。正如贺桂梅指出的,这是因为在80年代,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的人道主义表述已经批评了过去国家对人性的压抑,转而把“个人”视为绝对的价值主体。
《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电视剧也让胡咕噜有所触动。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王起明获得了在中餐馆刷盘子的工作,一个月900美元。“美国毕竟是一个海纳百川的移民国家,什么人都可能定居下来,并不需要是有钱人。传说中洗洗盘子就能买车的去处,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这样一部作品似乎是给九十年代的出国风潮定了个调:如今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国了,但都得靠自己打拼。不过,我觉得就是得靠自己打拼这个现实让它变得激动人心——个人自主选择生活道路,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在胡咕噜眼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反思,反思这个国家在之前几十年发生了什么,重新找回它的身份。知青文学和1983年首播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就算是在这些方向上的尝试。而九十年代开始之后,很多人都在思考,自己能拥有多少自由?假如那时出国移民和这个问题有关系,我一点都不奇怪。王小波在九十年代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很可能是他比知青作家想得更多,体现了更纯粹的自由。”胡咕噜认为这和王小波在八十年代的出国经历多少有关。
“自由”成为了胡咕噜眼中九十年代留学生的关键词。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一种具有整合力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上个世纪70-8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登台的时代。而在中国,人道主义知识话语也成为了80年代变革社会的庇护伞。贺桂梅看到,人道主义把人从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但是这只是其“解放”一面,它还有构建秩序的一面——建构更适宜于“现代化”的“经济个人”。
这也符合在胡咕噜对八九十年代不同气氛的印象——在他眼中,八十年代算是中国政治气氛最活跃的十年,而九十年代大家都开始埋头做个人发展了。“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把对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变成了对自我生活的一种期望。”
在意大利时,邢建军的夫人和孩子曾去探亲,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办妥了签证。“待了三个月,签证到期我就让他们回来了,因为是朋友做的担保,我这人非常仗义,不能让朋友吃亏。”那时候签证不容易办,因为担心中国人有移民倾向。他在国外属于学生身份,是没有能力担保家人出来的,必须找意大利朋友来担保,“朋友得到警察局、移民局签字,知晓各种移民法律,签了字才能办出来,费老劲了。”
当时确实也有不少出国门后“黑下来”的人。一些华侨对邢建军的行为表示不理解,有的人得给蛇头交十几二十万才能偷渡到这里,怎么他这么傻,好不容易把老婆孩子带进来了,还让他们走呢?
邢建军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在意大利期间,佛罗伦萨的宪兵打死了一位当地华人。两兄弟在意大利有一间制衣厂小作坊,晚上正在装车的时候,宪兵认为,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装东西,可能有猫腻,于是就来一探究竟。兄弟中的哥哥有合法身份,弟弟则是偷渡来的。哥哥就让弟弟赶紧跑,自己则阻挠宪兵追赶。在这个过程中,宪兵把哥哥打死了。“当时当地华人的反应好像也不是太激烈。有的华人跟我说,要是打死的是黑人,意大利警察局一个月都不得安宁,门口肯定都是人在静坐,可是中国人就这么忍气吞声,不了了之了。”
除此之外,邢建军也看到,和美国不同,欧洲总体来说对外来者比较封闭和保守。“在欧洲著名高等学府里的有几个中国人?掐着指头算也掐不出来。”他认为在欧洲,想留下来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进入企业打工。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选择“黑下来”,等待大赦——也就是让黑户合法化,前提是有人雇佣。
胡咕噜离开中国时,国内的政策是出国留学会被注销户口,还被要求交数额不小的培养费,不交就不给办护照。“当时办理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种被迫了断的暗示”。在他读研的那个年代,出了国后又回去的人似乎有着“混不下去”的嫌疑。“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只有两位回国发展了,但他们特意为了生孩子专门回来一次。我的老同学们里没有海归的,他们看起来都享受着自己选择的生活,偶尔会回忆母校、乡音和小吃。而特别追求事业的,比如我大学的喜欢理论物理的朋友,虽然和他有好些年没联系了,但我很清楚,他肯定认为在美国有一个更安静的研究环境。以我对他性格的了解,在国内高校任职肯定会令他烦恼不堪。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假如回去,可能会活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抱着这样的想法,胡咕噜选择了在美国定居。
胡咕噜也认识一些偷渡客,“他们花了很多钱在律师身上,一步步走着缓慢的移民过程”。但他同时也觉得,“就中国人来说,是否有身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没有什么影响。中国人就是劳碌命。努力想要留在美国,也就是努力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邢建军认为自己这一批留学生和80年代的留学生差别不是太大,“大家都是省吃俭用,想要获得知识,改变命运,把日子过得更好。”邢建军从2010年起担任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国区负责人,他见证了中国学生在留学这件事上的态度变化。他看到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主要靠奖学金,而现在的留学生很多要花家里的钱。“我留学的时候,咱们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跟国外是差距还是很大的,现在咱们新一代留学生到了意大利,都觉得‘村’。他们相互调侃都是‘我进村了’。”
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变化也折射出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变化。
在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有一种处于现代化未完成状态中的焦虑。在《“美国梦”转型——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一文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认为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中国与美国的情感就像恋人一样充满了爱恨交织”。他说,1980年中国对美国处于“暗恋”阶段,美国作为国人想象中的“梦中情人”,是现代文明的典范和理想之地。1990年代初期,这种“单相思”的情绪达到顶点,正如刘欢在《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里唱出的那种纠结——“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粗看起来,在90年代似乎也有一些反美情绪,例如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曾经风靡一时。1999年4月,美国炸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美国驻华使领馆都遭到了抗议和围攻。胡咕噜记得当时成都领事馆因此关闭,他不得不去上海领事馆签证,看到衡山路人行道上排队等候的依然有很多学生。然而,在张慧瑜看来,这些都说不上是真正的反美:《中国可以说不》其实并非在反抗美国为代表的全球政经秩序,毋宁说是求认同而不得的一种心态;而1999年的事件也没有否定美式价值观,反而是进一步渲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悲情。

这是90年代的特别之处。在新世纪,人们讨论起“大国崛起”,讨论起修昔底德陷阱,接着又讨论起了“文化自信”。在新世纪成长的年轻人,对美国和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与他们的前辈有着极大的差别。
邢建军意识到,今天,国家实力、家庭财富等因素使得留学生不会太操心经济上的问题,这一点和9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形成巨大反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则这样讲述留学生之间的代际差异:“00后大学生往往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以‘愿望思维’看待国际事务,认为中国很容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们常以中国与外国两分的方法看待世界,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视为同一类国家,将和平、道德、公平、正义等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视为中国独有的传统,认为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和无辜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邪恶’的、西方人对中国有着天然仇恨。”很难想象在90年代的留学生中会存在这种思维。
(胡咕噜为化名,感谢申璐对本文的贡献,按语写作:黄月。)
参考资料:
温宪《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2日《访谈实录》版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俞敏洪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邓小平时代》[美] 傅高义 著 冯克利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世纪旋风:人才“大逃亡”》刘明华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3-7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959198
新中国档案: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战略决策http://www.gov.cn/test/2009-09/30/content_1430681.htm
留学政策变迁40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829623527112672&wfr=spider&for=pc
《1978:留学改变人生》钱江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4
杨晓帆:《贺桂梅:走出思想史的可能与限度》腾讯文化 https://cul.qq.com/a/20150513/009585.htm
第五届教学共同体年会主题报告 | 阎学通:如何为00后大学生讲授国际关系课程https://mp.weixin.qq.com/s/GcftpDXIBDFJ26E570VHcg
张慧瑜:“美国梦”转型——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3/09/305763.html
张盖伦:《落实办学自主权 高校究竟如何做主》,科技日报 2018
http://m.people.cn/n4/2018/0830/c155-11528097.html
程元:《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
郭艳红,王芳. 世俗中的挣扎与沉沦,从刘震云《一地鸡毛》看知识分子的困境[J]. 电影评介,2008,05:104.
浦树柔:《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艰难的转轨》,《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31期
《留学的历史定位:划时代的留学潮》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874/745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