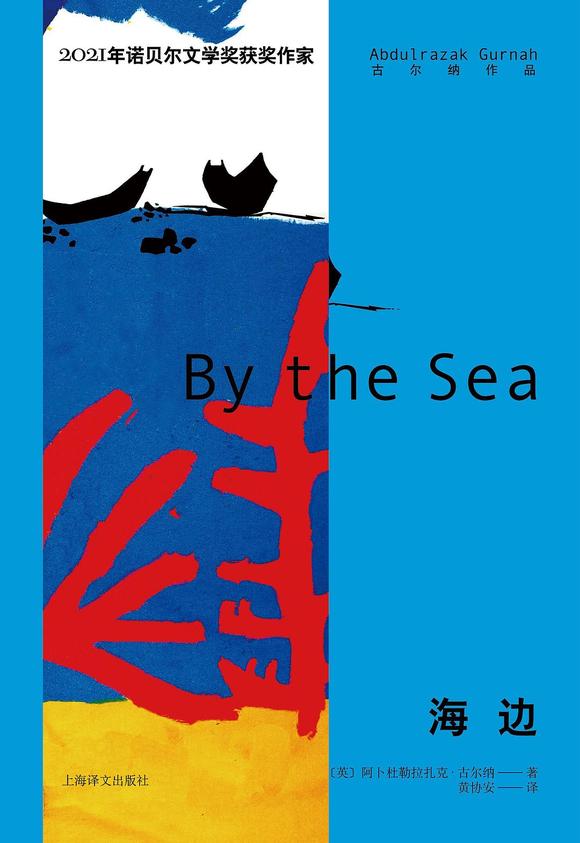距离古尔纳捧得诺奖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时间,界面文化对他进行了一次视频采访。他说,尽管人们可能在他人的鄙视目光下,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他们仍然可能从生活中找回自己最珍视的东西。

古尔纳 TOLGA AKMEN /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写作可以揭示冷酷专横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也可以让无足轻重的人保持自信,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讲述,他相信写作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或迟或早,残酷、爱与软弱会成为写作的主题。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古尔纳在东非桑给巴尔度过童年,1963年桑给巴尔独立,人们的生活遭遇了巨大的混乱,处决、监禁、驱逐时时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古尔纳与兄弟逃往英国。直到移居英国几年之后,他才开始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像是历史为何常常是偏颇的,以及人们为何对残酷保持沉默。多年后,当古尔纳回到家乡,重新走过那条从小长大的小镇街道,目睹那些两鬓斑白、牙齿掉光的人仍在生活,他意识到,有必要通过书写找回人们赖以生存的时刻。

在代表作《海边》里,古尔纳描写了从桑给巴尔逃往英国的难民心态。一个人在过关时就可能面对刁难与讯问,所以即便能说英语,也往往装作一无所知,直到感觉安全才开口说话。沉默或驯服的人们,一直是古尔纳关注的焦点。他在成名作《天堂》里写老园丁被困于美丽的花园中,从不想要自由,因为他相信自由就像太阳会升起一样自然,不是任何人可以夺走的东西。
偏颇的历史也是古尔纳书写的重要主题。《海边》里的孩子们佩服给他们上课的英国老师,或更准确地说,是屈服——因为英国人掌握那么多实用的学问,会开飞机,会拍电影,完全掌握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可是他们分发的历史书在讲到当地的疾病、人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时,又是那样不客气。相比之下,当地人对自己的理解显得古远而玄幻,如同神话。孩子们绝不会自卑,同时也相信,他们的知识比不过这些英国人。
在残酷的命运中,抒情与诗意仍然有生机,古尔纳为笔下的人物留有希望:少年喜欢花园里有坚实丰满的果树,相信石榴集水果之大成(《天堂》);孩子将每一封信都写得优美,让人以为他住在海边自由自在;知识虽会遭受污染,能够逃脱监督与等级制污染的名字仍会勾起人们高尚的兴趣(《海边》)。
距离古尔纳捧得诺奖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时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日前视频连线采访了他。他在采访中说,尽管人们可能在他人的鄙视目光下,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他们仍然可能从生活中找回自己最珍视的东西。

哈利勒告诉他,石榴集所有水果之大成。它既不是橙子,也不是桃子,也不是杏子,却包含每一种水果的元素。石榴树是丰饶之树本身,树干和果实就像勃发的生命一样坚实而丰满。
——《天堂》
界面文化: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讲自己听过许多故事,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古尔纳:并不都是很大的正式的故事,也许就是小的回忆的片段,我母亲说的关于她小时候的事,逐渐会变成其他的故事。有时候是成人和孩子玩的游戏,会告诉孩子什么是值得害怕的,什么不是。还有一些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的书本里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会通过口头讲述,关于先知的人生。还有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这很容易理解,当你述说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记不清细节了,就编造一些新的,或者选用你喜欢的细节,所以与文学意义上的故事相比就会有一些变动的因素。一些故事与重要人物和历史瞬间有关,但人并不总会意识到这点,因为讲述时会有一些变化,你会明白那不是真正的人物,而是一些特定的隐喻,比如恶魔或权力的化身。
界面文化:你在不同的作品里引用了许多桑给巴尔的信仰与神话故事,相较于被欧洲的知识塑造的头脑与心灵,那些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怎么看待两种不同的头脑与心灵?
古尔纳:这些信仰或神话对本来就熟悉它们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不是未知或特别的习惯、风俗和信仰。我决定这样处理,是因为从欧洲视角出发的、对这些人群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展现有种种不正确。如果你误解了这种文化,它也许看起来会是厌女的或是无思想的,但人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是由什么构成的,他们知道如何生活,也了解他们自己。思考他人的文化应当有一种谦卑的心态。
许多人都要么离开了,要么被驱逐了,要么已经死了。剩下来的人也都遭遇了无数的邪恶和苦难,没有哪个人大包大揽,也没有哪个人能逃脱。于是,我做着小生意,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于一定要说的话,语气之中也不带任何仇恨,听着人们诉说苦难的经历,我的心态非常平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命运。在人们的眼中,我坐过牢,经历过生死离别,是最凄惨的人,所以,他们和我说话的时候非常亲切,富有同情心,我则报以感激和无区别的善意。然后,到了黑夜,我独自一人住在摇摇欲坠的店里,我一想起逝去的亲人,就会伤心落泪,随着伤感日渐减轻,我转而因为碌碌无为而悲伤。
——《海边》
界面文化:小说里也写到了许多对自己的处境保持顺从忍耐甚至麻木的人,以《天堂》中的隐喻来讲,就像在花园里的植物。为什么要写到这样的人?
古尔纳:我并不是要将人们描写成受苦受难的样子,我想写的是尽管人们看似是无权无势、毫不重要的,但他们仍然有着完整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是简单地顺从于更强大的权势,他们仍然可以保全人生内心最重要的、最荣耀的东西。我并不想写那些英雄或是脚踩地球征服全人类的人,他们可以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我想写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值得写的人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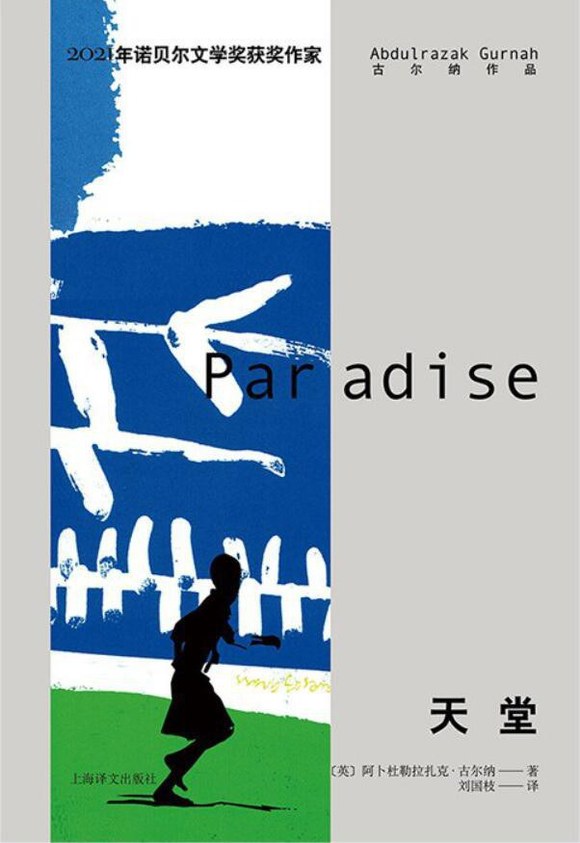
界面文化:“值得不值得”依据的是什么标准?
古尔纳:举世瞩目的成功,或者说可以克服困难。举个例子来说,《天堂》里的优素福看起来是一个受害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可轻蔑的角色,他还是有他的人生,他在他的人生中挣扎,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很多时候我们陷于困境,并没有“我正在人生途中挣扎”的明确意识,但还是拼尽全力去保存某样东西。这个困境也许会压垮你,会毁灭你内心最宝贵的东西,但你挺过来了,你抵抗了,你赎回了自己。
界面文化:一个人从现世中幸存,获得第二重人生,就像《来世》标题所暗示的那样?
古尔纳:对,来世。一些人的生活已经被削减贬低到一个地步,但他们又可以发现另外一重人生。他们从创伤中获得了一些可以让他们继续的东西,这些东西让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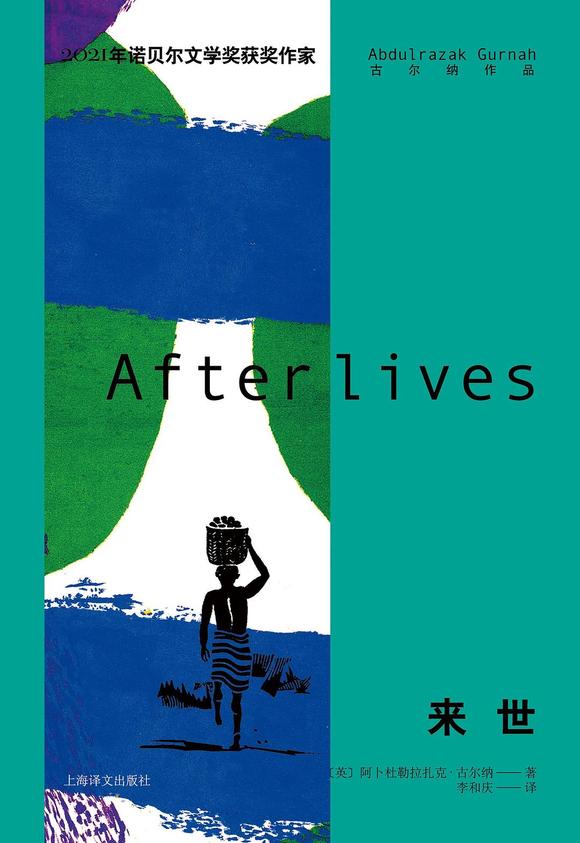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对她说,但这是个谎言。我记得许多事情,每天我都要记起它们,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要忘却。我本想着只要我还能再沉默一天,我就要对这一切保持沉默。我本想着只要我开了口,我就停不下来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说,先不要问我那件事。或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那件事。我本想着我可以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来说这些事情,免得让人从中听出怯懦与可耻来,可那个时机一直都没有到来。我不知道我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的礼物》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你在小说里也做了一种区分,将人群分为可以滔滔不绝说话的人以及那些无论如何都保持沉默的人,《赞美沉默》中尤其如此。我很好奇,对你来说沉默会不会比发声更有力量?
古尔纳:并不总是如此,不是说沉默总比发声有力量,但有时候沉默是唯一保存自我尊严的办法,因为你无依无靠,而发声不会改变你的情况,反而会让你更暴露于羞辱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是最合理的保全自我的方法。
然而另一方面,沉默也有其他的意味。如果你掌握着权势,想要压制他人,这时你想要的并不是沉默,你想要的是奴役、奉承和赞美,权势需要它们来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而沉默会引人联想,为什么这人不赞美、夸奖我?所以,沉默也意味着保守与防护,意味着我不会臣服于你,我不会这么说出来,但我保持沉默,在这个意义上沉默指向了一个人不愿为奴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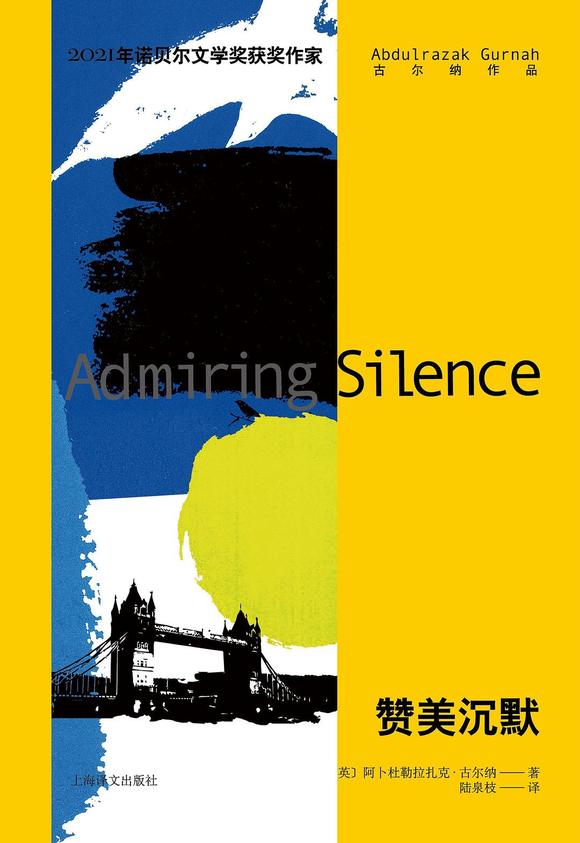
界面文化:在你的作品里,一个人的经历通常与经济有关,比如一个主角从贫穷渐渐变得富裕的过程。金钱或经济是理解你小说的一条线索吗?
古尔纳:可以这么说。金钱是通往权力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没有金钱,你会缺少力量,陷入赤贫,需要依靠他人。我感兴趣的是有权势、有金钱的人如何误用了他们的资源,如何控制他人——比如孩子和女性——的生活。金钱也可以是帮他人纾解困难的方式,金钱联系着权力。我对权力如何腐化很感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小社会当中。
我们乐于把自己看作谦良温和的人民。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罗人,我们毗邻而居,彼此相互争吵,有时也会通婚。文明人,这正是我们。我们乐于被这样描述,我们也这样描述自己。事实上,我们已不再是我们,我们待在各自的院子里,封闭在历史的贫民窟中,自我宽恕并且满心都是偏狭、种族主义和怨恨。
——《赞美沉默》
界面文化:你小说里的讽刺与愤怒的语调挺明显的,你如何定义你在小说里的声音?
古尔纳:我希望不止有一种声音,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语调。对我来说,这还是由写作题材以及叙事方式决定的。
比如《天堂》里的声音是有意味的、较为遥远的,并不是非常直接的,跟《赞美沉默》或者《来世》不同。《赞美沉默》更为愤怒,因为我写的是一个反抗自我处境的人。他看起来很失败,离开家园,婚姻崩溃,对周遭的压力怀有一团怒火,他的生活一团糟,但他没有承认这种一团糟的印象,他在反抗失败。
界面文化:还想听你谈谈身份问题。你之前说身份是“可协商的”,这是什么意思?
古尔纳:“身份”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词,因为它并不准确。“身份”暗示的是某种永远固定的、一旦到达就不会变动的东西,就像是买东西,有人说“这就是你的‘身份’,好了下一位”。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但如果要找到一个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是复杂的存在。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与父母兄弟见解相同,在另一些事情上存在分歧,我们可能会沉默,也不想陷入争吵。我们当然有相同之处,在社区内外皆是如此。
我们对自己的理解都是流动的、可变动的、可商议的,所以“身份”并不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果你去其他地方,作为陌生人,体验到家乡与陌生地之间的不同,这种感觉会加强,但不意味你就分崩离析了,并不是这里的你是你,那里的你就是另外一个人。
活着就是去学习、去商议你是谁、你了解什么、你发现了什么。“身份”暗示的是固定的东西,好像如果不依赖它就是背叛它一样,可实际上,你仅仅是学着生活下去。当然有时候人们会想要以身份来抵抗,如果外界对你具有敌意,你会强化自己的身份感,告诉自己我有更宝贵的东西并不在意外界,但那也意味着你对外界多样动态的选择关上了闸门,选择了向内而不是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