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幸福”概念的日渐崇尚,作为个人的“我”越来越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把不幸和无能归罪于自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今年3月,一条“中国人幸福感全球最高”的新闻登上热搜。民调机构益普索集团(Ipsos)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参与调查的32个国家中,幸福感指数最高的是中国(91%),其后是沙特阿拉伯(86%)和荷兰(85%)。美国和日本分别排在第14位和第29位。
中国人是怎么衡量幸福的?中国人的幸福感评价经历了从宏观标准到用数据说话的转变过程,在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幸福的概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随着对“幸福”概念的日渐崇尚,作为个人的“我”越来越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把不幸和无能归罪于自己。
德国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对古代中国人的幸福进行了描绘。他首先区分了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认为中国人更看重后者。在儒家观点中,个人不是由自己独具的内在特征界定的,而是由社会关系界定的,所以中国人的自我里常常包含着家庭、家族乃至整个社会。
中国人“幸福的本质及乌托邦的本质里,包含着某种悖论性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个人幸福要在社会幸福中实现,但是社会幸福的实现却可能会以个人的不幸为前提。鲍吾刚看到,纯粹追求个人幸福的学说也存在着,比如道家学派之一杨朱学说追求尽可能享受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快乐,但这类思想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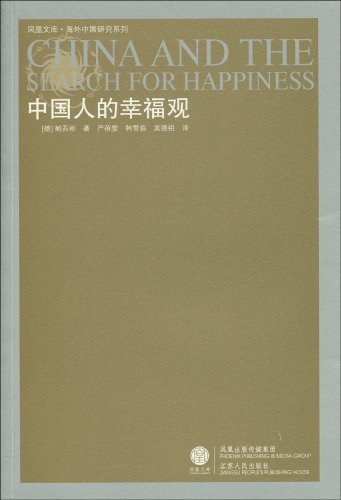
鲍吾刚还把中国人的幸福区分为此时此地的幸福和彼世的幸福。对现世幸福的热衷,追求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在儒家承诺的德治社会中非常明显,墨家崇尚的兼爱尚同也是渴望建立现实的理想社会。对彼岸世界的迷恋则体现在对道家隐士和神仙所在的世外桃源的向往。然而,即使是在道教里,长生不老也总是和现世享受绑定在一起,现世幸福终难舍弃。
2012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了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是:“你幸福吗?”一时间,“幸福”成为热词。
本世纪初,梁捷在《幸福指数》一书中看到,近些年来,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要素都在被数字化、科学化,“用数字说话”成为了人们的思维习惯。2006年,中国统计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幸福指数”的概念被提出。人们开始思考真正的生活质量,含含糊糊的幸福似乎结束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种工作虽然有简化幸福含义的嫌疑”,却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幸福的本质”。

为什么偏偏是幸福这个词最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不是其他的一些名词——公正、审慎、团结或者忠诚呢?或许这也与中国社会日益强大的个人主义思潮相关。《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的作者卡巴纳斯和伊洛斯就认为,幸福之所以在如今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中至关重要,原因尤其在于它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中,作为个人的“我”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诉求,集体和社会则被看成是不同独立意志的集合体:“通过自称科学的、中立的、不带有意识形态内涵的权威话语,幸福概念使个人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
1970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非常直白地写出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一家企业唯一的道德责任就是赚到尽可能多的钱。戴维斯写道,他们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自己去开一家公司,让它成长为未来的巨无霸。你在犹豫什么?是不是欲望还不够强烈?难道你没有这种战斗精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问题的是你,而不是这个社会。”对芝加哥学派来说,竞争不是要与对手共存,而是要彻底毁灭对方。
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这种理论在华盛顿迅速传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影响了许多国际上的监管者。而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并非人人都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主义、攻击性和乐观精神。对于不够“自我”的人,一种新的科学应运而生,那就是圣路易斯学派的精神疾病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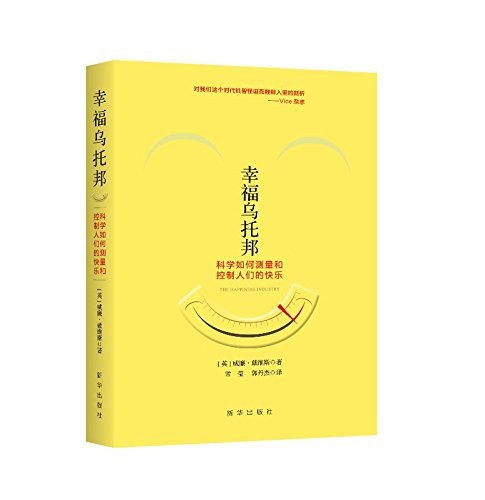
这一学派认为,精神疾病存在是因为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要用科学方法来观察和治疗,而不是进行社会学层面的解读。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使用了圣路易斯学派的理论,在其中,精神疾病成为了一种靠观察和分类就能够确定的病症,不需要任何关于起因的解释。
之后,越来越多的标准和度量被发明出来,帮助人们记录正面和负面的情绪。每个新工具和新研究的发表,都彰显出仅靠科学标准来理解他人感受的雄心。人们“希望不同形式的悲伤、忧虑、挫折、神经衰弱和痛苦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量表来衡量,从最低到最高依次标上量级”。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一个广泛的、个人的成长为最高目标的社会,广泛的、个人的精神崩溃就会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只认可乐观主义的文化会伴生消极主义的病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会让失败成为一种疾病……
在这样的社会中,感到不乐观、不幸福的人们该如何自处呢?没关系,你可以学习积极心理学。马丁·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习得性无助”实验中对一条狗持续进行电击,狗逐渐放弃了抵抗,只会低低地哀鸣,被动接受电击;即使后来很容易就能避开电击,狗也不会去尝试避开。这项实验撒下了积极心理学的种子,该学科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化的手段去抵消无助感。
在《真实的幸福》等著作中,塞利格曼向读者指出,过去的心理学多半关心心理与精神疾病,忽略了生命的快乐和意义,他想要校正这种不平衡,帮助人们追求真实的幸福与美好的人生。

在《真实的幸福》中,塞利格曼谈到,悲观的人很容易认为挫折和失败是永久且普遍的,而且全部是自己的原因;相反,乐观的人具有坚韧性,把自己面临的挫折看成特定的、暂时的、别人行为的结果。“悲观的人在学校表现比较差,在运动、工作上也是如此,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太好,寿命相对较短,他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好。”
但如果你不是天生的乐观者,该怎么办?没关系,塞利格曼讲述了“拉近幸福的六种美德”、“获得幸福的24个优势”等,认为只要使用“习得性乐观”的技术,你就可以振奋起来。《真实的幸福》这本书在全球畅销近20年,销量达到200多万册,指导人们获得幸福的类似作品如《哈佛幸福课》等也火爆全球。
在《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作者埃德加·卡巴纳斯和伊瓦·伊洛斯看来,“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玩味。在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行使和分配权力的过程中,在一些组织内部实施强制策略的过程中,在用墨守成规和麻木不仁来代替创新和反抗精神的过程中,无助、脆弱等情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习得性无助”的概念本来可以用来帮助理解社会再生产和转型机制,但塞利格曼却只是认为,成功是乐观主义的结果,失败、失业、阶级下滑都是糟糕的心理架构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性成为了一种专制态度,刻板地把人们的不幸和无能归罪于人们自己。人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当幸福学家断言,无论情况如何,包括流浪汉和妓女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积极的感情和美好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幸福这种意识形态是禁止社会批评的,它以现实原则的名义强制人们接受条条框框。“人民对社会变革的请愿、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往往来源于类似发怒或憎恨等情感。掩饰这种情绪,本质上就是在批判社会动荡背后的情感结构,认为它给社会带来了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