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个人的痛苦和大众的痛苦乃至人类的苦难建立联系,如何把对自己的关注升华为对苍生的关注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普世的意义,大江先生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2002年冬,莫言与大江健三郎在高密东北乡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编者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在日本逝世,享年88岁。
在2009年10月的演讲《我是唯一一个报信人》中,莫言讲述了与大江健三郎相识十年的友谊。莫言对大江健三郎的印象包括紧张、拘谨、执着、认真,害怕给人添麻烦等。莫言以大江曾引用的《白鲸》里“报信人”的典故,向人们阐释了他的创作原则,即将自己作为唯一的报信者来写作,这不仅要求写作者具有表达现实的勇气,更需要有追求真理、保存真相的信念。三年后,莫言也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在这次演讲的三年之前,莫言在2006年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对大江创作的评价,表达了对年过七旬的他勤奋创作的钦佩。莫言认为,支持大江健三郎持续创作的力量来源于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以及“唯一逃出来报信人”的责任与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从出生背景到创作原则,莫言在许多地方都觉得与大江健三郎相通,大江健三郎处理的问题也是莫言所关注和长期思考的。莫言注意到,大江健三郎在早期作品里调用了丰富的故乡资源,也在民间文化与民间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与官方文化城市文化相对抗的东西,但并没有一味地迷信故乡,而是对故乡的愚昧与保守做出了批评。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曾前往莫言家乡高密访问,见到了莫言笔下的故乡。
文 | 莫言
认识大江先生,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间,我们七次相逢,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大江先生毫无疑问是我的老师,无论是从做人方面还是从艺术方面,他都值得我终生学习,但他却总是表现得那样谦虚。刚开始我还以为这谦虚是他的修养,但接触久了,也就明白,大江先生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事实上许多人都不如他,但他总觉得自己不如人。他毫无疑问是大师,但他总是把自己看得很低。他紧张、拘谨、执着、认真,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因此,每跟他接触一次,心中就增添几分对他的敬意,同时也会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曾经私下里跟朋友们议论: 像大江先生这样,是不是会活得很累啊?我们认为,大江先生的确活得很累,但我们的世界上,正是因为有了像大江先生这样“活得很累”的人,像责任、勇气、善良、正义等许多人类社会的宝贵品质,才得以传承并被发扬光大。
2002年2月,我与大江先生在我的故乡高密,做过长时间的座谈。当时我说:“在您的《小说的方法》一书中,您讲到麦尔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您说这是您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饱含深意。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搞文学也好,做电影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这才是作家写作应该持有的态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是唯一的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有这种‘唯一一个报信人’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读不读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
事过七年,回头重读当年的对话,回顾大江先生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和许多果敢的行动,我感到有必要修正和补充我当年的话:正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报信人”,所以,我的声音、我的话,对于保存事物的真相,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这个“唯一的报信人”,既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又要有忠诚的品格。即便他的话遭到很多人反对,但他还是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出真相。

也是在那次对谈中,大江先生说:“文学的效用之一,就在于赋予孩子们和人们一种方法,比如说教给孩子们和人们如何克服恐惧,以及如何让人们更有勇气……我觉得饱含对人的信任这一点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是文学的使命……我就像冒险一样,把非常可怕、黑暗的世界当作大河流淌一般描写着。但是文学的支点是:文学不论描写多么黑暗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看最后来临的喜悦是什么。我觉得所谓文学,应该是以显示对人的希望、对人类社会的信赖为终结的……”
这七年来,大江先生身体力行着自己的话,他写出了好几本不仅仅是献给孩子,也是献给成人世界的书。在这些书里,他没有回避这个世界的黑暗和面临着的巨大危险,他一如既往地向人们提醒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惨剧,告诫着人们要防止历史重演过去的悲剧。同时,他也将他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未被魔鬼置换过的纯真儿童身上。他的声音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令人头脑清醒的声音,他的作品也是能让我们的心智变得冷静和健全的“醒世恒言”。
2006年9月,我与朋友通信时,曾以“老爷子”戏称大江先生。大江先生的年龄的确比我们大一些,但他的精神比我们年轻。从他的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他那颗灿烂的童心。尽管四周黑暗重重,但我们看到了那灿烂童心照耀处的光明。
文 | 莫言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大江先生不懈地创作?我想,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和“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的责任和勇气。大江先生经历过从试图逃避苦难到勇于承担苦难的心路历程,这历程像但丁的《神曲》一样崎岖而壮丽,他在承担苦难的过程中发现了苦难的意义,使自己由一般的悲天悯人,升华为一种为人类寻求光明和救赎的宗教情怀。他继承了鲁迅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牺牲精神和“救救孩子”的大慈大悲。这样的灵魂是注定不得安宁的。创作,唯有创作,才可能使他获得解脱。
大江先生不是那种能够躲进小楼自得其乐的书生,他有一颗像鲁迅那样疾恶如仇的灵魂。他的创作,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绪福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寻求的是“绝望中的希望”,是那线“透进铁屋的光明”。这样一种悲壮的努力和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更强化为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这让我联想到流传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海力布能听懂鸟兽之语,但如果他把听来的内容泄露出去,自己就会变成石头。有一天,海力布听到森林中的鸟兽在纷纷议论山洪即将暴发、村庄即将被冲毁的事。海力布匆匆下山,劝说乡亲们搬迁。他的话被人认为是疯话。情况越来越危急,海力布无奈,只好把自己能听懂鸟兽之语的秘密透露给乡亲,一边说着,他的身体就变成了石头。乡亲们看着海力布变成的石头,才相信了他的话。大家呼唤着海力布的名字搬迁了,不久,山洪暴发,村子被夷为平地。——一个有着海力布般的无私精神,一个用自己的睿智洞察了人类面临着的巨大困境的人,是不能不创作的。这个“唯一的报信人”,是不能闭住嘴的。

大江先生出身贫寒,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写作之初,即立志要“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几十年来,他对小说文体、结构,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试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又说:“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由此可见,大江先生对小说艺术的探索,已经达到入迷的境界,这种对艺术的痴迷,也使得他的笔不能停顿。
最近一个时期,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了大江先生的作品,回顾了大江先生走过的文学道路,深深感到,大江先生的作品中,饱含着他对人类的爱和对未来的忧虑与企盼,这样一个清醒的声音,我们应该给予格外的注意。他的作品和他走过的创作道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我将他的创作给予我们的启示大概地概括为如下五点:
对于大江先生的“边缘——中心”对立图式,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实际上还是故乡对一个作家的制约,也是一个作家对故乡的发现。这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大江先生在他的早期创作如《饲育》等作品中,已经不自觉地调动了他的故乡资源,小说中已经明确地表现出了素朴、原始的乡野文化和外来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峙,也表现了乡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双重性。也可以说,他是在创作的实践中,慢慢地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中天然地包含着的“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在上个世纪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大江先生一方面用这个理论支持着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他又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地证明着和丰富着这个理论。他借助于巴赫金的理论作为方法论,发现了自己的那个在峡谷中被森林包围着的小村庄的普遍性价值。这种价值是建立在民间文化和民间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是与官方文化、城市文化相对抗的。

但大江先生并不是一味地迷信故乡,他既是故乡的民间文化的和传统价值的发现者和捍卫者,也是故乡的愚昧思想和保守停滞消极因素的毫不留情的批评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创作,更强化了这种批判,淡化了他作为一个故乡人的感情色彩。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出现了边缘与中心共存、互补的景象,他对故乡爱恨交加的态度,他借助西方理论对故乡文化的批判扬弃,最终实现了他对故乡的精神超越,也是对他的“边缘——中心”对立图式的明显拓展。这个拓展的新的图式就是“村庄——国家——小宇宙”。这是大江先生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他的理论,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文学,具有深刻的意义。他强调边缘和中心的对立,最终却把边缘变成了一个新的中心;他立足于故乡的森林,却营造了一片文学的森林。这片文学的森林,是国家的缩影,也是一个小宇宙。这里也是一个文学的舞台,虽然演员不多,观众寥寥,但上演着的却是关于世界的、关于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戏剧。
大江先生对故乡的发现和超越,对我们这些后起之辈,具有榜样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与大江先生相同的道路。我们可能找不到自己的森林,找不到“自己的树”,但我们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高粱地和玉米田;找不到植物的森林,但有可能找到水泥的森林;找不到“自己的树”,但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图腾、女人或者星辰。也就是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来自荒原僻野,而是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血地”,找到异质文化,发现异质文化和普遍文化的对立和共存,并进一步地从这种对立和共存状态中,发现和创造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共寓一体特征的新的文化。
大江先生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日本“私小说”的元素,当然这些元素是与西方的文学元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大江先生的小说,无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个人的体验》,还是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还是近年来的“孩子系列”,其中的人物设置和叙事腔调,都可以看出“私小说”的传统。但这些小说,都用一种蓬勃的力量,涨破了“私小说”的甲壳。他把个人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隐秘情感,放置在久远的森林历史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广阔背景与国际国内的复杂现实中进行展示和演绎,从而把个人的、家庭的痛苦,升华为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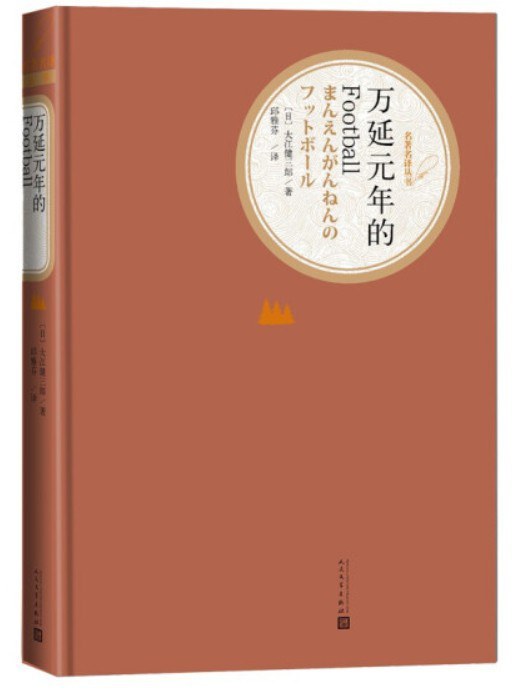
正像大江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叙述方式,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我还认为,通过对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带给我和我的家庭的神秘感和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其实,所谓的“私小说”,不仅仅是日本文学中才有的独特现象,即便是当今的中国文学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类似风格的作品。如何摆脱一味地玩味个人痛苦的态度,如何跳出一味地展示个人隐秘生活的圈套,如何使个人的痛苦和大众的痛苦乃至人类的苦难建立联系,如何把对自己的关注升华为对苍生的关注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普世的意义,大江先生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小说都是“私小说”,关键在于,这个“私”,应该触动所有人、起码是一部分人内心深处的“私”。
十九年前,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过一段名人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但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界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一个问题。我们承认风花雪月式的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但我们更要承认,古今中外,那些积极干预社会、勇敢地介入政治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并发挥巨大的教化作用。文学的社会性和批判性是文学原本具有的品质,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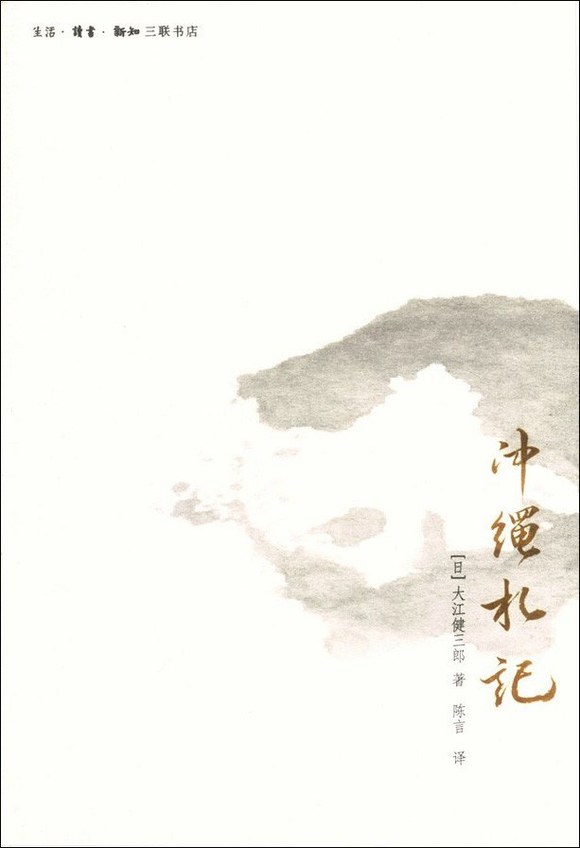
在这方面,大江先生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做出了有益的启示。大江先生的鲜明政治态度和斗士般的批判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小说落入浅薄的政治小说的俗套,他没有让自己的小说里充斥着那种令人憎恶的教师爷腔调,他把他的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诉诸人物形象。他不是说教,而是思辨;他的近期小说中,存在着巨大的思辨力量,人物经常处于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是真正的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复调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他把他的小说舞台设置在了他的峡谷森林中,将当下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和对照,他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和小说主人公家庭成员同台演出;于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从文学的意义上,这里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如果世界上允许存在一个中心的话。
去年,我曾经为我的读比较文学的女儿设计了一个论文题目:《论世界文学中的孩子现象》。我对她说,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世界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孩子为主人公,或者以儿童视角写成的小说。这种小说,已经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的成长小说,而是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文化背景,塑造了独特的儿童形象。譬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利《饥饿的路》中那个阿比库孩子阿扎罗,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中的萨利姆·西奈,中国作家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那个白痴,以及我的小说《四十一炮》中那个被封为‘肉神’的孩子罗小通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那个始终一言不发的黑孩儿。我特别地对她提到了大江先生最近的“孩子系列”小说:《被偷换的孩子》中的戈布林婴儿、《愁容童子》中的能够自由往来于过去现在时空的神童龟井铭助。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在小说中描写孩子?为什么这些孩子都具有超常的、通灵的能力?为什么这么多作家喜欢使用儿童视角,让儿童担当滔滔不绝的故事叙述者?为什么越是上了年纪的作家越喜欢用儿童视角写作?小说中的叙事儿童与作家是什么关系?我女儿没有听完就逃跑了。她后来对我说,导师说这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她的硕士论文用不着研究这么麻烦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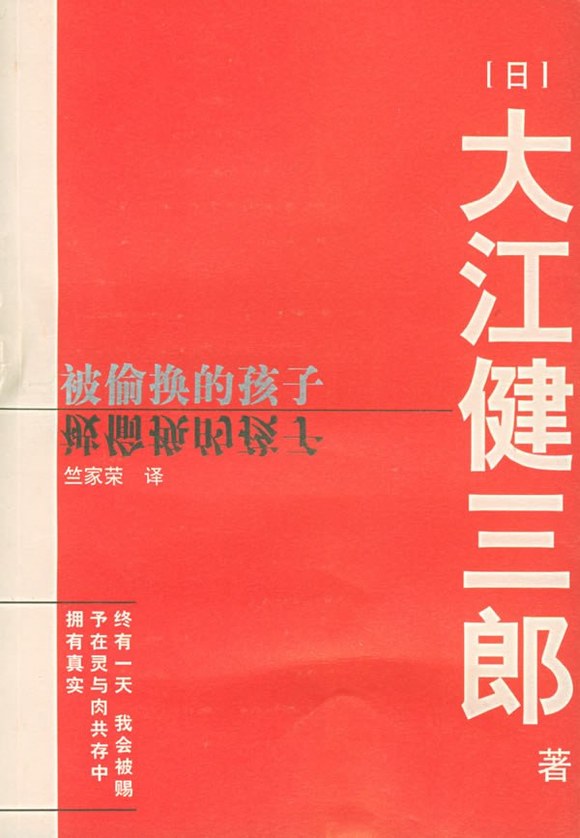
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很难理解大江先生“孩子系列”作品中孩子形象的真意,但幸好大江先生自己曾经做过简单阐释,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钥匙。
大江先生在《被偷换的孩子》中,引用了欧洲民间故事中的“戈布林的婴儿”。戈布林是地下的妖精,它们经常趁人们不注意时,用满脸皱纹的妖精孩子或者是冰块做成的孩子,偷换人间的美丽婴儿。大江先生认为他自己、儿子大江光和内兄伊丹十三都是被妖精偷换了的孩子。这是一个具有广博丰富的象征意义的艺术构思,具有巨大的张力。其实,岂止是大江先生、大江光和伊丹十三是被偷换过的孩子,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没被偷换过呢?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那么,谁是将我们偷换了的戈布林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戈布林的象征,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那些将我们偷偷地置换了的人,自己不也早就被人偷偷地置换过了吗?那么又是谁将他们偷偷地置换了的呢?如此一想,我们势必跟随着大江先生进行自我批判,我们每个人,既是被偷换过的孩子,同时也是偷换别人的戈布林。
大江先生在他的小说和随笔中多次提到过他童年时期与母亲的一次对话,当他担心自己因病夭折时,他的母亲说:“放心,你就是死了,妈妈还会把你再生一次……我会把你出生以来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还有你做过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讲给他听,而且新的你也会讲你现在说的话,所以两个小孩是完全一样的。”我想,这是大江先生为我们设想的一种把自己置换回来的方法。大江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第二种把自己置换回来的方法,那就是像故事中的那个看守妹妹时把妹妹丢失了的小姑娘爱妲一样,用号角吹奏动听的音乐,一直不停地吹奏下去,把那些戈布林吹晕在地,显示出那个真正的婴儿。
我们希望大江先生像他的母亲那样不停地讲述下去,我们也希望大江先生像故事中那个小姑娘爱妲一样不停地吹奏下去。您的讲述和吹奏,不但能使千千万万被偷换了的孩子置换回来,也会使您自己变成那个赤子!
文摘部分节选自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经授权后发布,段落有删节,小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