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带来体面感或趣味的体力活,不仅是那些对体力要求不那么大的“轻体力活”,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能够在现行经济制度中得到优质回报的劳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75期主持人 | 尹清露
“好多年来,人们把读书的目的设置为一份惹人艳羡的白领工作,可是,焦虑、抑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生活的终极目标难道不是开心吗?”
这段话来自豆瓣小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创建于2022年11月,短短几个月已经拥有两万多名成员,年轻网友们在组里求师问道,希望降薪辞职去做不费脑子的体力工作,其中不乏一线大厂员工。此外,更多人选择在主业之余探索一份副业,既给生活找一个喘息的空间,也多一个赚钱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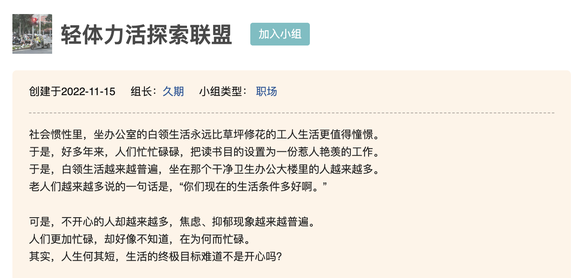
想做体力活的理由很多:为了摆脱长时间思考以及神经紧绷的折磨,试图在体力劳动中找寻类似冥想的“心流感”和“内心的平静”,这也是为什么收纳整理师是组内呼声最高的职业之一,近藤麻理惠就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中提到过:“不用特意游玩山水,在家动手整理就能体验到瀑布修行的快乐。”也有备受艳羡的口腔科医学生看不到就业前景,索性放弃职业规划去做保洁员,表示自己“真的喜欢理东西,也不怕脏”,这些例子似乎说明,我们对理想工作的标准正在发生松动和改变。
实际上,大多数人期待中的体力活是不太累又要有足够尊重的体面工作,比如宠物理发师和瑜伽老师,分拣快递或者保安这种工作则要“离得远远的”。也有不少人给体力活戴上天真的滤镜——有人爱吃某品牌的零食,就想去那个公司打工,结果被提醒那可能是“一家压榨人的企业”;有人辞职去连锁咖啡店工作,以为可以逃离办公室的繁琐工作,却要受制于机械劳累的操作流程和超高的客流量。这一方面折射出我们不了解体力劳动的现实——它大概率又苦又累,没有田园牧歌风情,且同样会在工业体制下被异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脑力打工人与体力劳动者的疏远和陌生,他们往往疲于谋生,并没有太多选择。
叶青:前段时间农村田园生活视频特别流行,视频中呈现出的多是轻松从容、远离喧嚣的生活方式,许多在一线城市从事繁忙工作的年轻人会在这类视频中寻找慰藉,不少人在评论区表达了向往。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爱看这种视频,但其中多少有一些对农活的美化和幻想。看似独立完成且信手拈来的农活其实通常是团队合作的成果,有过种地经验的人想必都知道,这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劳动,对体力也有一定要求,在烈日下辛苦劳作半天后是绝不可能像视频中那样妆容完整还大气不喘的。
我小时候也对农活很感兴趣,觉得长辈们在农田里一边插秧一边聊天有趣极了,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难度,闹着要一起“玩儿”,但下田后才知道这完全不是什么我想象中的趣事。田里满是淤泥,插秧过程中泥水溅得浑身都是,并且全程都得弯着腰,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姿势,不一会儿就腰酸得不行。实在佩服长辈们还能一边劳作一边闲聊,我累得只想赶紧找借口放弃。
林子人:真正的农村生活当然不同于视频中的田园牧歌幻想,这是李子柒在收获了全球粉丝的同时,也招致不少人反感的重要原因。前两日读《克拉克森的农场》,看一个当红汽车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一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暴躁老头如何突发奇想去当农场主,乐得不行。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克拉克森提醒读者注意木工不是那么好做的——我们以为电锯很拉风帅气上手又很简单,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锯子启动之后你会发现,操纵电锯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你会感到超级恐怖,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它随时都可能脱离你的双手,反过来锯掉你的脑袋。于是你小心翼翼地拿着它走向你准备开刀的那棵树,下一秒你却掉进了獾的洞穴。因为地上长满荨麻,你根本看不清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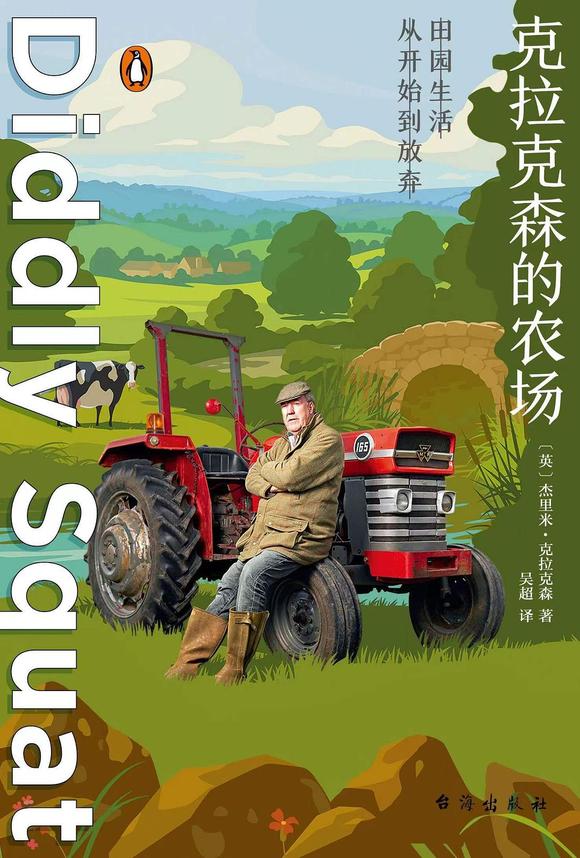
据说讲述他农场生活的纪录片非常受欢迎。我想这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很微妙地满足观众心理的叙事角度:它向你展示一个此前毫无务农经验的都市人(恰如很多正在观看这部纪录片的观众一样),在面对真正的农村生活时会出多少令人忍俊不禁的洋相,同时又告诉你,虽然做农活很累很操心,但它切切实实在“创造”一些东西(食物),确实能让你获得一种简单的快乐。
潘文捷:看音乐会如果遇到全体起立,大家会觉得音乐家好成功。但是你知道吗?演奏家演奏结束,大家站起来鼓掌,倒不全是因为演出太棒了,也可能是因为坐太久了,想要活动活动。这件事是《久坐危机:如何让你更愿意动起来》的作者彼得·沃克谈到的。在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的工作和快递员工作之间,沃克自己选择了后者。他每天骑车在伦敦派送文件,每天要骑行八九十千米,随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骑车速度变快了,耐力增强了,腿部还有了肌肉,还不知不觉中摆脱了身体虚弱的旧形象,给了他一种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的快乐感。

如今,日常活动的减少是在城市中全面发生的。我们身处于一个久坐不动的世界,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可怕的威胁。越来越多人对“轻体力活”的向往,当然是对现今工作环境的有力质问。可其中也不乏一些天真的幻觉成分,比如说,我也曾经想过一些体力活儿会不会比坐着的工作好一些,比如说送餐送快递,想必可以缓解久坐不动导致的问题。后来发现真是想多了——北京的快节奏送货甚至不会允许你骑自行车,大家都是骑着电动车飞驰,速度变得更重要,倒计时给人压力骤增,为了赶时间,逆行、撞车等问题屡见不鲜。
董子琪:昨天一下子与三位师傅同时打交道,一位是帮忙抬家具的,一位是负责装柜子的,还有一位是专门来丢旧家具垃圾的。有一个时间点三位师傅齐聚,他们彼此毫不相干,谁也不认识谁,各忙各的,但却有一些有意思的交互,丢家具的师傅看见装家具的师傅在找地方摊平木板,问要不要帮忙抬起来,于是他俩合作把餐桌和沙发都挪开,还互相问候对方老家哪里,大家都很乐呵。虽然不构成竞争关系,能看出来还是略微有点差别——装柜子需要技术,收入也高一些,师傅性格更沉稳;丢家具的师傅似乎更为开朗,头发已经白了,活也最辛苦琐碎,搬死沉的家具上楼下楼这件事需要一点野蛮的肌肉与精神。听见楼道口低闷的吭吭声就知道了,他所做的是让这些旧东西消失,回到空无一物的状态,可是空无一物竟然是要这么拼命才能实现的。看到了这些,就不太相信体力劳动放松身心,甚至是相反的,体力劳动是为了人们放松身心地享受但最好无声无息像从来没存在过似的。
尹清露:体力活无法放松身心甚至相反,这让我想起“轻体力”豆瓣小组里有人说,只要有搬东西的机会都会很开心,因为可以当做健身锻炼,但如果单纯是为了生计而劳动呢?我高中暑假做过大卖场的冷饮售货员,要推着货物在电梯间奔波,全天站立外加大喊“欢迎试喝”,于是发明出不太累发声技巧,“欢迎”二字语调向下,“试喝”二字语调向上,听上去果然很像餐厅服务员惯用的语气——那是当然,因为这样就是最省劲儿的方法。

董子琪: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经说,很多白领大概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不是重要的以及成果是什么样的,而人们的天性就是想要影响世界、看到结果。亲力亲为的体力活,比如种地,就是一个能看见结果的诚实劳动,它可能会帮白领洗刷掉一种假装在做事的愧疚感,减轻心理的负担?
先不说体力活有多么复杂细致,从《劳动者的星辰》里我们能看到,那些普通的活计,比如漏粉条、种植棉花,都需要长久的经验,那些构成经验的名词好像都能成为一门语言。真实地从白领工作切换到体力工作,一个人所感受到的心理落差想必也很大——你是否能真的放弃对于穷达贫富的考量呢?陶渊明“聊为陇亩民”并不是真的变成了农民,真的变成农民也没必要以陶渊明的视角来写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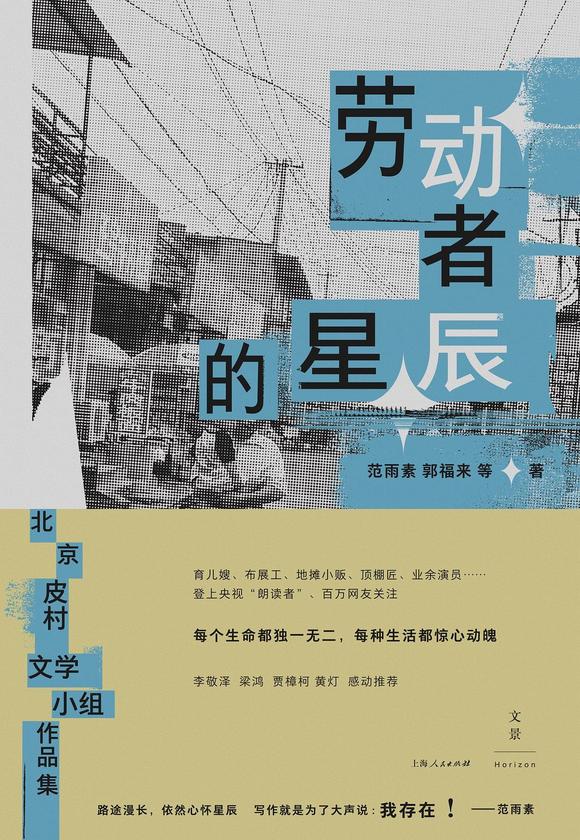
徐鲁青:我很认同“看见结果”对人心的安慰,如果把和身体行为紧密连接的工作看作体力活,那织毛衣是体力活,做木工是体力活,再往前推一点,其实做雕塑、画油画都可以算体力活。但在很多人眼里,它们和送外卖、流水线拼装这些工作又是不一样的。细想起来,这是不是创造的可见性的区别?做饭赚外快的女孩喜欢的是和顾客创造的一段段直接关系,大厂下班搞缝纫的年轻人看到的是自己做的成衣,他们在大厂感受不到每天加班创造出的结果——机器太大了,我怎么知道我做的那一部分真的有任何意义?
能放松的体力活往往是流水线的反面,人不隐蔽在机构之内,不作为流程图的一部分,个人直面物件,个人直面个人。格雷伯便认为自由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对一件事情感到有掌控能力,我们在工作里得到的快感不是投入精力少而获取多,更多来自于发现自己有改变什么的能力。体力活的这些特点都挺明显的。
不过也有一些时候,放松是因为投入的精神价值少,同时成效立见。我洗过一些盘子也送过一些外卖,最大的解压之处在于没什么意义寄托,比起办公室工作更能感到是实打实的交换,我的行为就是交换筹码的全部,不带任何精神附加值,不会为做不好一件事怀疑自我价值。很多人提到的体力活“不用想太多”,估计就是这个层面。
林子人:辞职去做体力活倒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多年前出于好玩的心态去上过一节木工课,大概花了一天时间做了一只木盘。当时木艺工坊刚刚在杭州兴起,工坊提供很多零基础木工课程,颇受年轻白领欢迎。2016年我写过一篇特写报道《发现杭州“创艺青年”:做一番有趣的事业并以此为生》,其中就采访了这家木艺工坊的联合创始人。他原本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木艺是他工作之余的自娱自乐,但因为感到工作压力太大、缺乏成就感,他就干脆辞职创业了。他教对木艺感兴趣的人如何做木工,有一位学员甚至也因此走上了木艺的道路,开创了淘宝上声名鹊起的家居品牌。

在那篇报道里我采访了几个类似的脱离“正统”白领职业发展路径,去做和“手艺”相关的事的人。现在回头再看,感到那些采访对象可能和现在豆瓣小组里探索“轻体力活”的年轻人在心态上有些区别。但不变的是,给人带来体面感或趣味的体力活,不仅是那些对体力要求不那么大的“轻体力活”,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能够在现行经济制度中得到优质回报的劳动。
在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威胁白领工作的可能性陡然提升的当下,办公室工作和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模糊——毕竟两者都有被机器取代的风险——但也有研究发现,那些和“对人的服务”相关的工作是最难被机器取代的,比如小学老师、老年人的照护人员等。但我们会发现,在现行经济制度中,这些人群的报酬和他们的工作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我们对体力劳动的偏见甚至污名化,可能正是因为如此。
日本学者广井良典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中提出过一个我印象深刻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了劳动力过剩(慢性失业)、资源不足的困境,为此我们应该改变“生产率”的定义,从劳动生产率(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转向环境效率,即积极地使用人力劳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及环境负荷。广井良典指出,生产率的概念发生如上转变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本被认为“生产率低下”的、对人服务的领域,变成了生产率最高的领域。结构性的社会变化将表现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将逐渐转向服务和人与人的关系(或‘关怀’),以人为核心的劳动密集型领域必将走上经济的中心舞台。”如果那样的未来真的成为现实,我们对做体力活残余的顾虑与偏见,应该也会消失殆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