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的政治学》敦促我们思考:为什么宣称追求尊严和尊重的人会持续地以羞辱他人为乐?羞辱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群共享同一道德规范的观众。

第74期主持人 | 潘文捷
1999年出生的女孩郑灵华去世了,她更广为人知的一个称呼是“粉发女孩”。就在2022年7月,郑灵华保研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医院,和病床上的爷爷分享这件喜事,并且拍摄了照片与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留念。万万没想到,仅仅因为她染了粉色头发,这条动态一下子“火爆”起来,一时间,“陪酒女”、“夜店舞女”、“红毛怪”等脏水不由分说地泼向了她;有人说“染发的都不是好人”,有人骂“你那头发简直丢华东师大的脸”,甚至有人指责她不该拿爷爷炒作,“老爷子走慢了”……许多网络账号盗取了这张照片,肆意歪曲事实,有人造谣说这是“老人带病考取研究生,还娶了一个小女生”。事发后,郑灵华试图卸载这些社交平台,把头发染黑,她没有放弃取证,决意进行反击。但是谣言和讥讽带来的伤害使她患上抑郁症,并在今年因抑郁而自杀离世。
近年来,网络暴力导致自杀的事件屡屡发生。根据联合国《网络欺凌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一文,“网络欺凌”概念经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但实际上它是欺凌这一旧问题的延伸,“欺凌来自社会中潜在的偏见和歧视,对那些具有种族、宗教、性、性别认同和残疾等受保护特性的人影响最大。”
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称自己被“网暴”却难以获得舆论同情。例如,在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中,刘鑫说过去五年持续的网络暴力让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希望网友帮忙募捐赔偿款,而她的“网暴”遭遇并没有获得很多人的同情。去年,有网友称中国量化投资协会理事长丁鹏在微信群发表骇人听闻的言论,称对儿子的期待是“不要求发财,只要求儿子多上几个女人”。这一言论被散布后,丁鹏遭到不少批评,随后他在微信群中称:“都是一棒子女人受不了了,微博上网暴我。”(注:截图显示其原文中使用的就是“棒”字)表明自己成为了“网暴”的受害者。所以,关于“网暴”的经验不被认同,或“网暴”被作为一种标签使用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概念?
尹清露:郑灵华拥有一头超级漂亮的粉色头发,粉色既代表甜美和柔弱,也代表出格和叛逆;一方面是由男性施加的理想化样貌,另一方面却又被女孩拿来,挪用为发挥创造力的有效工具。《粉色:关于朋克、美丽和力量的历史》的作者就认为,粉色一直是一种“过渡性”的复杂颜色,意义摇摆于尊贵和媚俗、温顺和越轨之间。而当本应该“乖乖待在它属于的地方”的粉色(比如衣服,同时不能太暴露)出现在了头发上,那个温顺的女孩形象竟然就拥有了令人不安的力量,甚至让某些喷子担忧“这还怎么为人师表”。

这也是大家称郑灵华去世的悲剧为“又一场猎巫运动”的原因,女性应该负责治愈和教育,女巫则通过烹饪毒药颠覆了女性的基本职责,但为什么老师就一定要是循规蹈矩的样子?进而言之,为什么老师就一定要按照框架去教那些“不会引起恐慌的东西”?从这次网暴事件开始,值得思考之处还有很多。
在几年前,我采访了某位偶像的已经脱饭的粉丝,一些粉丝不认同那位受访者的观点,所以那篇文章惨遭围攻,也有几个人跑到微博上来骂我和受访者。仅仅是这种程度就已经感到心有余悸,实在难以想象郑灵华面对这样的遭遇该有多痛苦。我当时的做法是“试图表现得云淡风轻”,甚至给骂我的那条微博点了赞——好吧你说的都对,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我也深知这种方法在面对更汹涌的恶意时根本无力招架,网暴者敲完键盘就拍屁股走人了,只留下恶意飘荡在当事人头顶。为了保证身心健康,不被喷子摧毁,也许我们还是不要封闭自己从而走上恐惧的漩涡,多和亲友联络,多从他们口中得知自己真实的样子,应该会有所帮助。

叶青:我有限的(被)网暴经历都来自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是因为人在竞技时戾气会特别重吗?我发现再小的事情都会引起某些队友的不满,因而对你进行辱骂,而且往往都发生在我选择了女性英雄、被当成了女性玩家的时候。比较初阶的就是说“女的就是菜”,更过分的会上升到人身攻击,打出一些全是和谐符号***的字眼。在这种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开麦和对方交流几句,也很奇怪,对方在听到我是一名成年男性,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小女孩时,又常常突然间开始走爱与和平路线,称兄道弟,仿佛上一秒和我对线的网络喷子不是他一样。
潘文捷:在我看来,同样是称自己受到网暴,其中的差别是巨大的。比如说,丁鹏引发众怒的言论和刘学州受到网暴的情况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财经杂志-财经E法》的《少年刘学州之死:我们该如何制止网暴?》一文中,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看到,对于刘学州来说,他“既有一个现实身份,也有一个网络身份”,两种身份在生活中密不可分,因此,网络信息对他的现实生活构成直接影响,刘学州自述因在网上公开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图、被“一些颠倒黑白的人说要求买房子”等经历,而遭到网络暴力,可见,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缺少亲人关爱的他来说,网络上的说法影响很大。
但是对丁鹏这样的人来说,他除去中国量化投资协会理事长一职以外,还是CCTV特邀嘉宾、第一财经《解码财商》资深解码人、《财经》《财新》《中国金融报》等媒体的撰稿人,担任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他在现实身份中的地位难以撼动,从泄露的群聊消息看,即使是在遭到批评之时,他的社交圈里还是不乏支持他观点的男男女女。这也意味着,对于丁鹏这样的特权人士来说,人们似乎只能在网络上发起舆论攻击“口诛笔伐”。

林子人:网络暴力毫无疑问是一种日益严峻的社会现象。在我看来,网暴的本质是一种由社会焦虑作祟引发的“越轨指控”。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两三年经济压力增加放大了社会焦虑,让人们对所有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判断的他人都有了更强的抵触和反对心理。我在评论“佛媛”、“病媛”事件时曾援引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中的观点:
“广泛性的社会偏见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息息相关。当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每个社会成员被允诺潜在平等,被鼓励通过努力和好运实现向上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激励与恐慌,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加速崩坏的情况下,那些对个人境况不满的人更容易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偏见。‘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而来的焦虑感增加,使得人们倾向于将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替罪羊。’在社会失范时期,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被感知的竞争会被夸大,不满之人由此产生敌对心态和攻击冲动。奥尔波特认为,为了保持社会的核心稳固,大多数社会都会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鼓励公开表达对特定‘女巫’群体的敌意,以此充当公众发泄情绪的安全阀门。15世纪的欧洲社会和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公开鼓励人们猎巫即为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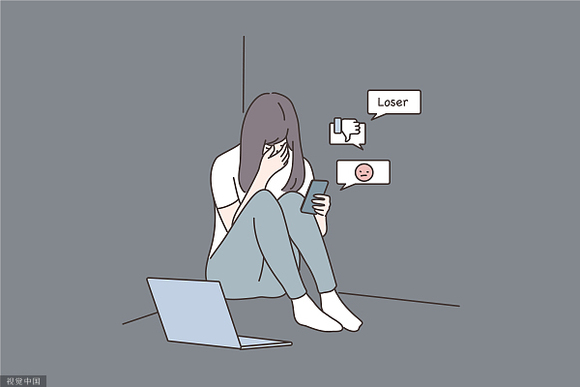
不少研究者认为,社交网络是一台“炒作机器”,有时会放大现实世界中原本只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恶意。美国学者詹姆斯·道斯在《恶人》中提醒我们,注意身处群体之中对个人思考和道德判断的负面影响。道斯认为,我们在群体中倾向于采取更极端的意见,对其他群体更容易产生竞争心理,更倾向于简单的解决方法而非好的解决方法,更容易随大流、聚焦在大多数人已经熟悉的信息,而不理会只有少数人提出的新信息。
更糟糕的是,我们会更注意陌生人的负面信息而非正面信息,对他者坏行为的反感强于对他们好行为的好感,更容易对他人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而且负面刻板印象的产生比正面刻板印象的产生所需的信息更少。
“在我们焦虑或缺乏安全感时,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当我们处于这些情绪状态中时,会更容易把别人刻板印象化,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私(in-group favoritism),认为内群体的成员比其他群体成员拥有更好的品质,更容易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专找比我们差的人进行比较来安慰自己)。”
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会专挑符合我们既有信念的信息,过滤掉那些对既有信念构成挑战的信息,并且否认现实——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许多网暴者在事后不仅拒绝道歉,而且幸灾乐祸。
徐鲁青:我没有被网暴过,但我和身边的人都有过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在网上发言需要特别小心,这种小心又不是逻辑严谨意义上的,更多时候是一种情绪、一种语气。写文章也是,做判断的时候总要加很多副词,可能、或许、似乎,这当然会更周全严密,但大多数时候反方观点横冲直撞,不怕举报,被质疑就反扣道德帽子。
网暴很常用的话术是以阴谋论揣测发言者动机,批评《流浪地球》就是“别有用心”,写环境问题就说“白左的走狗”。全嘻嘻的事也是网暴,揪着一个女性声讨她软弱的地方。
这几年很明显能感到精彩的、观点鲜明的评论性文章越来越少。我有段时间沉迷于早期的《锵锵三人行》,太好看了,不只是话题,还有话语场的氛围,每个人都立场鲜明、论据充分。原来在举报和网暴还没有泛滥的时代,公共对话可以是这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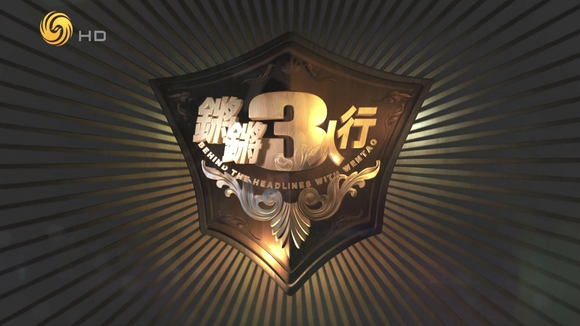
董子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豆瓣小组评论区也变得不太友好,即使是探讨学术问题的帖子,下面也能偏离主旨吵起来,好像本来要拉近人们关系、邀请人们分享生活的社交网络,变成了彼此构陷的方便之所。但是,难道不能讨论吗?难道不能发言吗?难道不能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在想浏览大家对一张摇滚乐专辑的评价时,如果看到太多乐手品行的点评会觉得有点苦恼,苦恼的不是意见不好,而是噪声如山呼海啸。可是,噪声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的象征吗?噪声中不也会诞生出美妙的乐章吗?原来也会觉得更激烈的讨论能彼此激发,经历了许多噪音极大的讨论,不由得对所谓的直抒胸臆保持警惕,很多发言看上去是非常正义的,只是这些正义的理由也相当地具有迷惑性,甚至能蒙骗了自己,我自己又何尝没有被自己的正义感蒙蔽过呢?声张正义与宣泄不满,要求平等与倾泻嫉妒之间的种种界限,是不是模糊的、难以察觉的呢?或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当代社会人们追求的是平等激情而非优越激情,正因为人们知道在网络上人与人的声音都是平等的,所以大家要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展现自己的智慧,可这难道不会将人们导向对自己声音以及力量的迷醉?
潘文捷:乌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的书《羞辱的政治学》敦促我们思考:为什么宣称追求尊严和尊重的人会持续地以羞辱他人为乐?她告诉读者,羞辱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群共享同一道德规范的观众。一旦相应的道德规范遭到拒斥,羞辱的极端残酷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可见,虽然“要求儿子多上几个女人”的言论本来会羞辱女性,但如果当下的人们并不吃这一套,反而一致反对和声讨这种厌女言论,那么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就会感到被羞辱。如果在郑灵华遭到网暴的时候,更多人并不认为染发有什么问题并为之发声,也可以保护到被羞辱的当事人。
林子人:作为一个曾经遭遇过网暴的过来人,我最重要的经验是“不要责备自己”,陷入“为什么被网暴的是我”的思维泥潭里。了解网暴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在遭遇网暴的时候保持理智——你要知道,绝大多数网暴者实际上是缺乏理智的,他们甚至对你本人一无所知,他们对你的批评不对你的身份认同、个人价值构成任何有意义的评价。
能举起法律武器与网暴者“正面刚”,当然值得鼓励,这有助于净化网络风气,但这样做的确对被网暴者的心理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你觉得你无法承受这种心理压力,也不要苛求自己,断网一段时间,在线下生活的社会联结中汲取力量与支持。网暴就像龙卷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会没事的!而对所有有基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来说,下一次因为某个原因想对网络上的陌生人口出恶言之前请三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