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槟榔相关的话题——包括国家对槟榔产业的管控角色、槟榔在近10余年的扩散状况以及其可能的未来——我们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味蕾背后复杂的历史、阶级与性别问题。

槟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9月10日,歌手傅松因口腔癌去世,“36岁歌手嚼槟榔6年因口腔癌过世”的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傅松生前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的口腔癌是由槟榔诱发,并呼吁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槟榔”,他的去世也让禁售槟榔的呼声再度在舆论场中响起。
这不是槟榔第一次登上热搜。今年8月,一则以“槟榔在土耳其列为毒品”的新闻传播甚广,而早在三年前,《千亿“软性毒品”槟榔,和正在上瘾的6000万中国人》一文就曾引起关注,槟榔致癌问题一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些备受热议的槟榔,大多是在2000年以后来自湖南湘潭的包装干制槟榔,分布在街头巷尾的小卖店,消费人群大多是客货运输司机、夜班工人及电竞从业者等。饮食人类学家曹雨发现,槟榔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中国人食用,在漫长的历史中几起几落,与之相伴的是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变迁。

自称“吃货”的曹雨,在从事学术工作后以自己最大的兴趣——食物——作为研究对象。2019年,他写作《中国食辣史》,探讨了四百年间辣椒在中国作为食物的演变历史。书成之后,曹雨开始关注槟榔,他的母亲是湖南人,回老家时常看到亲戚嚼食槟榔。曹雨发现,槟榔在中国的食用历史颇为悠久,而学界从未系统研究过这种小小的青色果子。它在饮食文化中的阶级属性、文化属性是如何随历史变迁而变化的?为什么是烟草、咖啡、茶叶这些嗜好品行销全球,而槟榔只能屈居于亚洲一隅?未来槟榔有没有可能成为流行全世界的嗜好品?
在《一嚼两千年》出版之际,界面文化(booksandfun)连线采访了曹雨。除了槟榔相关的话题——包括国家对槟榔产业的管控角色、槟榔在近10余年的扩散状况以及其可能的未来——我们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味蕾背后复杂的历史、阶级与性别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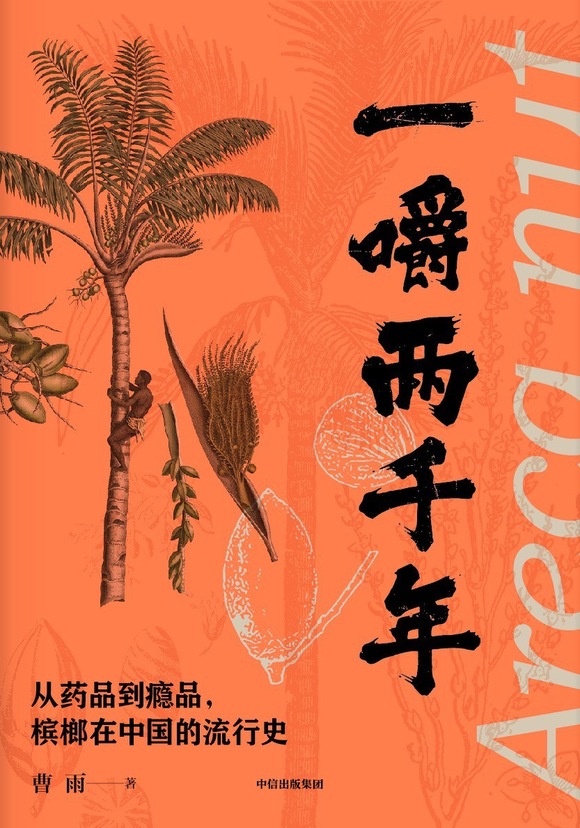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之前研究中国人吃辣的历史,作品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这一次研究的槟榔好像更小众一点,甚至很多人从没见过。你觉得槟榔的研究价值是什么?
曹雨:做槟榔研究的人不多,现有文献很少,所以是有初始价值的,特别是大部分有很大意义的食物——比如说茶——已经被研究过了。另一个原因也是使命感驱动,研究需要对槟榔文化圈的文献相对熟悉,能够做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人,历代以来对槟榔做出细致研究的都是广州人。
界面文化:你观察到喜欢嚼食槟榔的大多是客货运输司机、工厂夜班工人及电子竞技从业者。很多地区售卖槟榔的店铺集中于加油站、汽车维修厂、物流货场、工厂区域和大型网吧附近。槟榔食用上有很集中的职业(或者说阶级)特征,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样的食物更容易出现阶级分化?
曹雨:槟榔有显著的提神功能,可以帮助体力劳动者工作。功能性特征显著后就会出现阶级上的固化,一个人嚼槟榔的时候旁边的人可能会说,你怎么有这么体力劳动者的习惯,然而出现阶级区分。这是槟榔在现代中国社会分化中产生的符号象征,但在古代则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嚼槟榔的人最开始贵族比较多,比如南朝的贵族和清朝的满蒙贵族。当时有些汉人学习满洲贵族嚼槟榔,觉得嚼了之后好像身份就改变了。到现在,槟榔的阶级意义完全反转过来。
所有食物都是有阶级分化的。喝葡萄酒、啤酒、茅台的人都有不一样的身份,而且分化出的阶级也会发生流变。比如,二十年前喝咖啡的人更集中在中上层阶级,现在咖啡就更加普及了,茶叶本来在欧洲是贵族饮品,后来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变成一个更普遍的饮料。
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士绅化(gentrification),可以形容很多食物的流变。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士绅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产阶级标志性消费物的追捧,比如咖啡和飞盘;另一个是由于快速的城市化,一些保持了旧有生活方式的人实现了阶层跃迁,把原本很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带入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视野。

界面文化:除了阶级之外,现在嚼槟榔的群体里几乎没有女性,但在以前不会出现这样的性别分化,邓丽君就在上世纪70年代的歌曲《南海姑娘》里唱过:“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50年后,我们很难想象优雅的女性形象描述中会出现嚼槟榔的动作,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曹雨:性别可以和阶级话语放在一起讨论。在食物消费上,不仅是贵族和平民吃的不一样、男女不一样,其实不同年龄组也是不一样的。
男性女性的食物分化很明显的,过去中国基本上男女不同席,桌上吃的东西也不一样,男性桌上很多酒肉,女性吃这些更少。从年龄上看,老年人和小孩在餐桌上分开坐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喝茶也是。你如果去潮汕,会发现功夫茶是一种男性社交工具,女性就是忙里忙外的角色,很少有闲工夫喝茶。我在越南做调查的时候也发现,男性会很长时间坐在门口喝咖啡,但是女性绝对不会,如果请一个越南女性喝咖啡,她会得到一种特别的尊重的感觉,因为平时根本没有喝咖啡的机会。很多食物在男女之间都有类似的差异,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女性不吃某种食物的刻板印象。
当然,食物符号中的隐喻含义也各有不同。比如抽烟现在变成了女性解放的符号,好像一抽烟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不受男人控制的、有自主意识的女性,而小孩叼起一根烟会觉得自己像个大人。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提到,槟榔因为错过了被西方承认的阶段,而没有变成全球流行的成瘾品。对大多数食物的全球传播来说,“被西方注意到”是一个重要因素吗?许多食物在全球的流行都经过了一个被西方社会认可的过程。比如康普茶(Kombucha)首先是一种东亚本土茶饮,近十年在西方流行后又回潮至亚洲国家,成为了时髦中产的饮料。还有现在很流行的燕麦奶,其实追溯起来中国本土就有很深厚的植物基饮料历史,但一直没有广泛流行。
曹雨:是的,这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绝对存在,一种食物首先要在欧美社会里流行起来,才可能有一个强势的话语地位。而且很多地方会因为西方刺激而去吃某种东西,比如日本人本来是不吃牛肉的,曾经杀牛都是违法的,但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对日本的侵犯,日本人觉得吃牛肉能够强国强种,所以开始大力提倡吃牛肉,以至于日本现在的名产是和牛。
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植物基饮料是西方的发明,实际上拥有最深厚植物基传统的就是中国。西方喝动物基饮料比较多,牛奶在中国的流行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也是和强国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植物基饮料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两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喝豆浆、芝麻糊、杏仁露,桃露,都是非常常见的东西,但它们只是本土的流行,没有形成话题效应,一直到燕麦奶流行,现在人人都开始讨论植物奶。

界面文化:你在《一嚼两千年》中写了槟榔传播的几条路径,其中一条是依靠佛教传播的驱动。中国历史上以宗教带动食物流行的例子多见吗?
曹雨: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比欧洲和中东要小,所以其实例子并不多。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忽视了槟榔传播过程中受到的佛教影响。
素食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本土宗教传播的例子。佛教本源中对食素没有太多强调,梁武帝时期素食才开始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道教对素食的影响也很大,教义很早就提出不食酒肉,因为会影响人的冥想和精神上的精进,另外也有养生方面的考量。现在城市人群中产素食的趋势和宗教又慢慢脱离了,这主要是西方环保主义的推动,不完全是本土的传统了。
界面文化:槟榔既是食物也是一种成瘾品。在食物史和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对成瘾品兴趣很大,许多著作都关注茶叶、咖啡和酒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成瘾食物和普通食物相比有更复杂的社会历史意义吗?
曹雨:成瘾品有三个成瘾维度,分别是生物成瘾、习惯成瘾、社交成瘾。其实槟榔的生物成瘾性并不是太强,主要是习惯和社交这两个维度的成瘾。众所周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某种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如果放在一个社交群体中,这种习惯还会变成一种社交行为,更强化了它的成瘾韧性。

界面文化:在书中的第一节你就提到,制造植物成瘾品大流行的“历史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了。植物成瘾品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时间窗口仅出现在16世纪至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以后,这扇窗口就永远地关闭了。可以简单谈谈这个“历史时间窗口”是什么意思吗?
曹雨:历史窗口期和之前提到的西方话语有关。殖民帝国的构建需要成瘾性食品作为打通贸易的商品,比如大英帝国的构建和茶叶紧密相关,统治者可以通过茶叶构建一个殖民贸易体系。
鸦片也是构建大英帝国的关键商品,它把印度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印度输出鸦片到中国来,两个地方就这样通过殖民贸易联系了起来,使得印度和中国都无法摆脱鸦片。茶叶和糖的贸易也很有效地把殖民地连接在大英帝国的体系里——殖民地要给宗主国大量的物产,还要提供消费市场。宗主国就这样把整个世界连在一起,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殖民贸易的依赖。
界面文化:成瘾品和国家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它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又会担心人口素质的下降。槟榔在现代如何被禁止是很有意思的事,你在书中分析了产业、民众和政府的互动关系,政府有时推崇槟榔,有时又禁止槟榔。政府在管控槟榔流行时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对槟榔的管控与对烟酒的管控有何不同之处?
曹雨:成瘾品让大量劳动人口丧失劳动能力的结果是很坏的,但是槟榔的效果没有这么快,还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只是当民众厌恶越来越高涨的时候,政府会多方均衡考虑要不要禁止槟榔。
网上有一句话很流行——“烟民是国家的恩人”,因为他们贡献了大量的财政税收、缩短了自己的寿命、减少了福利支出。很多国家曾经强制推动过烟草消费,日本殖民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候就曾推广卷烟,压制受众更广泛的槟榔,因为槟榔是当地产业,卷烟是日本的产业。缅甸和泰国禁止槟榔时也是用烟做替代品——当地槟榔主要是小商贩,以一家一户的小推车的方式售卖,而烟草是国营的,大家都去抽烟对国家财政有好处。
槟榔对中国财政来说没有那么大的贡献,大概仅仅是对海南和湖南部分地方的经济有益处。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看,限制槟榔并没有那么大的阻力。

界面文化:为什么你预言槟榔这种食物已经到了流行的顶点,在未来不会有更多人消费?
曹雨:公众对槟榔的反感已经非常强烈了。只有在2000-2013年这段时间,槟榔有全国扩张的趋势,而且在特定群体上特别明显,比如货运司机,这个群体流动性很大且有全国网络,把槟榔带起了很大的一波流行。在2013年之后,槟榔销售增长的趋势开始放缓。
从2013年《槟榔王国里的割脸人》新闻专题报道开始,全国民众对于槟榔的观感基本上是负面的。从产量和销量上也可以看到,2013年以后槟榔的增长远低于前十年。由于现代资讯传播的高效率,我在2020年做槟榔认知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一半被访者对于槟榔的第一印象就是“致癌物”。有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槟榔再要发生流行就会遭遇强力的阻击。
界面文化:《一嚼两千年》的结构和《中国食辣史》很像,主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也是食物传播的历史脉络、文化中的隐喻,以及在中国饮食里的地位变迁。为什么都选择了这三个方面来做研究?
曹雨:这和我自己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关系,而且我自己更熟悉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会从时间维度中讨论食物的传播变化,再就是强调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以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聊食物的符号意义和隐喻,比如辣椒就具有急躁、革命性的隐喻含义。另外,从社会学角度进入,我关注食物在食品工业、人类社会当中起到的作用。这是我对食物研究的“基础三板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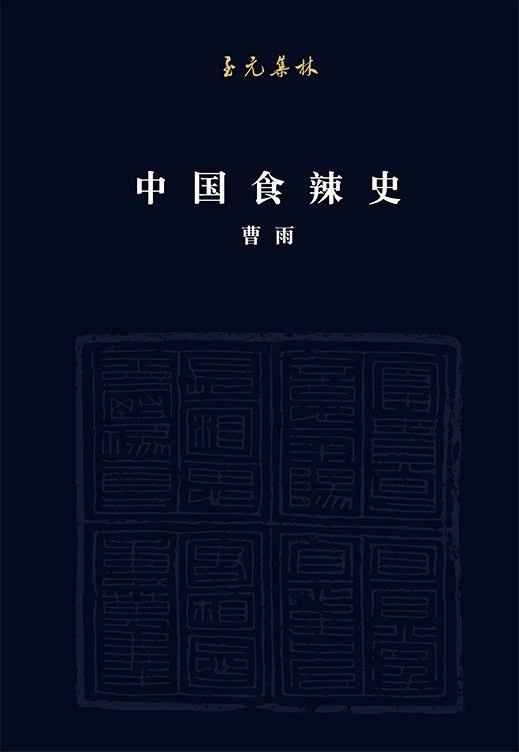
界面文化: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是有研究价值的吗?你怎么判定一种食物值不值得研究?
曹雨:有些食物是支撑人类社会的主要粮食,比如土豆、番薯、玉米、大米会引起社会相当大的变动,但有些食品对人类社会影响比较小, 比如大白菜就没有那么强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也和食物与民族的关联程度有关。稻米对东亚人就有特别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粮食和主食。日本有一本书叫《作为自我的稻米》,谈的是日本民族对米的崇拜,然而把土豆拿去日本就没那么大的意义了。
另外一些食物是符号象征性很突出。比如胡椒、辣椒、姜等,在中国食用时间不长,但由于强烈的味觉特征,所以人们附加了很多符号意义上去,《一嚼两千年》里写的槟榔则是男女情爱的象征意义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