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必将会对伊朗社会和政治产生更广泛的长期影响。”阿克斯沃西写道,如今正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或许正体现了这一点。

2022年9月23日,德国柏林,在抗议马赫萨·阿米尼死亡的示威活动中,一名抗议者手持一幅画。来源:视觉中国
按:当地时间9月13日,22岁的库尔德女性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在德黑兰被警察逮捕,三天后死亡,死因是头部严重受伤。她的死亡引发了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截至9月25日,抗议依然在发酵。近年来,伊朗多次爆发大规模抗议,但与此前抗议多关注政经问题不同,本次抗议的重点是保护女性权利和公民个人自由。
对女性行为举止、着装打扮的严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们对伊斯兰世界的印象,而伊朗与许多其他中东国家不同的是,伊朗曾在20世纪中叶实现过较深程度的世俗化(得益于伊朗王室巴列维国王的支持),中文互联网内也曾流传过1979年革命前穿着打扮非常西化的伊朗女性出现在城市街头的照片。因经济发展乏力、国内矛盾激化,1979年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在伊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革命的最大推手、意识形态导师和受益者是宗教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个人权利自那时起急转直下。

近半个世纪后回望1979年革命,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鲜明的“反西方”元素。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 Alitto)认为,伊斯兰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多为宗教性人物,霍梅尼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发起的革命及其主张更深更广地排斥西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它们在理论上与伊斯兰的公有主义与精神主义对立。事实上,艾恺在《持续焦虑》一书中指出,发生在伊朗等中东国家的“宗教-保守主义势力复辟”不过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在地表现形式之一。纵观全球,发端自西欧的现代化在带来科学技术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现代性焦虑,文化民族主义是其他地区的回应形式之一,“在任何文化或国家,只要是它面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优势,而被迫为自卫向外做文化引进时,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
伊朗的1979年革命就是这种现代性焦虑的反应。英国学者迈克尔·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在分析为何1979年革命有如此深的反西方印记时指出,形形色色的态度与动机慢慢汇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伊朗人民留下的历史创伤、西式教育和西式生活方式对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冒犯、年轻单身男性在面对就业机会匮乏和看似享有更多自由余裕的年轻城市女孩时被唤起的强烈焦虑与嫉恨……
阿克斯沃西同时指出,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女性的命运并非如外部观察者所预想的那般黯淡,得益于伊朗社会存在的对于学习和知识素养的潜在文化尊重,女性和男性一样被鼓励接受教育,其中不少女性在受教育阶段就脱颖而出,至少在中产阶级当中,已经出现了“女性一代”——在教育部门、神职岗位、私营经济、医药领域和国家公务员队伍中都存在着大量女性。“一些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必将会对伊朗社会和政治产生更广泛的长期影响。”阿克斯沃西写道,如今正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或许正体现了这一点。
撰文 |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翻译 | 赵乙深
不同于政变或能够给政治带来些许改变的小型事件,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剧变。革命并不仅仅是替换个别人员,还会改变整个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不仅会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政治纲领,还会改变整个政府体系、意识形态、国家宪法、公共准则;这种改变不会仅持续三到五年就消失,而是会持续几代人甚至影响全球范围。
根据以上标准,1979年伊朗革命完全可以比肩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发生如此重要且具有如此规模的事件绝不可能只出于简单的理由。解释革命缘起的复杂性往往会引发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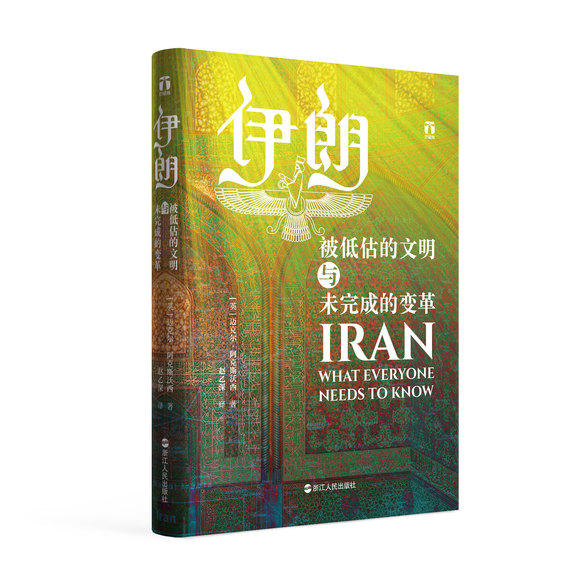
几个不同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参与了1979年伊朗革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团体在霍梅尼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然而革命成功后,这些团体发生利益纠纷,一些人感觉被新建的伊斯兰共和国背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描绘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整个过程时出现了几个被广泛认可的版本,这些说法各异且彼此相互矛盾。一个较为稳妥的观点是这些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所引发的。
革命爆发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国王长期没有给他的子民提供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1953年后,老一辈伊朗人对此已懒于改变,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伊朗人登上舞台,其中一些深受60年代风靡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学生运动与暴力革命的影响。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团体就是由世俗左派学生组成的,他们甚至比其他团体更激进。其他参与人士还包括老一代左派人士、同情人民党人士、摩萨台国民阵线的支持者。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仍然追求立宪主义和1906年制定的宪法原则。
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刻意疏远教团,霍梅尼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但其他教士对于国王所倡导的全面西化、世俗改革,对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王室的渊源的强调以及伊朗各个城市蓬勃兴起的西式物质享乐主义等也充满愤恨。和以往一样,与教团紧密结盟的是小商贩和工匠群体,他们对于经济模式的改变十分不满。国内乡村地区开始出现新兴超市和进口食品,导致了经济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他们从传统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推到边缘位置。这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小商贩们的生活被伊朗复兴党完全搅乱。起先,他们以为只要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生意,复兴党政权就会放他们一马,然而复兴党却要一竿子插到底,将改革措施直接指向社会最基层的普通人的生活。在1976—1977年的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飞涨(堪比1905—1906年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大批小商贩因所谓的投机倒把而遭到逮捕。除了小商贩和宗教学生与教团紧密相连之外,还有一个团体同时与宗教支持者和立宪派人士关系密切(即自由运动,虽然规模小,但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两个极端学生群体:其中一个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 Organisation, MKO),它试图融合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更加左派激进,即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Fedayan-e Khalq)。

引发革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不满。土地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使得大量贫穷、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向德黑兰寻找工作。伊朗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经历了短暂的上扬后,在1976—1977年开始下滑,在收入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物价和房租却依然逐步走高。有证据显示,伊朗城市贫民在革命初期并未过多参与其中,但到1978年秋,工人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他们的罢工游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和政府的正常运转。经济下行使得所有社会阶层都开始感到不安并越来越多地抨击政府。国王个人统治和单一政党国家的显著弊病就在于一旦情况发生恶化,根本没有替罪羊来分担责任。
导致革命爆发还有其他因素,一些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比如国王与人民之间渐行渐远,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才是对于他本人统治的主要威胁。但他的判断与事实可谓背道而驰。再有就是国王的病情。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得了白血病,并且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在1980年流亡期间死于此病)。
即使说了这么多,仍然无法完全解释革命为何会发生,因为只有通过叙述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阐明国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权力,以及革命为何变得势不可当。
就革命本身而言,各种形形色色的态度与动机慢慢汇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伊朗国内对于过去长久以来西方介入伊朗的深恶痛绝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从19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伊朗领土并对国家百般羞辱,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打破伊朗保持的中立并侵犯其主权。此后,西方于1953年策划的政变使这种对西方的愤怒情绪达到顶峰。然而与之矛盾的是,许多伊朗人却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民怀有一种亲近感甚至是崇敬感。在那个时代及以后,革命者们常说伊朗人的敌意并不针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而是完全针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政府。产生这种复杂情绪,部分是缘于一种屈辱的失望感。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颇为失望。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理应成为伊朗的朋友,并一再以朋友自居,但却屡次辜负了伊朗人对他们的信任。

对于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影响较少的更为保守的伊朗人来说,电视媒体和大街上各种扑面而来的西式广告、电影和服装给他们带来的直观感受是令人厌恶的,他们对于这些西方元素给伊朗宗教和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也麻木不仁。许多人因为美国广告媒体的大规模轰炸而感到迷茫,并觉得受到冒犯。当时在伊朗居住着大量外国侨民,尤其是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末期,数量多达约5万)。虽然也有例外,但总体来说伊朗人感觉美国人在当地表现得傲慢自大,且毫不在意当地人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人在自己的国家,特别是首都德黑兰,反而感觉像是外国人。霍梅尼也在1979年的一篇讲话中提道(讲话虽发生在革命之后,但霍梅尼本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革命前的状态),西方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强加到伊朗人民头上只是为了让伊朗人更好地受西方控制。
这些人渴望自由,渴望我们的青年也得到自由……但是,他们渴望的是怎样的自由?……他们希望赌场自由开放,酒吧自由开放,声色犬马场所自由开放,吸食海洛因者随意吸食,抽鸦片者自在抽吸,这就是他们用来阉割我国青年人的手段,使青年再也无力起来反抗他们……这些伪民主派受到那些想要掠夺我们、使我们的青年麻木不仁的西方列强影响,倡导绝对自由,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应被禁止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德黑兰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性的焦虑和怨恨。当时的德黑兰充斥着年轻男性,除一些学生外,还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和外省城市家庭,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勉强度日。他们生活在城市南部,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在那里女性都穿着伊斯兰传统罩袍。但在城市北部,他们却能见到年轻女性独自外出,穿着招摇,尽显西式时尚。这些女性身上同时表现出财富、傲慢和西方的影响。他们还能在广告中和电影院前的宣传板上不时看到女性的形象。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使人馋涎欲滴却又高不可攀,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自身令人绝望的劣等身份。他们没钱结婚,更无力组织家庭,由于成长过程中严苛的宗教影响以及与外来时尚形象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欲望的破灭与社会紧张情绪以及对西方影响的愤恨心态已经相互交织。

此刻,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随着20世纪6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反越战运动等舶来品言论被不断放大并逐渐成形,特别是在左派学生和青年一代当中。但是,许多在上一代就应该转向左翼的年轻伊朗人在70年代却转向伊斯兰教,并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伊朗人的自我身份的核心。
伊朗的女性地位问题自1979年革命以来就充满了矛盾(甚至要比伊朗社会其他领域更为严重),如果没有与之相反或者近乎相反的陈述以作平衡,就几乎不可能对此问题作出任何强有力的陈述。如果想要了解当代伊朗以及伊朗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至今几乎还没有其他哪一个复杂现象的重要程度能与这个问题相提并论。
要论述这个问题,需要从霍梅尼开始。霍梅尼对于女性地位的立场既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又具有多变性。1963—1964年,当他刚刚以反对国王而出名时,他曾抨击国王给予女性投票权的政策(却没有批评自己的土地改革的相关计划,土地改革在农民中大受欢迎,却损害了教士的土地红利)。但是到了1979年,霍梅尼承认女性在推翻国王过程中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他决定不再违背历史潮流,从而保留了女性的投票权。然而,他却重新引入女性需要佩戴面纱的制度,取消了国王在1967年推行的《家庭保护法》中有关自由化的规定,并再次强调沙里亚法相关条款应发挥其作用以及家庭中男性至上的原则。这就意味着,除了别的权利外,女性一旦离婚就将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在司法案件中,女性证词的重要性将不及男性,诸如此类。这导致女性不再可能从事法官或者律师等职业[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于1975年成为伊朗首位女性法官,却在1979—1993年期间无法再从事自己的职业。多年后的2003年,她以伊朗人权律师的身份成为该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然而,取消《家庭保护法》所引发的其他变化,例如在理论上重新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以及将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9岁(后又上调至13岁),却并没有真正起到多大作用,因为全社会都以此为耻。
伊斯兰共和国在建立之初的几个月里对女性地位作出的许多改变,使得许多伊朗女性,尤其是但不仅仅限于那些曾积极参与1978年抗议示威活动的左派女性,痛苦地感觉到自己遭遇了革命的背叛。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其他变化对于女性来说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两伊战争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当男性上前线作战时,女性就在工作中或者家庭里承担了男性的角色。教育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也引发了其他一些重要改变,而这些改变却往往得不到外界重视。

由于高出生率和快速增长的人口,以及巴列维政府牺牲农村以换取城市发展的偏颇政策,巴列维国王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民初等教育。而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即使是最偏远的乡村也至少有一所学校,在几年的时间里,所有儿童都有希望接受基础教育。伊朗识字率迅速攀升,在2015年达到86.8%。与此同时,许多来自更为保守的乡村地区和外省城镇地区的家庭(家庭里的父亲)破天荒地乐于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学校,因为学校根据性别将学生进行分离,而且女孩(从9岁开始)上学期间必须穿着希贾布。男孩和女孩上学开始成为日常,许多家庭要求子女去取得尽可能优异的成绩,在学校接受教育直到18岁,然后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这体现了伊朗社会存在的对于学习和知识素养的潜在文化尊重。政府对上大学持鼓励态度,在两伊战争后的几年时间里,一大批大学和自由大学(独立于政府财政支持,依靠学生学费自给自足的大学)在各省相继建立。
在此之际,伊朗出现了同西方国家中学教育阶段相类似的现象——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阶段的学习中表现得更为勤奋,考试成绩也相对优异。这也使得女孩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更高,所以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年里,大学录取学生中60%—65%为女性。紧接着,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离开大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伊朗年轻人失业率之高令人泪目,年轻女性失业率甚至更高),多数人都能找到优渥的工作。在教育部门、神职岗位、私营经济、医药领域和国家公务员队伍中都存在着大量女性(当今超过一半的伊朗教师是女性)。
伊朗女性地位的提高,可视为教士集团成功掌握伊朗政治和决策权所带来的一种结果。教团是伊朗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伊朗国内还有哪个阶层能毫无保留地将教育本身看作是一种优良品质的话,那必是教团无疑。女性接受更高水平的大众教育,以及更广泛地进入职场本身就是这种潜在观点的一种体现。同时,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引发另外一些现象。在伊朗许多家庭中,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更高的教育水平就意味着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一般来讲,女性结婚时间有所推迟,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左顾右盼,甚至干脆选择不婚。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产阶级女性中所发展出的关于家庭、职场和政治的自由派观点与女性自信心的提升和收入能力的增强存在密切关系。其他观察人士,特别是齐巴·米尔胡塞尼(Ziba Mir-Hosseini)和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都提到伊朗进入了“女性一代”的观点。
当然,人们也不应该对此过分夸大。以上现象大部分只出现在中产阶级女性中,大多数底层女性甚至不敢幻想能够找到一份收入良好的工作,她们仍然需要面对高失业率、不公正的性别歧视、极度贫穷等残酷现实,以及毒品、卖淫、家庭破碎等问题给她们带来的无法挽回的伤害。相当数量的女性仍然无法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晋升到管理岗位。近年来,政府中仍有人试图在部分大学课程限制女性上课名额(截至目前,这种限制所产生的效果还不明显)。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对于伊朗实现女性平等的合法愿望来说真可谓是一个持久且耻辱的污点。

然而,一些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必将会对伊朗社会和政治产生更广泛的长期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尽管社会还存在很多黑暗面,但这种变化是伊朗社会光明前景的特征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保持谨慎乐观态度。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第四章与第六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