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传中,霍布斯鲍姆更多书写的是社会与政治变动,极少提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当20年后埃文斯接过笔来,他不再执着于描绘大时代图景,而是登上霍布斯鲍姆落满灰尘的小小阁楼,阅读他写作的信件手稿、诗歌、短篇小说、游记,试图进入他更隐秘的内心世界。

霍布斯鲍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我和艾瑞克并非密友,但也相识已久。实际上,我对他太过崇敬,因此无法与他走得太近,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们谈论什么,他一定知道得比我多太多。”同为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成员,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如此回忆与霍布斯鲍姆的生命交集。在学术院的传统中,一位成员过世后,现有的一位成员将为其撰写传记,霍布斯鲍姆的人生回顾任务就这样交到了埃文斯的手中。
霍布斯鲍姆2012年去世,终年95岁,他肩负着太多头衔: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左翼阵营的重要代言人。在近百年的人生历程里,他亲历诸多重大历史时刻,无论是1933年纳粹在柏林掌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是冷战及其后的历史进程,横跨了他自己提出的著名历史概念——“短暂的20世纪”。
埃文斯将霍布斯鲍姆的传记取名为“历史中的人生”——这固然呼应了霍布斯鲍姆在《趣味横生的时光》里的自我评价:他的个人处境、人生追求和激情,都是被经历的时代塑造。在自传中,霍布斯鲍姆更多书写的是社会与政治变动,极少提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当20年后埃文斯接过笔来,他不再执着于描绘大时代图景,而是登上霍布斯鲍姆落满灰尘的小小阁楼,阅读他写作的信件手稿、诗歌、短篇小说、游记,试图进入他更隐秘的内心世界。

在那些资料里,他看到漫无目的、对生活不满的青年霍布斯鲍姆,“买书,整天做白日梦。为什么不呢?也许,给自己一点愿望满足感也无伤大雅吧。”读到他在妓女面前自卑得无地自容,回家后自我安慰般转移至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对此埃文斯调侃:“他用马克思主义充实自己的头脑,这会是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未曾体验过的性爱的替代品。”)在剑桥时期,霍布斯鲍姆是其他同学眼里那个“什么都懂的大一新生”,但因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上,以至于“不得不在假期里挤时间恶补落下的功课”。
直到九十岁高龄,霍布斯鲍姆都未曾停止过写作与发表,病入膏肓住进医院后,还持续关注着右翼阵营的动态,妻子会像“走私那样给他带去‘右翼阵营’的报纸,而他读这些报纸时会‘尽情释放他对右翼政治的不满,而且经常轻蔑地用尖刻的评价来形容戴维·卡梅伦:他就是个小人物’”。他的左翼立场始终鲜明,从未动摇,退休后曾受邀请到纽约新学院教课,听课学生回忆道:“他意见尖锐,经常处于愤怒之中……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立场鲜明,你要对自己诚实,作为一名享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士,你有责任选择正确的立场。”
在《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中文版推出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了理查德·埃文斯。埃文斯谈到,书写霍布斯鲍姆的最惊喜之处是,发现他并非大多数人假想的理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情绪丰富、感性敏锐的人。埃文斯感到他的自我评价是如此适恰——一个“内心千头万绪、受直觉驱动的历史学家。” 他也谈论了霍布斯鲍姆人生的重要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超越理论教条,保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霍布斯鲍姆不仅拥有“历史中的人生”,也影响了包括埃文斯在内的英国后代历史学家——他们结合宽广的世界视野,在历史写作里兼顾文学性与可读性,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广泛介入现实。

界面文化:历史学家A.J.P.泰勒曾经说过,传记不是历史,但每个历史学家都应该尝试写一次。对你来说,撰写历史研究与撰写传记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理查德·埃文斯:写传记比写历史更容易,因为传记已经有了主题——一个人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而且结构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而在历史中你必须发明主题、构建结构,并决定选择与放弃的材料。但传记也有比写历史更难的部分,因为必须追踪书写对象的每一个生活细节,而在历史研究中,你只要关注和问题与论点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
在写作传记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一种有些奇怪的乐趣:我发现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6月8日,而不是普遍认为的6月9日;他在1953年离婚,而不是标准传记所声称的1951年。
传记某种程度就像历史一样,你在讲述生活故事时,也要把它们编织到更大的语境里。一个人拥有许多平行的生活轨迹,需要知道如何在不丢掉主线的情况下涵盖它们。
界面文化:尽管你认识霍布斯鲍姆很久了,但你们并非十分亲近的朋友。在撰写他的传记时,你从他身上发现的最出乎意料的地方是什么?
理查德·埃文斯: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早年有过多少性生活,以及他有多会书写关于最亲密的关系与体验的散文。这些文字大部分他从未发表过,对我来说如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宝库。这些不为人知的散文,内容包括他1930年代在法国的旅行、1950年代与一名兼职性工作者的情事、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以及类似的回忆录。
这些材料连同他的日记(1934-1951),让我得以将他描绘成并非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假想的理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情绪丰富的人。最有趣的,也是我以前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他在思想和个人生活层面与法国和法国人的距离有多近、与德国和德国人的距离有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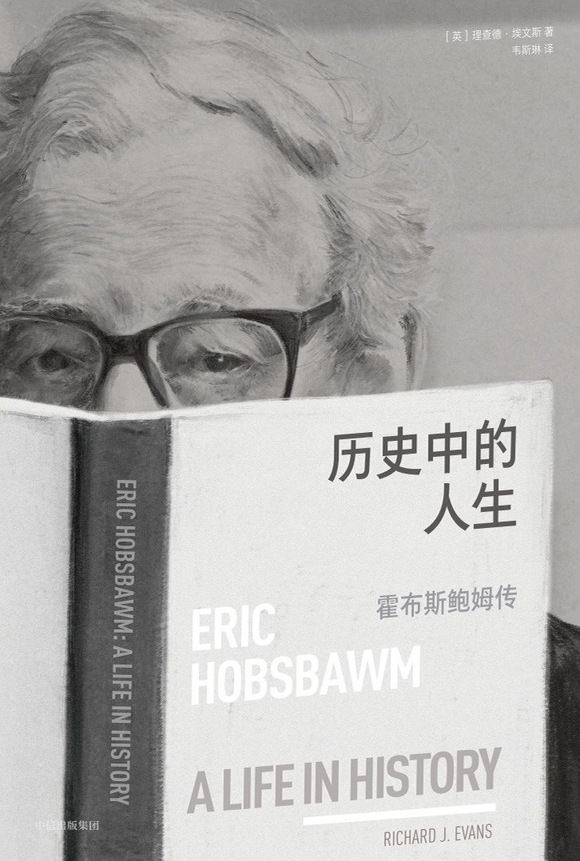
界面文化:这本传记也因包含太多有关收入、出版交易和销售等的琐碎细节而受到了一些批评。你对霍布斯鲍姆的思想历程与政治生活的关注远不如他的私生活多,为何选择这样写?
理查德·埃文斯:一开始我以为会分析他的书,但写了几页关于《革命的年代》的文章后,我意识到这样做会使传记长得离谱,而且其他人也已经在长篇的综述和讨论中做过了。所以我决定把他的每本书都当作个人故事的一个方面。收入、出版交易和销售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而且我有他的文学经纪人关于所有这些的档案,而这些细节以前是完全未知的。对于每一本书,我都会讲述它是如何诞生的,霍布斯鲍姆是如何写作、如何出版的,接着我会引用评论,这些评论也提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关键和分析要点。
关于霍布斯鲍姆的私生活和想法,我有很多令人惊喜的资料,以至于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要讨论是他的个人生活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另外,我的书是一本传记,而不是关于霍布斯鲍姆思想史的学术论文,尽管我当然会详细讨论他的思想和政治发展。
最后,我相信每本书都有各种各样的读者群,作者需要为所有人考虑。人们阅读关于霍布斯鲍姆的事,因为他们想了解20世纪的共产主义,或者1920年代维也纳的犹太社区、战时英国军队的生活、1930年代的剑桥大学、为何评论家将1950年代称为“波希米亚式伦敦的喧嚣生活”、新工党、法国人民阵线或军情五处的起源,或者许多其他的原因。总的来说,我希望这本书能解答什么是历史学家觉得是恒久有趣的问题,以及历史学家为何写了这些作品。

界面文化:我们来谈谈霍布斯鲍姆的人生。在书里你非常关注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的学生生活,那段时期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去剑桥后就不再写日记,离开后才重新开始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绝望,以为永远都找不到补充材料了。但是当我去采访他大堂兄——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罗恩的女儿时,她告诉我,她在搬家清空阁楼后发现了一个箱子,装满了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学习期间写给她父亲的信,并把它们交给了我。这显然可以作为他日记的补充材料,这些材料很长很详细,使我能完全还原他的学生生活。
他早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剑桥,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第一次见到了其他共产党人,那里的朋友包括来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人,这使他拥有了曾经缺乏的全球视野。他也认为共产主义存在狭窄和狭隘(narrow and parochial)之处(当时是斯大林时代),以及共产主义者们对音乐、电影或文学领域的不关心,并在这些方向上进行了自我探索。
他从来不只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导师穆尼亚· 波斯坦(Mounia Postan)是经济史教授,拥有多语种和多文化的背景,出生在比萨拉比亚(注:曾属于沙俄,1918年与罗马尼亚合并,后又成为前苏联领土,现大部分属于摩尔多瓦),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有所联系,他将霍布斯鲍姆介绍给了年鉴学派。在剑桥的经历让霍布斯鲍姆成为了历史学家。
界面文化:1946-1954年在剑桥学习期间,霍布斯鲍姆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核心成员。他也与克里斯托弗·希尔以及E.P.汤普森等其他左派学者建立了联系,这群学者如何影响了后来的英国历史研究?
理查德·埃文斯:从1947年起,霍布斯鲍姆在伦敦伯贝克学院担任讲师,也正是在伦敦接触到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小组出人意料地短命,但确实让他认识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和小组成员的讨论中获益良多。
该组织对包括我在内的1970年代进入历史界的那一代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成员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是在他们1956年离开英国共产党后出现的(霍布斯鲍姆没有正式离开,但在此之后不再受其约束)。当时,英国历史研究由政治历史学家主导,而霍布斯鲍姆、希尔和汤普森等人则为这一主题指明了一条更具包容性、更广泛、更理论化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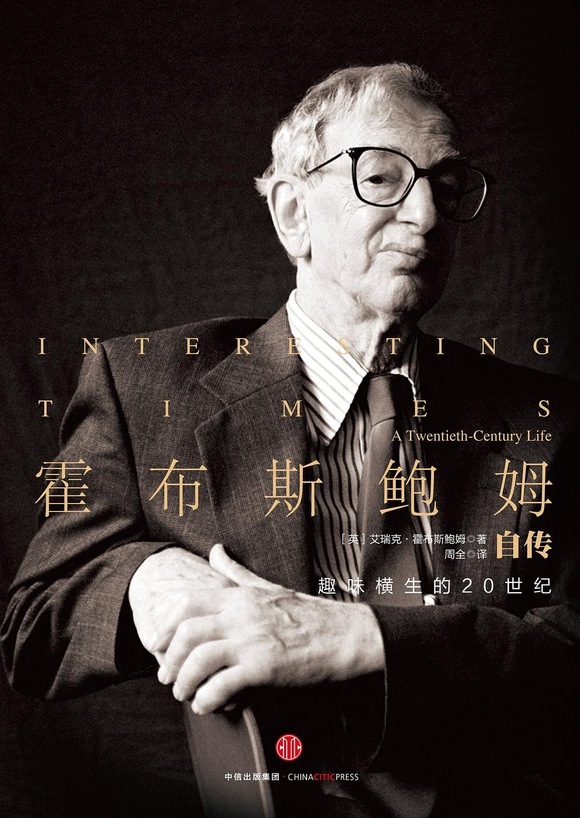
界面文化:在霍布斯鲍姆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方面被马克思主义信仰牵动,另一方面也秉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你认为后者最终占了上风吗?马克思主义给了他研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同时似乎也阻碍了他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他关于斯大林和前苏联的评价。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始终尊重历史证据,例如他拒绝列宁和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但他的方法总是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也结合了法国年鉴学派。他在感情上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尽管离党越来越远。在1956年的危机中(注:在当年的苏共二十大中,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震动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员),他试图使党民主化,但没有成功。此前不久的访苏经历打消了他认为这是未来发展方向的想法,但他仍然相信苏联抑止了民族主义,这在他看来是件好事。
界面文化:民族主义一直是霍布斯鲍姆的关注重点,他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对民主的巨大威胁,他的著作从《传统的发明》到《民族与民族主义》如今都是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文本。是什么让他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并形成这种想法?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人。他是英国人,认同自己的英国身份,但他也有很多国际联系,总是以比较的视角看待历史。1930年代,当他与一群年轻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人一起在法国旅行时,他开始认真思考国家认同问题,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倒退的、非理性的力量,正如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所证明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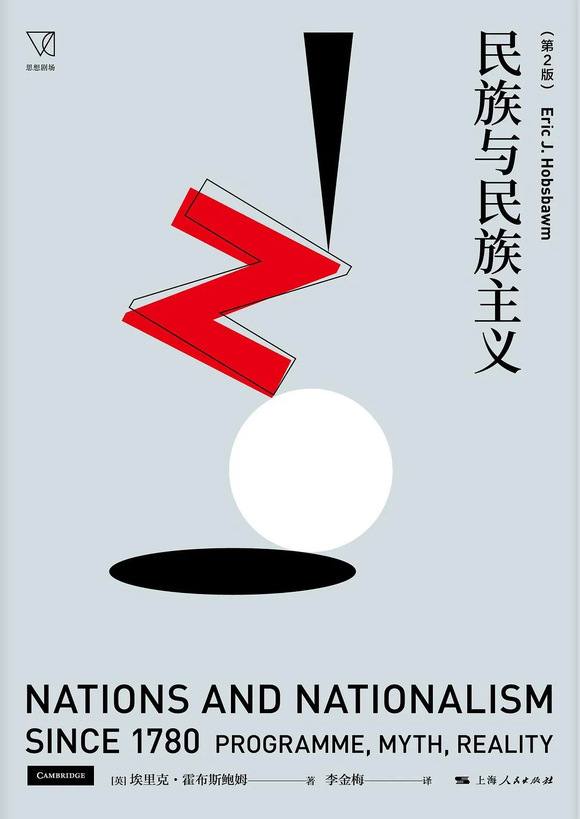
界面文化:在赞誉之外,他也因其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以及对女性主义和性别议题的轻视而受到批评。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当然有他的盲点,尤其是非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国,还有性别领域。他可能不像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欧洲中心:他曾通过在印度开放的棉花市场解释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但总的来说,他仍被广泛阅读,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好的可读性且引人入胜,尤其是社会历史研究,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界面文化:除了学院研究工作,霍布斯鲍姆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广泛介入现实。1980年代之后,他被视为英国工党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传记作者本·皮姆洛特曾经总结道:“如果新工党有智识上的创建者,霍布斯鲍姆绝对可以声称自己是其中之一。”他是如何参与英国现实政治的?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甚至在二战前就一直参与英国政治,他在1935年大选中帮助工党竞选。1945年,他再次帮助他们的竞选。他的热情持续存在着,尽管他也总是提倡广泛的人民阵线(比如他亲身经历过的1936年的法国)。1950年,他学习意大利语,远离了英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转向意大利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注:指西欧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路线,主张“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后者要求他撰写有关英国政治的报告和文章,这使他再次与英国工党进行了更紧密的接触,并做出了著名的演讲:认为工业工人阶级现在正在衰落,如果要赢得大选,该党必须与其他进步的中产阶级一起加入行动。
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在反对左翼极端主义的斗争中采纳了这一论点,这导致了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的成立,并在1997-2010年期间成功地推行了这一理念。[注:新工党试图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发展和赞成“第三条道路”,强调社会公正(而非平等)的重要性,相信利用自由市场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

界面文化:你多次提到霍布斯鲍姆影响了你后来的历史研究。就你个人而言,他的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之处在哪里?
理查德·埃文斯: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极好地展示了历史图景——正如他的写作和我自己努力实现的写作——结合了文学性和可读性、扣人心弦的叙述、概念和理论上的清晰分析,以及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性的细节。
贯穿于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霍布斯鲍姆有着极其宽广的历史视野,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结合起来,并跨越许多国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各地,摆脱了当时和现在大多数历史著作的狭隘性。
界面文化:写作完传记《历史中的人生》,你开始转向研究阴谋论。《希特勒的阴谋:第三帝国与偏执的想象》今年也在中国出版了,你为何对阴谋论感兴趣?是否受到了充斥着假新闻与阴谋论的当下现实影响?
理查德·埃文斯: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当我完成“第三帝国三部曲”时,我开始意识到关于这个话题流传着很多阴谋论,有些是旧谣言重新流行,有些则是全新的,它们呈现了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其中一些理论甚至进入了主流的历史写作,例如关于1933年的国会大厦火灾(注: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起火,希特勒下令逮捕和监禁反对党成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该事件推动了纳粹上台,许多坊间传言认为该次纵火事件是纳粹党故意为之)、1941年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飞往苏格兰的事件(注:指当年赫斯独自驾驶一架飞机在英国上空飞行,在苏格兰跳伞并被捕。有民间传言认为,赫斯此行是代表希特勒向英国提出“和平提议”)。我一直对历史的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感兴趣,这似乎是一个既令人担忧又有趣的现象,所以我设立了一个关于阴谋论的研究课题,这本书就是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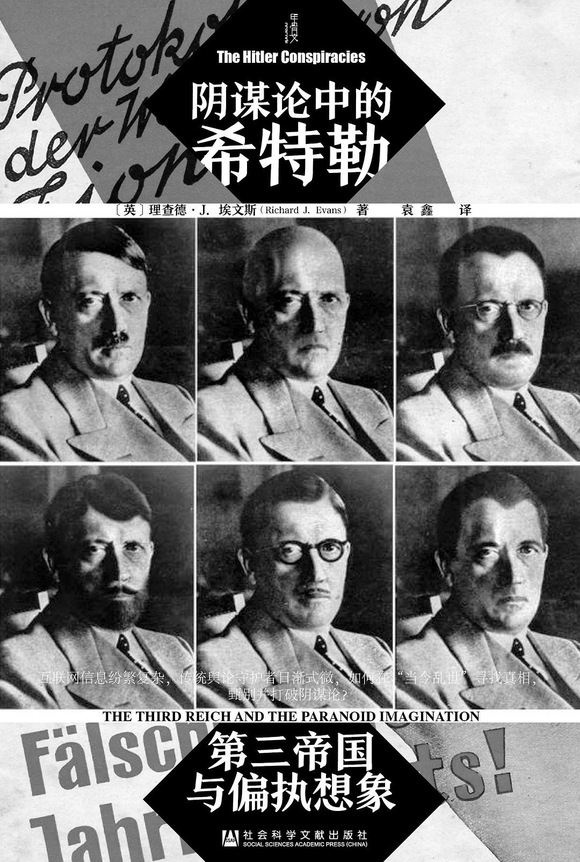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始终对介入社会、参与公共讨论保持热情,比如曾写作数篇文章驳斥戈夫的历史教育建议(注:迈克尔·戈夫是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他重新起草了学校的历史课程,增加了爱国主义内容)。在1950年代前后,英国历史学家很少为公众写作,如今许多英国学者都热衷于此,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你认为是什么让英国学者热衷于参与公共讨论?
理查德·埃文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见解,但我认为并不精确。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比现在要少得多,而且他们的研究通常不那么细分。相当一小部分人也为广大公众写作,包括我在牛津的老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和A.J.P.泰勒,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们,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当年的历史辩论里,“绅士”(农村资产阶级)在17世纪英国内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已经传到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知识和文化期刊上,受过教育的公众们也紧紧追踪着这些讨论。
最好的英国历史写作一直在文学传统中,由吉本和麦考利创立(在牛津我必须学习他们的作品),自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历史学家参与以来,欧陆的历史学术研究更加注重社会科学,所以可读性更差一些。
英国的政治辩论也非常关注历史——如今我们辩论的核心问题关于大英帝国,以及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现代英国经济崛起中的作用。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都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工作,并不参与当下的问题讨论。
界面文化:你在数次公共历史讨论中都提到,当下英国历史研究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为何做出如此判断?
理查德·埃文斯:不仅是英国政府,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期也是如此,都一直在试图塑造国家历史的呈现方式,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特别是让历史向积极的、不加批判的、伪爱国的方向倾斜。这在英国的卡梅伦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也很明显。政府控制着历史研究的大部分资金,越来越多地以此阻止反对国家历史解释的学者,真正的历史学术和理解正在遭受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