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本身具有意识的概念并不罕见,许多科幻小说就是利用这一概念来探讨人类与他者、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等问题的。

图片来源:豆瓣
记者 |
编辑 | 黄月
于日前播出的Netflix网剧《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三季收获了诸多好评,但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不少网友指出,大部分剧情失去了前两季的多样性,而是指向了同一个主题,即“人类是万恶之源,只能自取灭亡”。也正因为此,主题上仍留有想象空间的故事收获了最多赞扬,比如第九集《吉巴罗》引发了女主角是否代表殖民地原住民的争议,比如第四集《糟糕的旅行》中船长牺牲了一船人并从海怪手中逃走的做法,也让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失去了意义。
相较之下,第三集《机器的脉搏》里诗意的表达与缥缈的想象显得更加晦涩,令人难以参透。这个故事改编自迈克尔·斯万维克的同名科幻小说,曾获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它讲述了宇航员玛莎在一颗陌生的星球上死里求生的故事。玛莎与波顿本来在木卫一上执行任务,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掀翻了飞船,波顿不幸死去,玛莎只好拖着她的尸体,在氧气即将耗尽的状态下艰难跋涉。这时,木卫一突然化身为具有神秘意识的生命体,并通过波顿的思想尝试与玛莎进行沟通。最终,玛莎在木卫一的劝导下放弃了肉身,跌入熔岩湖,实现了意识上的“永生”。有趣的是,由于波顿生前喜爱诗歌,木卫一和玛莎的交流也是通过诗歌完成的,剧集的标题便出自于抒情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她是一个欢乐的精灵》。

玛莎的结局到底是生还是死?木卫一又为何要引导她跳进湖中?这些问题引发了观众的猜测与思考,有人提出木卫一是在诱骗人类,获得它所需要的物质和信息,从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意识。由于这个故事过于简短和开放,任何解读都可以是自圆其说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以简单的目的论来揣测木卫一的“行为”,毕竟,人类所能设想出的目的在遭遇既非人类、也无人形的存在时,极有可能是无力而无效的。
实际上,星球本身具有意识的概念并不罕见,许多科幻小说就是利用这一概念来探讨人类与他者、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等问题的。笔者认为,通过对过往作品的梳理,玛莎的故事或许有机会得到另一种解读。
说到具有生命的星球,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于1972年提出的“盖娅假说”,这个假说以希腊神话中的大地母神盖娅命名,认为地球是一个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有机整体,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地球就能获得适宜生存的内在平衡。自诞生以来,盖娅假说就面临着诸多争议和误解。反对者认为,所谓生物反馈稳定全球环境的说法,和当今气候变化的现状是相矛盾的,也有人将母亲的刻板印象附加在盖娅身上,将自然视为一个慈爱、友善却非常被动的存在。
虽然饱受争论,盖娅这一极具想象力的概念还是为科幻文学带来了许多灵感。在《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中,阿西莫夫就选择了“盖娅星系”这样一个人类终局。在机器人丹尼尔的引导下,人类放弃了个体意志,进化出集体意识,还将其扩展到了地球上的动植物,甚至是无生命的物质,万物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每个人都可以代表盖娅文明,并共同做出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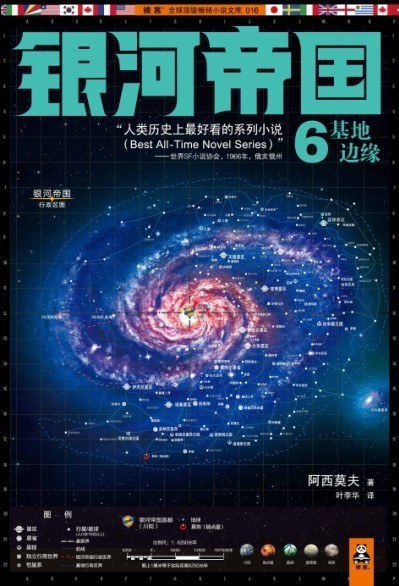
为什么阿西莫夫要放弃人类最引以为傲的自由意志,转而选择意识共融这条路呢?在《人类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基地系列”与 “三体系列”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在梳理了“基地系列”后发现,系列前半部分塑造的是一个银河帝国,这一形象是历史上罗马帝国及美国国家神话的映射;半个世纪之后,阿西莫夫逐渐认识到人类无止境的冲突与分裂,于是以盖娅之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共同体”方案。通过这种方式,阿西莫夫乐观地希望人类可以克服分裂,走向团结互助的未来。
另一名科幻文学巨匠阿瑟·克拉克也写过类似的故事。在《童年的终结》中,名为“超主”的外星人突然降临地球,并帮助人类实现了没有战争、一片祥和的生活。其实,超主的行为授意于一个名为“超智”的更加高级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已经进化出不需要物理形态就可以跨越星系的能力,它不断扩张着,吸收了地球上所有十岁以下的儿童,孩子们“像无数雨滴一样”脱离肉身,汇入了超智的海洋。与阿西莫夫的乐观不同,克拉克通过这个故事悲观地指出,人类的童年早已终结,融入超智慧体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而只是揭示出人类文明的穷途末路。
两名科幻大师无疑已经认识到了人类的局限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笔下的外来生命虽然有和人类不同的长相,但仍然拥有类似于人的思维,它们可以和人进行沟通,而且往往彰显出比人类更先进、优秀的品格。同时,“万物互联的超级智慧体”这一构想也似乎没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罗西·布拉伊多蒂的著作《后人类》就曾批评过这类构想。她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毫无障碍的交互关系揭示出人类对于他者的单一想象与普世价值观,这种想象非常被动消极,因为它建立在共有的脆弱感和大难来临的恐惧感之上。她所认同的后人类主体则应首先承认他者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与之联结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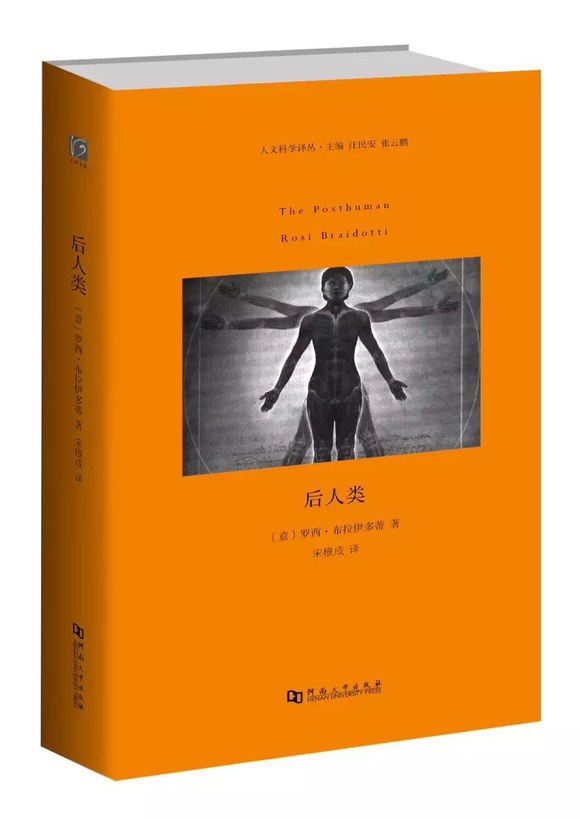
遵循着布拉伊多蒂对于后人类的看法,另一本书写“星球意识体”的著作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波兰科幻文学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于1961年写就的《索拉里斯星》。国外社交网站Reddit的一篇帖子甚至提出,《机器的脉搏》正是基于《索拉里斯星》改编而成,无论这个猜测是否正确,莱姆的这本著作确实可以成为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解读《机器的脉搏》的全新思路。
索拉里斯星的形象与阿西莫夫的盖娅截然相反,它不是友善的母神,而是令人不安的梦魇,是人类认知之外的“绝对他者”。索拉里斯星上覆盖着深红色的胶质海洋,它的形态千变万化,好似有独特的思维和能力。为了解开索拉里斯之谜,人类踏上这片海洋并试图与其进行“接触”,但是种种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面对索拉里斯,人类陷入了彻底的迷失,而这颗海洋星球则自始至终对人类的试探保持着冷漠。这当然是莱姆有意为之,在某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想要借助索拉里斯切断所有通往“生物”的人格化线索,这样一来,接触就无法按照人类的人际关系模式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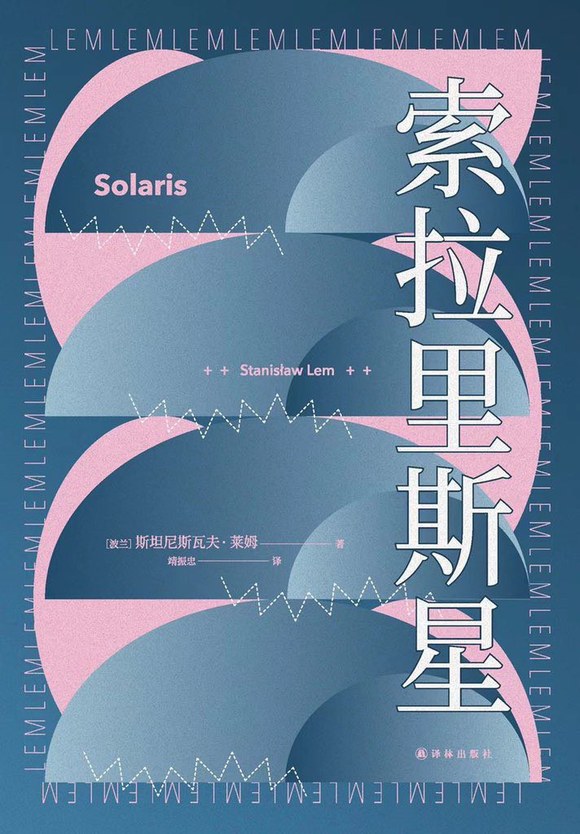
如果索拉里斯只是一片奇异的海洋,还不至于为读者带来不安的感受,在小说中,索拉里斯还会为每个踏上空间站的学者带来一名“客人”,“客人”是某位死者的复制版本,而这名死者通常来自于学者脑海中最深刻、最亲密的记忆。本书的主人公凯尔文教授的“客人”便是他的亡妻哈丽,凯尔文痛苦地意识到,这位哈丽根本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她一方面来自于凯尔文大脑中的潜意识投射,另一方面则显然是索拉里斯的造物,这让她成为了介于人与非人之间的存在,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恐怖之感。
然而,随着和哈丽的接触,凯尔文还是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同伴斯诺特提醒着他这样做的危险:“她只是一面镜子,如果她很美好,那也只是因为你的记忆很美好罢了。”
借斯诺特之口,莱姆在认识论层面揭示出人类伦理的局限,也顺便批评了“太空歌剧”式的科幻小说范式。他认为,我们寻找的并非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这样的世界已然超出了人的理解,我们渴望的只是在其他文明中找到自身的影子——当哈丽这样的他者出现,并展示出一些无法言说的真相时,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真相,而只能镜像地回看自我。理论著作《科幻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索拉里斯星》时也指出,莱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阿西莫夫,因为他在指出人类局限性之余,并没有急着寻求另一个可以依赖的外星人“上帝”,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迂回的路径来认识我们这个物种,并通过后人类哈丽的存在疏远了人们对现实的普遍认知。

正如凯尔文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了解“客人”哈丽,玛莎与被木卫一附身的波顿的沟通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通约性,这一点通过剧中大段的诗句得以体现。比如,在玛莎疲惫地向空间站跋涉、希望尽早获取氧气时,木卫一突然吟诵起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第五章的诗句,“睡眠啊!如此温柔,无人不爱”,让人无法判断这是一种慰藉,还是引诱玛莎睡去的说辞;而当木卫一说出那句“现在我用沉静的目光看到,恰是那机器的脉搏”,“具有脉搏的机器”这一悖论也提醒着我们木卫一那跨越了人与非人的模糊特质。
实际上,在华兹华斯的原诗《她是一个欢乐的精灵》中,这一悖论就已经展露无遗。诗人在诗中描写的是自己的妻子玛丽·哈钦森,他以三种不同的风格表达了对妻子的赞美:第一节中,玛丽是快乐的幻影,一个灵动却没有实体的存在;在下一节,她又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物,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最后,当诗人进一步了解过她的妻子,她成为了“机器”,一个“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过客”。通过这些描写,玛丽在诗人心中已经不像是真实的人类,而变成了一个完美却又不可企及的存在。
凯尔文对哈丽的爱犹如镜面,勾连出他内心深处的种种情愫。在《机器的脉搏》中,附身于死者波顿的木卫一对于玛莎来说也是一面镜子。当玛莎问木卫一它的功能是什么时,它回答道:“我是由你创造的,是为了认识你,爱上你,为你效力。” 这句话放在原著小说中或许更容易理解,在玛莎奋力跋涉的途中,她一直在回溯过往的心理创伤,并不停地把自己和波顿做比较——波顿比她更优秀,自己则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失败者,这既让她感到挫败,也激励着她奋力求生,直到求生的欲望也逐渐消弭,让她走向死亡。这个结局其实颇为可惜,因为在映射过自身并明白自己无法在认知层面与木卫一抗衡之后,她还是投身于一种宗教式的顿悟,但这可能已经是作者能够想到的最佳结局。
如前文所述,自洽、平衡的盖娅星系或许已经无法代表现如今的人类处境,我们不应该再将他者简单看作可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存在,而是要去承认人类伦理的限制。这并不只是虚构文学的异想天开,而对我们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随着地球气候危机的持续加剧,以往被认为是一个和谐整体的自然越来越频繁地爆发灾害,展露出极其不稳定、令人感到陌生的“非人”特质。面对这样的现状,人类学者布鲁诺·拉图尔重拾了神话中的盖娅概念,在著作《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中,他一反盖娅在人们心中慈爱、宽容的母神形象,而是认为她作为在混沌中诞生的第一位原神,是充满冲突、暴力且好战的。通过塑造盖娅的全新形象,拉图尔试图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并非人类的存在者,比如动植物、病毒和其他非生物,它们的活动正在影响着人类,甚至会挑战和颠覆人类的日常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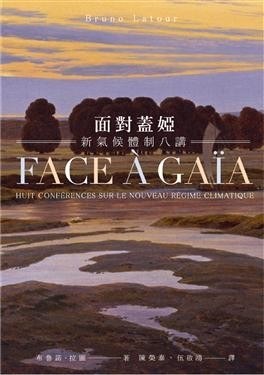
这样的盖娅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自然背景,也并不拥有“联合全世界”的渴望,她更像是索拉里斯的“客人”哈丽,或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死者波顿。当自然风平浪静时,盖娅让我们感到熟悉,但是她也会在暴风、洪水、森林大火发生时显露出令人惊惧的一面。同时我们会发现,盖娅也是一面镜子,认识盖娅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因为正是人类作为加害者导致了灾害的发生,也是人类作为受害者去承担其后果。这样看来,像《索拉里斯星》这样的科幻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寓言,而是正在发生的惊悚现实。
参考资料:
《后人类》 [意] 罗西·布拉伊多蒂 著 宋根成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6
《银河帝国6:基地边缘》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叶李华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0
《童年的终结》[英] 阿瑟·克拉克 著 于大卫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索拉里斯》 [波]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著 靖振忠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8
《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 [法] 布魯諾‧拉圖 著 陳榮泰 / 伍啟鴻 译 群學出版社 2019-7
《人类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基地系列”与 “三体系列”比较研究》 任祥辉 著 硕士学位论文 2020年
《科幻文学、外星他者与后人类伦理:评莱姆<索拉里斯星>》 王瑞瑞 著 中国文学研究 2019年第4期
The very pulse of the machine based off of Sol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