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的洪流中,怎样做到既共情他人又不被悲痛吞没,既保护自己又不滑向铁石心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030期主持人|徐鲁青
今年春天似乎格外沉重。俄乌战争、澳洲洪灾、日本地震、席卷全城的疫情,东航坠机……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涌来,每每刷上一阵新闻,就有末日不远之感,即使关上手机后,人也常陷入悲观情绪里。 "压力、焦虑、恐惧……"《卫报》给常看新闻的人开出了后果清单,讽刺的是,这篇文章也是巨大新闻信息流的组成部分。
许多研究都显示,负面新闻过载会诱发心理问题。“911”连续播放的灾难画面曾诱发观众的应激反应。在2020新冠疫情开始后,甚至出现专门的英文词Doomscrolling形容持续不断浏览负面新闻的状态,由此在全球引发了人们因看疫情新闻过多而抑郁的现象。佩雷尔曼医学院焦虑症研究中心的临床主任说:“人们有许多焦虑,想通过不断刷新闻找到心中的答案,并自认为能让自己舒服一点,但实际上总是感觉更糟糕。”

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新闻流,我们似乎更擅长遗忘了。今天为地震与核灾牵动心情,明天这些关心就被埋藏在记忆角落。情绪如潮水般随热点起伏,“过了时”的同情被拍死在沙滩上。面对他人的灾难我们只剩按秒计算的情绪波动,少有更深层的记忆与纪念——比如更进一步的行动,比如对更大机制与结构的反思,以此为未来的路提供某种参考。
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同新闻的关系比大多数读者更近,文化记者或许不像作者马尔克斯形容自己的记者生涯:“世事难料、随时候命”,但持续追踪与跟进公共事件必不可少,呈现与评析之责更不可开脱。总会有一个时刻,远方的消息如此直击内心,那时我们如何在职业属性与个人情绪中寻找平衡?在新闻的洪流中,怎样做到既共情他人又不被悲痛吞没,既保护自己又不滑向铁石心肠?

陈佳靖:这两年陆续看到全球各国的调查数据都显示,由于疫情原因引发的抑郁和焦虑的人口比例正在迅速攀升。人们担心的不只是健康,还有越来越难以维系的工作和生活,以及长时间缺乏人际交往和社会归属感。关注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与世界保持联结的方式,即便对于那些本身对公共事务不关心的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恐怕也很难两耳不闻窗外事,假装岁月静好。当然,要关注新闻就没办法完全避免负面消息,这些负面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冲击。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此回避这类新闻,但可以调整接收信息的方式,比如尽量不要重复去刷已经知道的负面消息,关注可靠的消息源以减少花费在信息甄别上的时间和精力,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有意识地戒断部分干扰信息,把重心转移到自己的生活和爱好上等等。
相对而言,记者对负面新闻的耐受力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好,但在新媒体时代,获取和吸收信息的难度都在增加,普通人看到一条负面新闻时,记者可能已经看过了几十条不同角度的同类内容,而且还要继续关注后续动态,分析背后的缘由,回答所有人想知道的一切。这里面的“工伤”是很难量化的,最终也只能被个人消化,所以更需要清楚自己能承受的边界在哪里,谨慎被情绪的洪水猛兽吞没。

姜妍:鲁青的设问主要谈的比较大的坏新闻,我从个人经验出发谈一点相对小一些的,就是逝者新闻和媒体从业者的关系。不管是什么领域的记者,都迟早要面对行业里逝者新闻的处理。如果去世的人和自己没什么私交,也没有投入特别的情感,可能还可以当作正常工作去操作,但如果是曾经非常亲密的采访对象或者是自己的偶像去世了,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印象很深的是前同事的两件事:一件是2009年6月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我当时供职报社的音乐记者是在公交车上从朋友发来的短信得知这个消息的,他瞬间泪流满面,杰克逊是他的偶像;另一件是一位老翻译家去世的消息传到办公室,我同部门的一位记者曾经做过这位翻译家的个人史采访,她也是马上红了眼圈。作为记者,除了悲伤,同时还需要面对的就是职业属性层面的逝者报道。音乐记者饱含伤悲写出了一版专业性很强的逝者稿件,而那位文化记者拒绝了这个工作,她说,“我太难过了,我写不了。”于是这个活儿落在了我头上。
我分享这两个小故事并不是要评判什么,而是想说,作为记者我们既有职业属性的部分,同样也有剥离职业回归到纯个体作为一个人的样貌。随着职业年头的积累,很多我采访过的文化人都陆续告别,我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甚至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合作最紧密的编辑同事也在2019年因为心梗猝然离世。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会把职业属性放在前面,在完成正常工作后,再去消化个体情绪上的起伏,但我也完全能理解当年因为悲伤无法工作的前同事的感受。
徐鲁青:我很容易被负面新闻流影响,有时候通过写稿缓解焦虑,制造似乎做了些什么的感觉(或者幻觉),更多时候是转发消息——也是“似乎做了些什么”。在极其严肃的事件前我总感到笔下无力,加之公共写作是一种权力,更让人惶恐不安。最近我第一次写逝者新闻,需要在很短时间里选择逝者一生值得记录的故事、理念,与成就,整理成不长的文章。写的时候一想到媒体稿件逝者家属可能会逐一阅读、收集,放在纪念盒子里(现在可能是电脑文件夹),我就压力巨大,自己何德何能做这样的盖棺定论呢?

董子琪:替代性创伤是有的,从2020年疫情刚爆发,到去年河南郑州的暴雨洪水。现在身处疫情的漩涡中,已经不能说是替代性创伤了,而是全身心地感知不安惶恐,短暂以麻木过渡,接着是更深的颓丧。但替代性创伤不正是儒家推崇的“仁”的表现症候吗?仁的核心要义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没有这种仁的基础,难以想象社会会被如何组织。
叶青:我觉得普通人每天能承受的坏新闻是有限的。从游戏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处在一个“满血状态”,那这几年无处不在的疫情就相当于一个大型长效“debuff”,我们本就在不断“扣血”,此时其他糟糕的消息加在一起,很容易变成最后一根稻草,给我们“KO一击”。这时候难免会产生逃避的想法:关掉新闻推送,不刷社交媒体,靠其他事情来分散注意力。这样当然没错,能让我们从压抑的情绪中暂时舒缓过来。但逃避是解决之道吗?坏事总会发生,岁月静好的安全泡沫终有一天会破裂。我们最终还是会回到现实中来,面对坏消息,或发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声音,或愤怒,或悲伤,总比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好。
潘文捷:看飞机失事的视频让我悲伤,熟人身上发生的苦难也会让我感到揪心。活着既有甜蜜也有痛苦的时刻,身而为人好像就是这样好坏参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更多地从一个功利主义者去思考问题。具体是这样的,边沁认为,“每个(人)都算一个,没有(人)多于一个,”每个个体的利益都应当予以同样程度的关怀,没有谁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更重要。既然有那么多的坏事发生,那么我就想办法让这个世界上发生几乎同等数量的好事,是不是心里就会没有那么难受?更加关爱身边的人,关爱动物,少吃工厂化养殖的动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无法抵销事实上发生的灾难,但只要有所行动,心情就会好一些。
如果说俄乌战争、日本地震、东航坠机这些新闻像是刺一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那么半数野生动物正在遭受物种灭绝威胁,全球气温不断攀升,垃圾泛滥成灾,10亿人在贫困线以下挣扎,15亿人过度肥胖……这些苦难大概就是煮着青蛙的温水吧。这些根本不算新闻,而已经是常识了。几乎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地球正面临着一系列难题甚至是灭顶之灾。人们一边对地球的灾难性未来高谈阔论,声称它会比世界大战还要严重,另一边却一成不变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我的想法是人类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迎接负面新闻,更要居安思危,来防止坏事发生。

徐鲁青:大家的讨论让我想到一个挺有启发的观点,传播学学者、媒体人方可成认为,人们在看新闻时倾向于关注坏的一面,然而过多的负面新闻却可能让人失去行动力,因为当我们过度悲观,觉得世界没有希望时,容易陷入“犬儒主义”之中,不再愿意做出改变与尝试。方可成提倡媒体生产更多的“解困式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即报道不仅关注问题,也关注人们为解决问题作出了什么努力,这样能激励更多人不被悲伤淹没,保持行动。
董子琪:我看到,已经有专家注意到了封锁限制、疫病恐怖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建议大家保持规律的生活、健康的作息。专家建议固然是好的,至少提到深层精神震荡的可能——这点通常被强身健体盖过了,也经常被当成闲情逸致的笑谈。然而我还是觉得,这种建议只是接受规范好的现实,而不是理解或建设现实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消极的)。
以我浅薄的人生经验看来,接受而不理解,即使能够抵达平静也不能持久。我需要去理解,人的心灵和智慧都需要有沟通才不至于淤塞干涸。如果说这些抑郁能带来什么,就是以高密度的感受和不容抵抗的方式促使颅内燃烧。我去读了一些之前不感兴趣的思想史的著作,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有五四时期青年人感到苦闷的主题文章,陈独秀的《自杀论》回应的是由于困惑而出现的青年自杀事件,钱穆也有文章分析学生的自杀。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关心这些问题的时候难道是在关心旁人吗?思想史与生活史合二为一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一个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治学,才有切身之感,才能学而为己。近来看到许纪霖说发觉研究生做论文主题有时代变化的印记,年轻人好像对思想史和苦闷的研究更加重视,我想这也是一种外感内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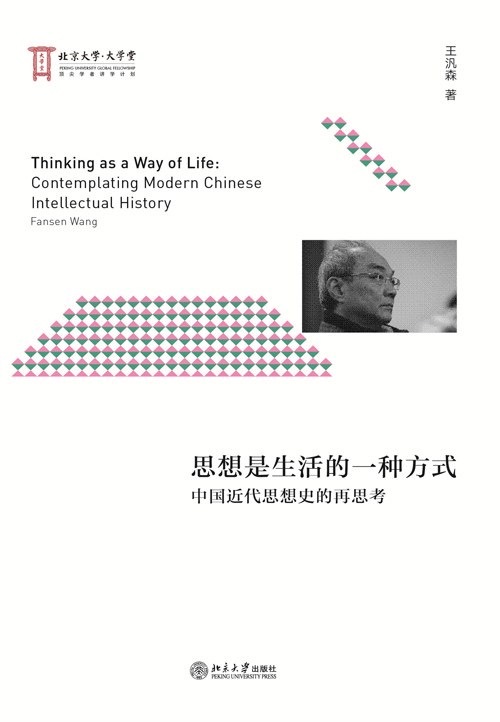
林子人:去年读了《亚当·斯密传》,这两日读了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莱恩·帕特里克·汉利的《伟大的目标: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再次深刻感觉到亚当·斯密或许是我们时代最亟需重温并从中发现思想资源的思想家。在《伟大的目标》一书中,汉利援引了《道德情操论》开篇的第一句话:
“无论一个人多么自利,他的天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则引导他关注他人的境遇,让他人的幸福成为他自身幸福的必要条件。”
汉利指出,虽然我们如今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斯密是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自利论的奠基者,但其实他希望我们从对他人的天然关切出发考察人类的道德生活。而且他激进地认为,我们天性之中对他人的关切与同情足以使“他人的福祉”成为我们的“必要需求”。在斯密看来,一个人的福祉和另一个人的福祉并不存在零和关系,如果我知道你的境遇悲惨,我自己也不可能全然幸福。
早在新闻行业诞生之前,人们就在以各种方式传递和获取信息。当然,古人所关心的“世界”放在今天或许只相当于一座村庄或一座城市,但他们依然对“我的生活之外发生了什么”怀有与我们相同的好奇。我认为这种好奇就源自我们天性之中对他人的关切与同情,这驱使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愚行与苦痛,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新闻行业诞生和存在的理由,而在一些更理想的情况下,这还是社会变革的起点。我们可以批评新闻行业从业者在具体实践上的不当手段,但唯独不可以质疑人们想要获取信息、了解内情的欲望,以及为此存在的新闻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