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认为,在扬弃传统中国法律中对妇女道德压迫的内容之余,我们也应当看到传统法律“仁治”理念中保护弱者、重视家庭等道德关怀的重要性。

1793年,马葛尔尼使团随行成员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中国妇女和她的儿子。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记者 |
编辑 | 黄月
2013年,赵刘洋曾在苏北某村从事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搜集到近三十年来该村的自杀案例。当代基层社会的妇女自杀案例与他在档案馆中看到的18世纪清代诉讼档案产生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呼应。于是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中国基层社会自杀行为者往往是女性,这与不同时代的法律构造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大清律例》中关于婚姻尤其是“离异”的法律主要分布于“户律·婚姻”和“刑律·犯奸”中。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赵刘洋发现,清代涉及婚姻纠纷和奸情(如买奸、卖奸、买休、卖休)的案件数量非常庞大。当时的底层社会买卖妇女、一妻多夫的现象屡禁不止,且部分地方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18世纪的清廷又极端强调妇女守贞的重要性,甚至在法律层面鼓励妇女为了守贞采取极端行动——在有一类案件中,妇女若遭到调戏而自杀,调戏者将被依照律例处以绞监候,妇女则会得到政府的旌表。
清代法律愿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被赵刘洋记录在《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一书中,这也是他研究妇女权利相关法律史的起点。该书贯穿清代、民国、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四个阶段的法律社会史,探究不同时期的法律实践与妇女权利保障之间呈现的种种张力。

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考察中国法律史,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的进步朝着去等级化的方向缓慢前进,然而文化惯性往往顽固地遗留在社会观念、习俗规则乃至法律之中,即使在今日,我们依然需要呼吁加强法律实践对妇女权利的保护。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赵刘洋反复强调,在扬弃传统中国法律中对妇女道德压迫的内容之余,我们也应当看到传统法律“仁治”理念中保护弱者、重视家庭等道德关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提醒我们注意,法律在被社会观念变迁推动修正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观念的转变。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或许能够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界面文化:《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贯穿清代、民国、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四个阶段的法律史。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研究当代妇女法律地位变迁的意义是什么?
赵刘洋:贯穿这本书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从传统儒家仁治理念去看中国妇女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地位问题。西方性别史研究学者特别突出传统社会中妇女的主体性,我在书中则强调传统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她们既非简单的被动—受害者,但和主体性也相距甚远。第二条线索是(中国)法律演变是否仅仅在往个人权利理念的方向发展,比如婚姻和家庭越来越像一个私人领域,是否就意味着妇女权利就能实现相应保障了呢?从长时段视野去看待妇女权利的演变,其实是在回应上述两种看待妇女权利问题的主要理念。
单一以上述一种理念去理解妇女权利都存在问题,我在回应和批评这两种理念的最终目的是强调,保障妇女权利一方面需要个人权利理念,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和考量弱势群体的道德原则,融合权利理念和道德原则。与此同时,法律应当面对社会实际情况,处理好和道德的关系,从书中对妇女自杀和离婚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简单的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去道德化做法,都会造成相应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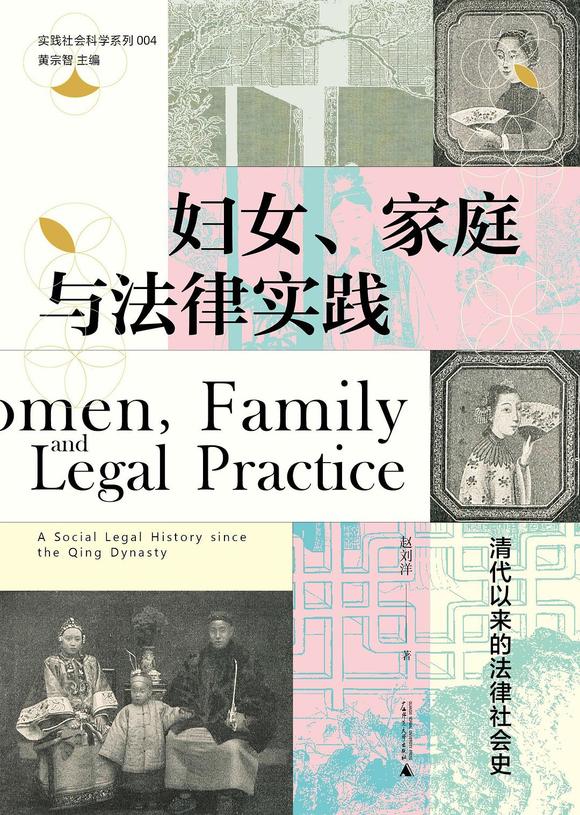
界面文化:此前我们采访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他提到传统中国对法律的理解与今人完全不同,大量判牍显示,判官做裁决时考虑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情”“理”“法”的结合。你在《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的导论部分援引了滋贺秀三的观点,他也以“情”“理”“法”来概括清代诉讼制度的民事法律渊源。能展开谈谈这三者的区别与联系,以及这三个方面是如何影响帝制中国的法律实践的么?
赵刘洋: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时期民事法律判决的学者中一个争论比较多的话题,黄宗智和滋贺秀三是其中一个著名争论。在黄宗智看来,传统中国的民事判决有一部分是依据清代律例来进行判决的,同时他认为,还有一部分民事诉讼是通过社会调解进行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二者交接过程中解决的,县衙判决和民间调解并非截然对立。滋贺秀三则突出传统中国法律类型和西方法律的对比,认为民事法律是“情”“理”“法”的混合,和权利理念主导的西方法律类型不同。这种争论与他们各自的研究旨趣有关,黄宗智主要从社会史角度去理解,滋贺秀三更突出的是中西法律类型的对比。
清代的法律判决其实比较复杂。如果婚姻、土地等纠纷涉及命案,清代的判决严格遵守律例,且要经过逐层审核,涉及到命案的案件甚至要一直上报给皇帝。但如果是单纯的婚姻、土地、分家等民事纠纷,上级官员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和监督就没有那么严格,会给予县衙或地方官员一定的自主权。在县衙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如何把纠纷处理好,息事宁人,让各方都不会继续上诉。在民事案件里,如何将一个案件处理妥当,官员会综合考量各种不同因素,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个案中的复杂因素,比如当地的具体情况、社会习俗、各方看法等等。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官员在处理案件纠纷的过程中要求综合考虑地方性知识和法律条款。当然,如果是明显违背律例的情况,地方官员也不太会冒险完全按照习俗来判决。另外我们知道,清代的律例本身也已纳入“情”和“理”。
界面文化:美国历史学家任思梅在《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一书中指出,在人口贩卖相关法律中,清代律例纳入了大量“例外情况”。这是否意味着传统中国在法律层面也有某种“情”“理”“法”的混合?
赵刘洋:是的。清代的律和例是有区别的。律的主体部分在之前的朝代里已基本建立完成,从唐代开始不断发展完善,是更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那部分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例是在不断地增加和修订的,这里面就会有例外情形或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案件类型。地方官员在判决过程中如果出现疑案,会上报到刑部甚至皇帝,最后可能会以例的方式被纳入大清律例中,为之后的官员判决类似案件提供某种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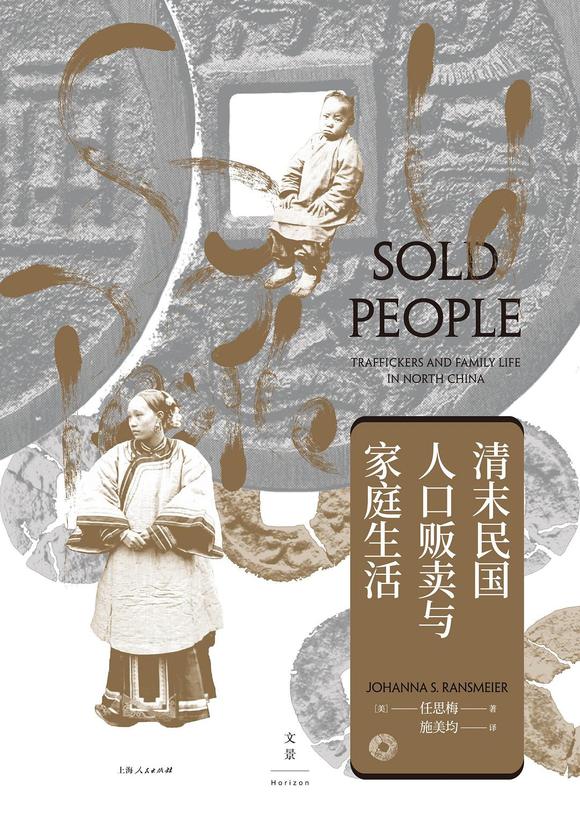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对韦伯式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念的批评是,它倡导一种去价值化、去道德化的法律,未能看到中国传统法律包含的儒家仁治观念,即对弱者保护、对家庭道德观念的重视。如果我们认同瞿同祖的观点——“法律儒家化”的实质是以法律维护儒家等级秩序——那么这种法律哲学中的“仁治”似乎势必建立在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要求之上。请再解释一下你的观点?
赵刘洋:儒家仁治理念不仅包括等级制压迫,也包括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保护。瞿同祖在著作里也讲到了,清代律例中传统中国的仁治理念不单单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比如父对子),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弱势方(比如子)如果犯明显违背社会道德或清代律例的错误,对强势方(比如父)而言是不能随意压迫或随意违背自身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婚姻中的“七出三不去”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方面,丈夫对妻子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象征着夫权对妇女的压迫。但另一方面还有“三不去”,这意味着丈夫不得违背自身承担的义务,随意欺凌妻子或违背自身义务。
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18世纪商品化发展和社会流动性增加,阶级维度的不平等在弱化,18世纪以后两个阶层之间发生纠纷的案件其实数量非常少,通常是农民和农民之间的纠纷,清代法律案件比较少看到农民和士绅发生纠纷。雍正时期废除了贱民制度,传统社会等级制不断弱化。进入近代,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在阶级方面可以说已经打破了传统中国对等级制的要求。
近代以来的法律发展趋势是往去等级化、平等的方向发展的。但在抛弃等级性内容的同时,法律还要考虑仁治理念中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和道德考量。如果我们同时也抛弃了实质正义的理念,我想也并不是法律建设的理想目标。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把道德纳入法律造成压力,或法律的去道德化,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都有可能造成相应的问题。
界面文化:在当今社会,我们真的有可能用法律去阻止道德滑坡吗?在法律中召回某种“道德主义”是否有可能会反过来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压迫?
赵刘洋:倒不是说召回道德主义。我突出强调的是,法律需要面对社会实际情形。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到法律中已经包含的道德原则的真正适用,不应该简单地抛弃。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应该也要充分考虑它们原则性的指导作用。比如说《婚姻法》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原则,当今法律判决过程中,对家庭原则、性别平等等方面的关切本身就是法律体系之中的一部分内容。我们是需要考虑到它们的指导性作用的,而不是简单地忽略法律中的道德原则或者形式化一刀切的做法。

界面文化:我们要如何理解清代法律层面对妇女贞节的强调和现实层面妇女卖休层出不穷的矛盾?
赵刘洋:确实如此。如果去第一历史档案馆你会发现两类案件的数量非常庞大,一类是婚姻家庭,一类是婚姻奸情,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专门卷宗。一方面,清代非常重视和强调妇女贞节问题,如果符合官方的旌表制度标准,地方官员特别乐意上报为贞妇求旌表,这是清代官员的一大政绩。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社会中有非常多妇女卖休案件。我们需要认识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清代法律监管是比较严格的,由于地方官员很重视婚姻奸情这一类的案件,这些案件就会被大量纳入官府的关注之中;第二,清代官员在监管能力上是比较弱的。比如萧公权就指出,19世纪一个县官要管理将近25万人口,这种监管能力要达到目标是比较困难的。
上述两类案件数量庞大有其背后的社会原因。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激增至近2亿多人口甚至更多,人地比例紧张伴随着商品化不断发展,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人口流动性增大,从清代的法律档案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因为贫困要去外地讨生活。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底层社会民众之间的接触变多,造成越来越多的案件纠纷。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乾隆时期对妇女贞节的强调其实是为了应对18世纪人口激增和商品化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的挑战。通过妇女贞节和家庭道德的强化和重视,对变动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监管和安排。
界面文化: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对妇女贞节的制度性强调其实远远早于清代,比如从元代开始,法律就禁止遗孀将其妆奁从夫家带走,反映了蒙元对家庭经济稳定性的强调和重视。我们是否可以说,18世纪的法律变化其实是女性商品化历史趋势的延伸?
赵刘洋:类似卖休的案件类型确实不是清代才有的,各朝各代一直都有。我想强调的是,18世纪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时期,和以往相比,这一时期清政府通过种种方式强化了社会监管。比如康熙和雍正并不支持妇女为了获得旌表“舍生取义”,他们都曾专门发布谕旨告诫地方官员停止对殉节妇女的旌表,不要在社会实际情况中造成因为守节自杀的案例。但乾隆有所不同,他对妇女的道德贞节非常强调。

界面文化:任思梅认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法律改革者都未能在法律中根除儒家等级制和交易型的中国家庭的影响,这是妇女法律权益无法切实得到保障,特别是人口交易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原因。你对此怎么看?
赵刘洋:和同时期的欧洲法律相比,民国时期国民党颁布的法律在性别平等原则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实际效果方面对普通民众生活影响比较小,法律的贯彻力不行,这和当时的国家能力有关。
民国时期的妇女拐卖案件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方面,社会中等级制并未被清除,妇女和儿童在家庭等级中的地位较低,容易被卖;另一方面,民国的拐卖案件很复杂,比如迫于生存压力的妾、童养媳和佣人等往往和拐卖密切相关,拐卖案件在法律实践中认定困难。民国时期人口买卖涉及的因素很多,这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
最近恰巧为任思梅这本书的中译做最后校对,从她的著作中的案件材料也可以看到,社会中底层贫困、溺女婴加剧了性别失衡状况,这些社会问题都会对人口买卖问题造成影响。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民国时期“妾”在法律实践中往往被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妇女离婚诉讼请求经常会被法院认为缺乏“法定理由”而驳回,然而法律也未禁止男性不得纳妾。可见当时的法律是有漏洞的,不利于保护妇女法律权益。
赵刘洋:民国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妾的身份没有在法律上被明文禁止,但同样也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纳妾的行为在民国时期处于法律的漏洞之中,法律对此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这造成的一个问题是,民国时期妾的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这和当时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在法律层面,民国越来越趋于性别平等,但在社会层面和观念层面又保留着很多传统社会的问题。民国的法律制定者可能认为涉及面太广,没有对过渡情况进行明确的法律处理,也造成了相应的问题。
界面文化:1950年婚姻法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1950-1960年代婚姻法的实践(离婚判决)的起伏反映了法律愿景和现实社会之间怎样的张力?
赵刘洋:1950年《婚姻法》在法律原则上非常突出强调平等原则和子女的婚姻自主权,而且规定妇女可以主动离婚,这对扩大女性在婚姻家庭纠纷中选择的权限非常明显。《婚姻法》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在颁布后紧接着开展了全国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以政治运动方式推进妇女权利保障。和民国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民国法律虽然在法典层面非常强调性别平等原则,但它在基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乡村社会保留着传统社会的诸多习俗。但1950年《婚姻法》颁布之后,国家干预和政治动员对当时的不平等婚姻压迫案件的解决,起到了很多重要作用,其贯彻力远远强于民国时期。

新中国《婚姻法》在实践过程中做了诸多调整。1950-1953年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主要是为了打破原来不平等的婚姻,重点解决对妇女权利有压制和影响的离婚案件。1954年之后,司法部门认为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而且认为这时出现很多“没有合理理由”的离婚案件,比如出轨方主动要求离婚的案件。为此,司法部门认为要严格限制离婚案件的增加,进入严格判决时期。到了60年代,生存压力冲击着婚姻稳定,婚姻买卖和妇女再婚案件增多,法律面对实际又显示出宽松立场。为什么出现这些变化?主要是社会情形在不断发生变化,法律的预期会影响社会,社会变动之后又会对法律形成新的要求和挑战,法律在不断的社会变动中寻找平衡。
界面文化:1980年《婚姻法》修订,在1950年的离婚条款“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的,亦准予离婚”一条中加上了“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离婚条款是如何影响婚姻自主的?
赵刘洋:1980年婚姻法修订把这一条明确加上,其实不是新鲜做法,在改革开放前民事判决实践中已经很强调这一点了。在我看来,这是把之前的审判经验汇总,纳入正式的法律条文中。更为重要的是,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详细列举了感情破裂的14条认定标准,包括“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或者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也是对以往审判经验的总结。

“感情确已破裂”这一条件其实给予了法官某种裁量权,法官审判既可以宽松,也可以严格,需要依据夫妻的实际情形去做安排,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标准的尺度可以自行决定,加之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一刀切”和形式化的问题,比如法官面对庞大的案件压力,面对第一次提起诉讼的一律判决不离,第二次就判决离,这种形式化的做法会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上造成很多问题。对于“感情确已破裂”的认定很考验法官的智慧,法官需要以更认真的态度去调查和处理。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在离婚判决依据、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方面,源自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面对社会实际的实用性考虑与实质主义的道德理念相结合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仍然延续。我们要如何理解“实用道德主义”?
赵刘洋:是说婚姻家庭案件有其特殊性,要避免简单化的做法,任何一刀切简单化的做法都会造成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法官能够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处理。法律的规则毕竟是比较抽象化的,但司法实践中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处理,综合把握各种考量,以此推动婚姻家庭案件能够取得符合实际情形的稳妥结果。
界面文化:书中最后一章所讨论的当代中国离婚法律实践中的房产分割是当下最受关注的婚恋话题之一。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布后,法律首先考虑的是财产分割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亲原则,该条主要目的是防止因子女短暂婚姻而带走父母一半的积蓄,损害出资父母的利益。当下的《婚姻法》似乎同时呈现出家庭主义(血亲利益优先)和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私人财产保护优先)这两个面向。从女性角度来说,假如女性所能掌握的财产、经济收入和家族支持不如男性,女性的利益反而会难以得到保障。你对此怎么看?
赵刘洋: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在血亲和姻亲之间选择了(保护)血亲(利益),也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优先。这样规定主要原因是,现在人们对婚姻的预期比较低,如果一对夫妻结婚半年就离婚了,考虑到现在的高房价,一个短暂的婚姻就有可能带走父母辛苦积攒财产的一半。在司法部门看来,选择血亲优先原则是在保护父母给予子女的财产赠予。
这个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影响是妇女权益保障受损,比如一个女性结婚多年,房子是男方父母在男方婚前给他买的,多年后离婚,女方也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但她分不到房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法律实际上也在给予人们一个观念,即女性也要有自己的财产和房产,这就有可能推动整个社会观念的变化。女性的父母和女性自己会开始重视拥有自己的财产,也许整个社会对女性财产权的保障会发生观念上的变化,由此可能推动法律制度出现新的变化。
法律并不是在真空之中的,它既会受到社会影响,也会起到引导社会观念的作用。社会观念中人们对婚姻的预期较低,影响了《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但另一方面,关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和解释又有可能造成社会观念的调整。如今女性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说是更加重要了,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女性对这方面也越来越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