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斯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社会公平,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记录和分析普通人的能动性和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制造的意义,重新定义阶级,将失意者拉出民粹主义的陷阱。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汉默镇,有12名工人阶级出身的男校中学生。他们抵制权威和教条,厌恶勤奋、谦恭、尊敬等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并因此鄙视和攻击将这些价值奉为圭臬的好学生,称他们是“书呆子”或“软耳朵”;他们处处和老师对着干,用破坏课堂秩序的方式“找乐子”,比如在课堂上打盹、哄骗老师和逃学;他们打扮入时,抽烟喝酒,以此吸引女孩的注意力,与身穿沉闷制服的“书呆子”区分开来;他们自恃优越于女孩和少数族裔,认为体力劳动是男子气概和优越性的证明,脑力劳动则是缺乏男子气概的“女人的差事”。最后,他们吊里郎当地混到毕业,不假思索地子承父业,走上了从事工人阶级工作的道路。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把他们称为“家伙们”(the lads)。1972-1976年,威利斯持续跟踪这群男生,试图解答一个疑问: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如何能够在处于从属性社会地位的同时保有文化自信?威利斯发现,他们参与塑造并产生深刻体认的反学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工人阶级父辈车间文化的镜像。家伙们借助于仪式、幽默、哄笑等感官手段和符号以及人工制品的特殊意义,来探索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身份。
威利斯认为,这些具体实践都是工人阶级子弟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的一部分——它们虽然极具创造力和自主性,却又是缺乏自我认识的。家伙们质疑教育和文凭的价值,认定自己面对的所有工作都是类似且无意义的,诸如此类充满局限(limitation)的“洞察”(penetration)产生了一个充满讽刺的结果,“恰好往往是他们自主性的一部分为自己盖上了宿命的封印”,让他们自愿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从属地位,由此完成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即工人阶级的自我复制。1977年,威利斯的《学做工》出版,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突破性”人物的历史地位。谷歌学术搜索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学做工》已被引用逾2万次——对于一部研究十几位英国白人工人阶级男学生的作品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不经意间,威利斯成为了“工人阶级文化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见证者。1970年代的西方处于二战后社会经济秩序的尾声,工业扩张、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曾在20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里让工人阶级不失体面,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后工业主义在西方造成毁灭性破坏,英国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成为了第一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的国家。在过去40年里,西方工人阶级劳动者(特别是男性产业工人)通过体力劳动获得可靠和体面工资的可能性降低。“工人阶级的衰落”如今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重要的政治后果,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和对精英的普遍怨恨。
2014-2017年间,威利斯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这给了他机会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观察校园如何复制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为年轻人奠定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虽然威利斯有意保持他一贯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但由于他在重点大学能接触到的大多是通过了严苛高考考验的标准好学生,他的中国研究更多是通过在《学做工》中一笔带过的“循规生”的视角展开的。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进入现代》(Being Modern in China)一书中,他借由三次田野调查和学生提交的个人经历文章发现,中国现代化的“象征秩序”由三条轴线构成:城市梦、消费主义和互联网梦。对于通过高考的学生来说,他们往往在中学阶段就完成了现代性的这一文化想象。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威利斯表示,中国的飞速发展——大规模的进城潮、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工业生产流程的重组和信息经济的兴起——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下的中国年轻人。根据他的观察,与英国人重视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人更多是从城市/乡村二元的角度形成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在一个儒家文化留下深刻烙印、人们自古以来就深信教育赋予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国家,要在中国的中学找到类似于家伙们的那种反学校文化或许相当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学做工》对中国读者的意义有所削弱。随着“内卷”“躺平”成为年轻人的新热词,“教育改变命运”的优绩制信念出现动摇,《学做工》中关于从属性阶级社会再生产的讨论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和分析工具。
即使身处不利地位,人们依然会积极地从周边汲取文化资源,以便自己在社会阶梯上占据一个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优势位置——这或许是四海皆准、亘古不变的普遍人性。然而在《学做工》出版45年后回望这部作品,至少对白人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文化想象已经和社会现实越来越脱节,正如威利斯在《25年过往:老书,新时代——写于<学做工>出版25周年》中所写,“他们不得不常常不情愿地或满怀怨恨地承认自己是一个近来‘引人注目’的族群,因为他们失去了殖民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继承(白人)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体面的工资所赋予的优势,他们也不再自动地认为获得这些优势是理所当然的。”威利斯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社会公平,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记录和分析普通人的能动性和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制造的意义,重新定义阶级,将失意者拉出民粹主义的陷阱。
界面文化:你曾经说,“《学做工》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本奇特的书,我没料到它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在出版后,这本书被广泛阅读、讨论和引用,如今《学做工》45周年纪念版即将在中国上市。你有想过为什么它能引起那么多英国以外的读者共鸣么?
保罗·威利斯:我相信是因为这本书的数据和写作的深度与质量。民族志对我来说一直和文学写作有些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今无论在哪里,研究者都几乎不可能像我当初那样深入地进入一所学校进行田野调查了。在西方学界,出于伦理考虑,学者是不能有如此长期的沉浸式研究的。
一个更循规蹈矩的回答是,这个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结合了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这两个维度的分析,这让它与众不同。它在承认工人阶级子弟的尊严和主体性的同时,也解释了他们屈从性社会等级的命运。安东尼·吉登斯(记者注:Anthony Giddens,英国社会学家)将这本书作为他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的主要例证可能也有帮助吧。
大多数关于《学做工》的书评和简介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压制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这个面向,忽视了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这一切只会在自觉性的行动和创造性的时刻中才能实现,而如果这些人被置于一个不同的环境,他们是有可能取得不同的结果的。
界面文化:分析学校教育如何促进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是这本书的核心。多年后回望这部作品,你恰好在新自由主义和后工业化时代来临前夕做了这个研究。当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差距还没有明显到剥夺工人阶级职业和身份的吸引力。如今重温《学做工》,我们该如何将这本书中的发现应用到当下教育系统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情况?
保罗·威利斯:将《学做工》中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案例、对当下结构性现实的认识,以及对人类团结和人类主体性的尊重结合起来——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当下语境内涌现出这样的研究。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希望搞明白的一个问题是,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如何能够在处于从属性社会地位的同时保有文化自信。从那时至今,工人阶级经历了种种变化和重组——无论是在种族、民族还是性别意义上——但我相信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依然在发生。

我在书中提出的一组关键洞见是种族、性别和阶级必须结合起来理解。我观察到阶级的引领性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种族和性别维度的经验、文化和政治就不重要了。我注意到,男性气概(masculinity)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时的阶级、性别、性取向和种族对立所塑造和影响的。如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成为了一个“新”概念,而我差不多50年前就讨论同样的问题了。但我们依然缺乏理解的是交叉性中的各个方面是如何缠绕在一起的——比如诸如身体/精神的区分之类的二分法——特别是教育系统在其中如何起到作用。在《学做工》中我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除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以外,也在深刻塑造性别和种族。
阶级之所以只在分析意义上占据头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在于它是种种(社会)变化和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高薪工厂工作机会的流失、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优劣)对比,以及教育市场化都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分析基础,相比之下,种族和性别维度的变化没有那么显著。目前的问题在于,自下而上的社会再生产新形式,已经和当下主导性的社会与物质结构以及它们所允诺的机会脱钩了。这导致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长期危机,即国家盲目且无效地试图通过教育、社保和警察系统管理人民,然而如果我们缺乏批判性的文化分析和指导,人民将深受“受害者有罪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否定之苦。
界面文化:书中对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非常有趣。通过他者化女性,家伙们将体力劳动与男性身份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女性一直是社会焦虑、失落和剥夺感的替罪羊。工人阶级男孩在多大程度上要为四处弥漫的厌女情绪负责?工人阶级女孩们是如何调和这种张力,并理解她们的身份的?
保罗·威利斯:我们在谴责工人阶级性别歧视的表达和后果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改变不会只通过唯意志论(voluntarism)和政治行动发生,还需要像《学做工》这样的文化分析作品去深入理解性别歧视及交叉性产生的物质背景。我们需要沿着婚姻、家庭、单亲家长等思路去做更多的研究。
整体而言,英国工人阶级女孩的处境要稍好一些,她们的非正式文化生产(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对劳动权力的主观认识)和新经济环境为她们提供的机会是相匹配的,如今工人阶级女孩的工作机会要多于工人阶级男孩。
在以前,工人阶级至少拥有稳定且较为体面的带薪工作、一些权力和自主性,尽管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一个屈居于下的阶级,社会再生产依然能够平和顺利地运作,源源不断地为工人阶级输入新鲜血液。我想强调的是,今时不如往日,从属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已经出现危机——工人阶级不再必然能够获得令人满足的结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失业,一部分人只能在低薪且无保障的工作中挣扎)。在非正式文化的层面,一个持续性且难以解决的危机正在蔓延,而这似乎没能引起官方的注意。无论官方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应对非正式社会再生产危机导致的后果和社会难题,比如试图降低民众对学校教育的预期,或让民众提前做好就业环境恶化的准备。
界面文化: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后工业化发展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则让我们注意到工人阶级的衰落和怨恨。这些事件是如何改变工人阶级文化的?
保罗·威利斯:特朗普主义和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是工人阶级经验/文化和工人阶级“管理”手段中的威权主义和阶级瓦解趋势做出的回应,而非根源。目前来看,特朗普主义/英国脱欧主义与工人阶级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呈现出彼此强化的态势。

界面文化:一些学者警告称,随着自动化和财富分化愈演愈烈,体力劳动者将率先承受自动化的冲击,工人阶级的未来将更岌岌可危,而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作也将面临同样的风险。与此同时,零工经济的兴起正在解构“全职工作”的概念,这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我们到了重新定义“阶级”的时候吗?
保罗·威利斯:我们一直都需要重新定义阶级:文化和物质基础之间的辩证法是一条线索;物质基础的变化本身是另一条线索,我们需要以交叉性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既看到种族和性别关系的变化,也看到教育系统如何调和与改变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分化。
界面文化:你曾指出如今社交媒体是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能再展开谈谈这个观点么?
保罗·威利斯:在文化的层面上,《学做工》出版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文化商品和商品拜物教在流行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愈发关键。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同样也在深远地影响和塑造工人阶级文化——或许如今应该被称为劳动者文化(culture of workers)或大众文化(culture of the popular classes)。50年前,《学做工》发现了流行文化/风格/时尚/商品化休闲(对塑造工人阶级)的影响和作用,但当时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还不存在。
在《中国走进现代》(Being Modern in China)中,我认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文化自我生产的工具,并且为年轻人提供了任何政党或教育都无法提供的东西——满足“寻找我们生活的见证者”这一强烈的人性需求。当然,这其中充满了矛盾冲突,而文化生产往往脱离创作者的掌控,被FAANGs(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和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超级大公司收割利用、谋取难以想象的巨大利益。在未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政治的首要任务之一都是(普通人)夺回文化生产的控制权。
界面文化:你的新书《中国走进现代》讲述的是中国的现代性与学校文化之间的关系。这部作品与你之前的作品有怎样的联系?你在中国是否发现了一种类似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在这本书中,你更多关注的是校园中的“循规生”(conformists),这一理论焦点的变化如何影响你的分析?
保罗·威利斯:在理论视角和研究兴趣的方面,我的不同作品之间显然存在联系。我带着一组研究问题和关注话题来到中国。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它的工业化/城市化速度非比寻常,使得6亿多人脱离贫困,并且在社会结构意义上(如果不是文化意义上)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工人阶级!
我尝试保持一贯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但由于我完全不会中文,这变得非常困难。我的确有一些田野调查的尝试并且将它们记录在《中国走进现代》中,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依靠的是二手资料,特别是关于“叛逆生”(non-conformists)的二手资料。由于我在中国大学里教书,我自然能够在我的学生中找到许多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循规生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过去的理论视角,即关注社会从属群体在文化生产中的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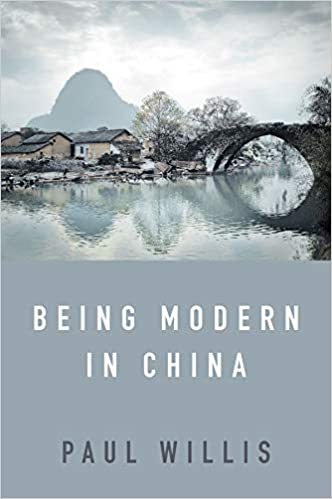
在《学做工》中,循规生更多是家伙们的陪衬,但我从未怀疑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生产。我对文化生产的理解至少在理论层面一直包含社会主导性的文化生产,但它们的方法、形式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很有可能非常不同。在《中国走进现代》中,我观察和分析了(循规生)个体的文化生产过程,让我有些吃惊的是,主流文化中的意义和信息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张力,无论是来自城市还是来自农村,忙于个人提升的好学生也在积极地参与文化生产。
界面文化:和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与最新的经济趋势(比如知识经济、零工经济)携头并进。在你的观察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重塑了中国年轻人对社会秩序的认知?
保罗·威利斯: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历了英国过去250年经历的变化。我不是很了解过去的中国,但我看到如今的中国年轻人被物质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同步变化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大规模的进城潮、不可思议的生产力提升、工业生产流程的重组和如今无重经济(记者注:weightless economy,即信息经济)的兴起是物质和结构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目前我们几乎不可能给中国的工人阶级下一个明确定义、给出某种结构性描述。在纯粹客观和结构性的层面,制造业岗位和带薪产业工人数量的大幅增长带来了一个向工业资本出卖劳动力的群体。如今的中国和过去40年里的英国一样,都在经历类似的去工业化。一如美国,中国东北地区也在形成某种“锈带”。近年来出现的“越南价格”夺走了一部分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这些还只是物质层面的分析,文化秩序、文化形式和对物质秩序意义的理解如何塑造阶级,这一方面的剖析难度会更上一层楼。相较之下研究西方是多么简单啊!中国的工人群体是一个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但不是一个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缺乏自主意识——而后者是我分析“文化秩序”的基础。
中国和英国情况迥异,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公众意识中阶级的存在感并不强烈,最重要的或许是进城的农村移民、与户口制度绑定的城市居民身份这些在物质和文化经验上造成巨大农村/城市区隔的因素。文化商品崇拜和社交媒体的(文化)自我生产也非常重要。再考虑到中国的超大规模和城乡间的发展不均衡,给中国的情况下简单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你可以发现一些与西方社会类似的元素和社会动态,但它们的“化学成分”是非常不同的。
考虑到中国强劲的流动性和显著的地域差异,我认为可以从地域、城市化程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维度去区分不同群体。在个人生活经验之外,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认识是非常不同又非常有限的。在《中国走进现代》中,我用“感性的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来描述当今中国人所经历的原子化和社会分离——这是我从T.S.艾略特的文章《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中借用的词。艾略特用这个词来形容17世纪英国诗歌中智性思考与感受经验相分离的情况。当然,我们必须记住“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的力量(我在2022中文版《学做工》前言中提及了这一点)和从属性(阶级)文化生产的力量。中国也许正在形成新的阶级形式和社群纽带,这是我试图在《中国走进现代》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