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仍未完全实现的当下,扭曲女性自我和同性友谊的土壤依然深厚。

《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剧照 来源:豆瓣
025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春节假期的时候我读完了《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广泛存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关注的问题:女孩之间的霸凌。首先要澄清一点:女孩的霸凌行为和男孩的霸凌行为存在很大的不同,后者通常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打架斗殴、言语冲突(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了解的霸凌形式),但前者往往是“隐性”的,表面上看女孩之间风平浪静,但背地里会展开“隐性攻击”,具体表现包括说闲话、传谣言、排斥、辱骂、冷暴力、操控等方式,引发受害者的心理痛苦。《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作者蕾切尔·西蒙斯在美国中小学展开长期调研后发现,霸凌行为在10-14岁的女孩中最盛行,与通常欺负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男孩不同,女孩攻击的对象往往来自亲密的朋友圈:
“在女性友谊亲密无间的背后,隐藏着一片弥漫着愤怒的秘密土地,而滋养这片土地的,正是沉默。”
西蒙斯认为,“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长久以来,女性都是依靠与他人的社交关系来加强社会地位的,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是“与人为善”“以他人为中心”的性别范式。所谓的女性之间的敌对与恶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女性不被鼓励直接表达负面情绪、正面应对冲突,于是在潜移默化间习得上述性别范式的部分女孩,转向了以摧毁对方社交关系为目的的另类攻击方式。在西蒙斯看来,“如果竞争和渴望不能通过健康的途径表达,如果要求女孩将照顾他人摆在首位,怨恨、困惑和报复就会紧随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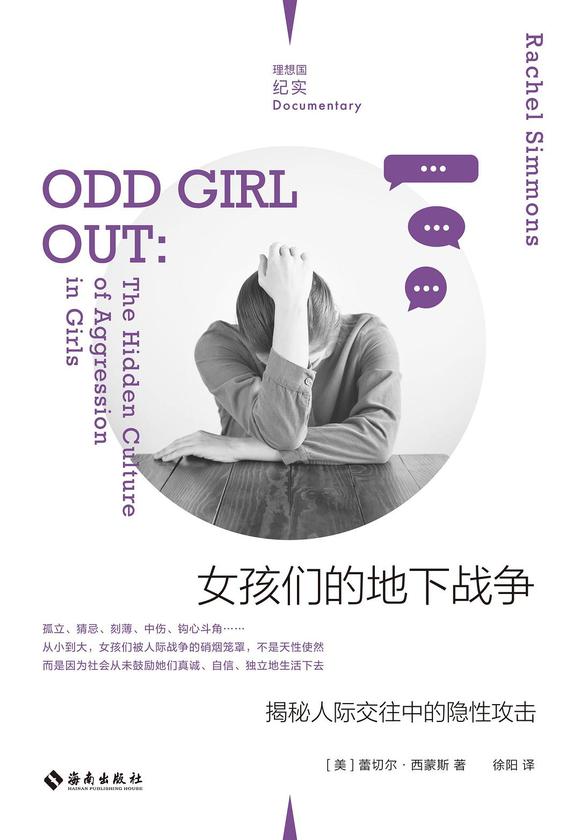
女性之间的刻薄行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女生本就如此”或“塑料姐妹情实锤”,但这本书提醒我们,我们对女性精神世界状况的了解和公开讨论是多么不足。这些年我们也陆陆续续在反思流行文化为何热衷于呈现女性之间的“扯头花”,为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开始出现真挚的女性情谊而欢欣鼓舞,为越来越多强大自信的女性榜样欢呼雀跃。但我们或许还需要看到,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仍未完全实现的当下,扭曲女性自我和同性友谊的土壤依然深厚——即使是在强调个人主义、独立自主的美国,女孩子们依然要在“甜美友善合群”的性别规范下压抑自我。
林子人:《女孩们的地下战争》勾起了很多我的回忆。我首先想到的是小学时班里有两位成绩最好、人气最高的女生,其中一位女生的妈妈刚好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在许多女同学看来,这给了她许多“特权”(比如评奖评优)和“打压”另外一位女生的手段。于是几乎全班女同学都围绕着她们俩划分成了两大阵营,暗自较劲别苗头。我虽然不在那两位酷女孩的社交核心圈里,但相比之下和那位“被打压”的女生关系更好一些。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班主任女儿阵营”的一位核心成员在课间冲过来讥讽我长相奇怪,说罢扬长而去,留下我和我的朋友面面相觑。
这样的社交攻击尚且可以一笑置之,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和大学我都有过被女同学单方面断交的经历。那是一种现在回想起来都锥心的痛苦——你曾经以为是亲密好友的人突然不再和你说话,在社交网络上把你拉黑,但你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仿佛你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积极、快乐等所有正面的情感。正如西蒙斯所描述的,被社交攻击的女孩在一无所知又不敢去当面对峙的情况下,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完完全全就是我当时的经历。虽然后来我和那两个女孩的关系都缓和了,但我一直没敢去问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害怕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且我也明白,我和她们的关系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女孩们的地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宽慰了我,遭遇到这种事情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叶青: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想形成和维持一些同性友谊,我常常得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像是小时候会害怕地跟着玩伴做坏事(偷地瓜、把邻居阿姨晒的鱼干丢进池塘等等),读书时会反感地附和同学开的下流玩笑。通过破坏、侮辱他人来彰显男子气概,是这些情谊得以维系的核心,而如果我稍微流露出一丝不配合与反抗,就会被迅速孤立,踢出这个兄弟会。现在我只庆幸自己被踢得够早。
潘文捷:如果一个人让我不适和痛苦,对方就已经不是我朋友了。不过未尝没有过心酸时刻。比如说初中的时候,以为A和B都是我的好朋友,结果某天赫然发现原来她俩之间才更铁一些,那就是我应该在车底而不该在车里的时候了。
潘文捷:不知道为啥友谊中的矛盾也要怪罪到性别头上来。曹操和关羽的关系不复杂吗?好了,要是尼采和瓦格纳是女性,那么大家大概会说她们最后反目,就是因为女孩的关系很复杂。但因为他们是男人,大家就会说是理念不合啦之类的,所以说人和人关系复杂跟性别又有什么瓜葛呢?
姜妍:如果从整体性上看,我觉得女性友谊和男性友谊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不是本质区别我不知道。比如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和《披荆斩棘的哥哥》,在同样面对离别的时候,女性的表现和男性确实是不同的。虽然里面的情感内核可能类似,都包含着不舍、伤心、难过。
徐鲁青: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里讨论过现实里的女性友谊为何困难重重。她认为在女性被客体化的社会,能否赢得男性欢心是女性成功的重要标准,因此女性间会产生以男性为中心的竞争关系,女性共同体的关系也更动荡。但在我看来,上野千鹤子没有关注到女性友谊的全部面向,“扯头花”之事难说哪个性别概率更高,男性间并不少有为权为名关系破裂之事。
另外,我也常庆幸自己身为女性,到现在仍可以和亲密的女友拥抱、牵手、同睡一张床,这对大多数男性友谊来说不太可能。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两个男性朋友出门旅行时会开两间房的惊讶,观察身边的直男,“哥们儿”之间在生活与情感里似乎离得更远,倾诉太多心绪波动是肉麻的,亲密的身体接触也被恐同文化抹杀,想和同性朋友靠得近一点,就得担心旁人或打趣或狐疑的揣度。在欧洲时会惊讶荷兰室友和“哥们儿”紧紧挽着手走路,告诉国内的男性友人时,他沉默了一会,说小时候也常和发小抱着同睡一张床。看来厌女文化既令女孩发生“地下战争”,也让男孩失去与朋友的亲密拥抱。
叶青:鲁青提到直男因为怕被误会不敢与同性好友有亲密举动太好笑了,干嘛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以为扮直(straight acting)是只有怕被发现身份的同性恋才会做的事。这样来看,怕被误解而约束自己这种带有恐同性质的行为,反而是在实践同性恋性质(practice gayness)。
陈佳靖:想起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拍的是两个男车主在开车时发生了剐蹭,二人都很气愤地摔门下车,想要找对方理论一番。没说两句他们就推搡起来,这时候双方都不甘示弱,摆起拳法阵脚,实实在在跟对方过了几招。好笑的是,挨了几拳之后,这俩人反而佩服起对方的格斗技能,很默契地放下了车的事,在大街上开始了第二轮“切磋”。事后他们拍拍身上的灰,再拍拍对方的肩膀,车的事就这么了结了,还萌生了一种不打不相识的兄弟情。我不知道这条视频是不是完全真实的记录,但在现实中以及影视剧里类似的情节也很常见。发生冲突的时候,男人们好像打一架就能解决(大不了再喝顿酒),事后还可以做朋友,女人们却从不会轻易出手,只要有一次恶语相向,她们的关系从此就多了一个死结。

这是不是说明女性之间的情谊就比男性更复杂呢?也许是,但这不是女性天生更敏感或更记仇导致的。正如《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所描述的,女性之间的战争之所以要隐匿到“地下”,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塑造了女性交往的规则。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就被教育要克制攻击性的一面,至少要在表面上成为友善懂事的“好女孩”。相反,男性则被鼓励去展现刚强、有力量的一面。长期以往,不仅女性的愤怒被压抑了,而且大部分女性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正常地表达愤怒和正面地处理人际冲突。她们可以委婉、刻薄、爱猜忌、“婊”且“mean”,唯独不能与人公开对立,因为一个“好女孩”应该有能力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换言之,她们的复杂不过是因为缺乏对人际交往的安全感罢了。
董子琪:对《简·爱》最深刻的印象不是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而是她小时候在洛伍德学校跟海伦的友情,读那一段时我正好也是十二三岁,跟她们差不多大,也在半寄宿学校里,很能理解在孤寒的寄宿学校里遭受的严苛待遇——好像寄宿学校更放大了友谊的重要性,因为吃完饭的一段时间就是social around的时间。书里两个女孩互相给予支持,性情也互补,简·爱倔强而海伦坚忍,简·爱能勇敢地帮助海伦走出屈辱,海伦也能以慈悲帮简·爱化解愤怒,这是青春期里很难得的感情了。但可惜的是,海伦早早地离去了,仿佛简·爱的一部分慈悲也跟着死去了。在之前或者之后,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友谊描写了。
给女性友谊“抹黑”的例子来自简·奥斯丁。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里写伊丽莎白与夏洛特交好,可是实际上两人在人生选择上大相径庭,夏洛特选择了伊丽莎白完全理解不了的柯林斯先生,从此过上了蒸蒸日上的好日子,她对婚姻的安排“充满头脑而没有爱”,连伊丽莎白也得赞赏其理性。对人生伴侣审美的分歧会让她们走上友谊的岔路吗,可能这也是写实之处。至于《诺桑觉寺》里的同性友谊,是多么糟糕啊,凯瑟琳与伊莎贝拉开始得热烈,进展得迅速,一起交流看书的心得,伊莎贝拉还嚷嚷,男人总以为我们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她可要让他们看看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呢,不知不觉,凯瑟琳就觉得伊莎贝拉有哪里不对又不能确认,而正是“不知道哪里不对”透露了那位好友的真实本性。这段友谊最终也被证明没有继续的必要了。奥斯丁参透了这种少女情谊热烈里的虚荣之处,这位作家对分辨情谊的真假、品性的高低确实在行。
黄月:认为女性友谊只是“扯头花”无疑出自一种顽固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横亘古今、不分东西,这或许也是今天许多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被重新发掘或新鲜创作的原因,比如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比如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作者和读者都有意识去纠正这一偏见,去书写其中无数的层次,去发现和照亮女性友谊的复杂与立体、爱与竞争。
很遗憾我无法身处一段男性友谊之中,去看到不同的友谊的状态,但我既见过街头兄弟酒肉朋友,也有幸在《此时此地》中体会到了库切和奥斯特的情谊、在《歌德席勒文学书简》中见证了两位文学巨匠的惺惺相惜,在《三人书简》中感受高尔基、罗曼·罗兰与茨威格的思念和热情。那些都是友情这种事物中无分性别的最珍贵的核心——它是人去努力建造和维持的结果,不是什么与生俱来或理所应得的果实,是超越自己的局限去爱另一个人之所是,是时时生长去创造一段关系之所是。
姜妍:昆德拉在小说《身份》中借着女主角和丈夫的对话曾经讨论过一部分男性情谊和女性情谊的区别。对话中他们提到友谊的产生,最初为了对抗敌人而彼此结盟,所以起先是男性间的产物,因为他们外出打猎要互相援助。到了现代,集体打猎的记忆则变成了看球赛、喝酒等等,从结盟衍生出了新的契约关系。男性相对来说会更早接受这样的“驯化”,甚至也内化成了男人的一部分,而女人这部分的“驯化”程度则要更浅。
随着年纪渐长,我更向往的情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看似不那么绵密的相处,是“朋友十年不见,闻流言不信”的友情,因为这背后其实需要强大的价值信念做基础。
林子人:前段时间读了《形影不离》,这是《第二性》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生前从未公开发表的一部小说,以她少女时代的挚友扎扎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友谊。读完我发现,早在费兰特之前,波伏瓦就写过“我的天才女友”了,连两个女孩的生命轨迹都几乎一样:一个早早地就显现出惊艳卓绝的才华,但被家庭环境所限无处施展;一个看似本分乖顺,却在天才女友的激励下力争上游,闯出了一片天地。20世纪初的法国女性所面临的礼教束缚之严苛,不输同时代的中国。这是否是一个女性生命经验中永恒的命题——因榜样缺失,女孩们只有从身边的“叛逆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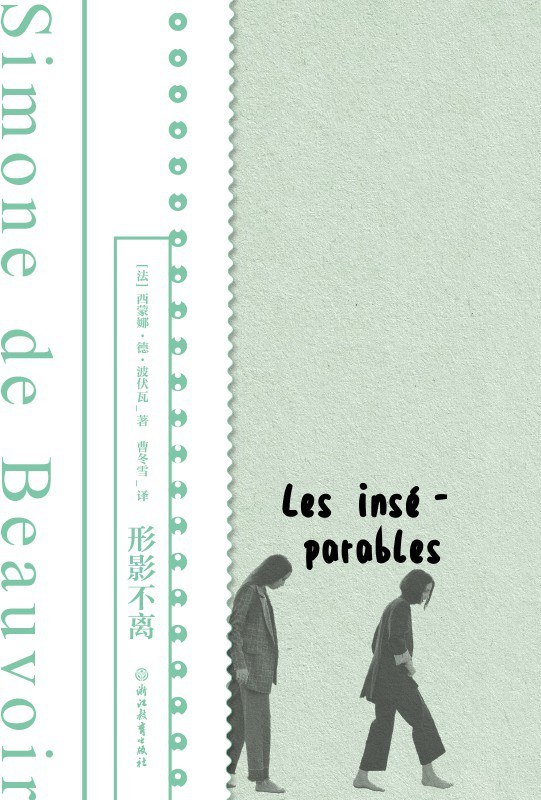
“那不勒斯四部曲”最触动我的一点其实是它展示了女性友谊的复杂性,我完全能够理解埃莱娜在深爱着聪明、漂亮且大胆的莉拉的同时,心怀羡慕、憧憬,又带有一点点妒忌(反过来讲埃莱娜身上也有莉拉妒羡交加的东西)——扪心自问,哪个女孩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俗气的女性故事可能就止步于此了,但杰出的故事和真实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女性能够正视这种同性友谊的复杂性,坦率地承认心中的确存在某个阴暗角落,发现女性之间的共同点和联结的可能性,并把这种张力释放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如今女性研究的发展则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女性友谊的复杂性”是性别维度的结构性倾轧所导致的。
愿天才女友的故事代代流传,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女性的警示与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