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连德谈了谈对智利大选的看法,和母亲的2.4万封通信,以及为何把所有的书都送给了别人。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平静,也试过冥想——可惜屡试屡爽。”图片来源:Saroyan Humphrey/The Observer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书已被译成42种语言并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7500余万册。她的创作涵盖了虚构与非虚构文学,并为纪念在1992年逝世的女儿建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基金会,其宗旨是为全世界的女性和女孩赋权。她的新小说《维奥莱塔》(Violeta)有着100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来自南美的女主人公动荡的一生与时代。现年79岁的阿连德出生于秘鲁,在智利长大,她在加州家中的书房里接受了我(指本文作者Hephzibah Anderson,作家、评论家)的访问,每天她都会在这里写作。
《维奥莱塔》是如何诞生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想法始于我母亲去世,正值新冠疫情爆发前夜。她1920年出生,彼时大流感正好传到拉丁美洲,小说的首尾都谈到疫情,也就近乎自然而然。写书时我没有计划,也不立主旨——我只想让人们与我相伴,容我为他们讲一个故事。

与标题同名的女主角是否以你的母亲为原型?
伊莎贝尔·阿连德:维奥莱塔和我母亲同时出生,所处的社会阶级也相同,许多读者大概会认出地点是智利。她美丽、天赋过人并富有远见,这些都和我母亲相似,但我的母亲有依赖性。维奥莱塔是个可以自力更生的人,这一差别不可不谓巨大。我常说,如果你养不起自己和孩子,那女性主义就无从谈起,如果你依赖别人,那万事就要看他人脸色。
《维奥莱塔》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而你的处女作《幽灵之家》源自一封写给你祖父的信。你很擅长写信吗?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经常写信给母亲,她也会回复,几十年来天天如此。我的儿子雇了一家公司来把信件数字化,据他们统计大概有2.4万封。一切尽在信中,包括我母亲的一生以及我的生活。如今母亲已不在人世,每天记录生活的习惯也就没有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日子过得飞快。

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有能力做许多事。这两年里,我出版了一部女性主义的非虚构作品(即《一个女人的灵魂》),又写了《维奥莱塔》,还写了一本有关难民的小说,现在还在翻译过程中,大概2023年会面世。我有三件所有作家都想要的东西:宁静、独处与时间。但由于基金会那边经常和高风险人群打交道,我也高度关注绝望、暴力与贫困。第一批丢掉工作的人是女性,还有移民。
你在《一个女人的灵魂》(The Soul of a Woman)里说,你在知道女性主义这个词之前就是女性主义者了。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年少时就察觉到生而为女性对我而言并非优势,但我也留意到了社会性的不正义。我性子很烈,因为世界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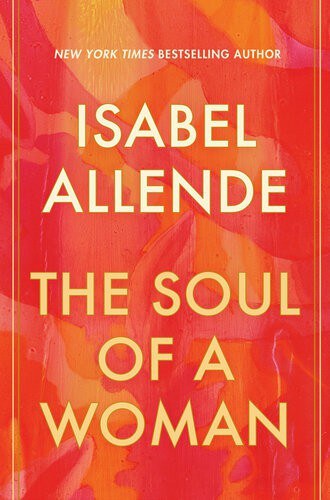
不正义是否也令你怒不可遏?
伊莎贝尔·阿连德:那肯定!我和以前一样充满愤怒。我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平静,也试过冥想——可惜屡试屡爽。
对女性主义运动而言,尚待完成的最重要任务是什么?
伊莎贝尔·阿连德:尚待完成的最重要任务是打破父权制。我们还在零敲碎打——我觉得这太慢了,这样我就等不到成功之日了,但那一天必将到来。
你如何看待最近这届智利大选?
伊莎贝尔·阿连德:乐见其成。就包容、多元性以及正义而言,新总统的所有看法都与我希望听见的相符。他现在35岁——差不多是我的孙辈了,这真是再好不过,世界终究是新一代人的。
生活在英语为主的环境里并以西班牙语写作是怎样一种体验?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说西班牙语了,有些东西我只有用英语才能表达。我可以用英语写非虚构题材,但虚构就不行,因为虚构文学是以一种高度有机化的方式流淌的,创作时用得更多的是肚子,而不是脑子。
书本与现实中的爱有何主要区别?
伊莎贝尔·阿连德:在现实生活里,不便之处每每要多于方便之处。如果你像我这样结婚偏晚,那就得背上一大堆包袱,另外还有一种紧迫感,令这段关系以及每一天都显得异常珍贵。
这是你的第三次婚姻。对它有怎样的预期?
伊莎贝尔·阿连德:你觉得有谁会想在77岁的时候结婚?绝不!但这个男人通过听广播认识和爱上了我。我们结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临门一脚来自他的孙女安娜,当时她才7岁,跑去学校图书馆问管理员说“你听说过伊莎贝尔·阿连德吗?”管理员答道:“听过,听过,我读过一些她的书。”一阵沉默之后,安娜接着说:“她和我的祖父睡在一起。”
可否向我透露一下为什么你的每部小说都是1月8日开始写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一开始是一种迷信,但后来我的生活变得异常复杂,迷信也就成了规矩。我会烧掉一些书页,点上蜡烛然后关上门度过一整天。每当我出关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寄来鲜花和电邮,还有一盒一盒以黑巧克力覆盖的橘子皮,它们给了我力量和欢乐。

你的枕边书有哪些?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在读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的《幻境》(Cloud Cuckoo Land)纸质本,同时在听爱丽丝·霍夫曼(Alice Hoffman)的《对立面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Opposites)。Kindle里面有一本很多年前就打算读的丹尼尔·梅森(Daniel Mason)的《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这是一个战争故事,我不喜欢战争故事,但它却很出色。
你是如何整理藏书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不整理。我都送出去了。
每一本书都这样?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唯一留下的书是继父在我10岁时送给我的见面礼《莎士比亚全集》。我是把它当故事来读的,此后也一直不变。
有哪些经典著作是你羞于没有读过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也许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觉得它很无聊。
幼时的你属于哪一种读者?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那代人还没有接触到电视,祖父不让我听广播,因为他认为里面的内容太恶俗,我们也没去过电影院,因此我从来都是个很好的阅读者。青年时期的我非常孤独,也很愤世嫉俗,我逃离一切以及自己的方式就是读书。
有什么书是你难以忘怀的吗?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记得很清楚,我13岁左右的时候全家住在黎巴嫩——女孩们哪儿都不去,只能待在学校和家里。大概跟你形容一下:我知道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即猫王)的时候,他已经胖乎乎的了,我与摇滚乐有关的一切缘分也就此断绝。但我继父那里有一个始终上锁的衣橱,里面是威士忌和巧克力,我猜可能还有《花花公子》杂志。我和我的兄弟们会打开它,兄弟们负责吃掉摆了一整层的巧克力,而我则直奔四卷本《一千零一夜》,据称有色情元素,所以一直被关在衣橱里。书是很色,但我没读懂,因为隐喻太多了,而我一点基础都没有。但我还是非常享受这种阅读衣橱里的禁书的感觉——有朝一日我总得就它写点什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