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在《祥瑞》一书中试图以“深描”的方式,审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互动。

记者 |
编辑 | 黄月
不论古今内外,人们在经历瘟疫时,总会不由自主怀疑灾异与运势之间的关系。有人可能会求助于民间信仰中的“算卦”来推测未来,也有人求助于天文星象。中国古代帝王将这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加以利用和延伸,有时再附以代表神灵不可测意志的符命,颁布诏书以自谴或表彰。这也是为何在两汉史书中,我们常能见到有关“灾异和祥瑞”的描述。
张向荣的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后简称《祥瑞》)便是借用西汉的“祥瑞”,以王莽作为线索,由表及里呈现了背后复杂的政治结构。在张向荣看来,“祥瑞”背后的儒生政治体系有着庞大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贯穿了中国帝制的发展进程。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儒生的工作之一便是观测和解释这些自然甚至超自然现象。

出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后人对某一特定历史人物的描述和诠释呈现出种种差异,而人物本身也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中渐渐失真。儒生政治体系、外戚政治、符命与祥瑞信仰构筑了这本书的舞台结构。作为主角的王莽,反而在这样的结构中显得有些不起眼。张向荣坦言,这正是他的意图之一——不再重新“制造王莽”,而是将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从传统印象中剥离,混溶于历史的长时段,以“深描”的方式,审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互动。
界面文化:你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张向荣:我在博士期间关注两汉的诗经学,这是一个史学和经学相结合的方向。借此机会,我系统地将两汉儒家经学的演进以及与诗经学有关的材料进行了阅读和梳理。经学发展至王莽时代到了一个复杂的阶段,换言之,王莽是西汉儒学演进到一个特殊阶段,或者说顶点的标志性人物。因此,理解两汉的经学,了解王莽是必要的一步。反之亦然。
随着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叙事有了新的可能性。在大众印象中,王莽是一个很怪异的人物。但是如果将王莽放置到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甚至东汉的经学发展也很大程度受到王莽的影响。但流传于世的学术传记十分有限,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祥才先生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在上个世纪对王莽的生平有所撰述,此外仅有一些演义式的小说。随着这十年来阅历的增长,重新叙述王莽故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界面文化:这本书并不局限于王莽的一生,而是具有较强的历史延伸性,你是如何构思的?
张向荣:关于王莽的基本史料其实不多,主要是《汉书·王莽传》及《两汉书》。出土文献有一些,但仍以补充为主。如前所述,王莽的崛起是西汉儒学演进的产物,因此,我觉得要想理解王莽,必须要从更广阔、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去理解。比如我们反思王莽成功的原因,会发现历史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的。首先,儒学是王莽起势最根本的条件,时人对祥瑞灾异无条件的信任,再加上西汉的政治机制为王莽提供了攫取政权的现实条件,种种机缘,才可以解释王莽独特的成因和败因。

界面文化:20世纪历史学年鉴学派提出了“长时段”的研究理论,认为如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请你谈一谈你所理解的汉代政权建制与儒生政治?
张向荣: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等前辈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探讨过士大夫政治,一些学术成果业已成为共识。去年底,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亮所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的中文版面世。她认为,巫蛊之乱后朝堂为之一空,所以儒生群体迅速填补空白,由此促成了一个儒生帝国的兴起。遗憾的是,当我知道这本书时已时值今年春夏,没能来得及系统地了解她的论证过程。她的观点中有一点我是赞同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汉武帝因采取董仲舒的对策开始罢百尊儒,从而形成儒生政治局面,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被扬弃,但普通读者可能还了解的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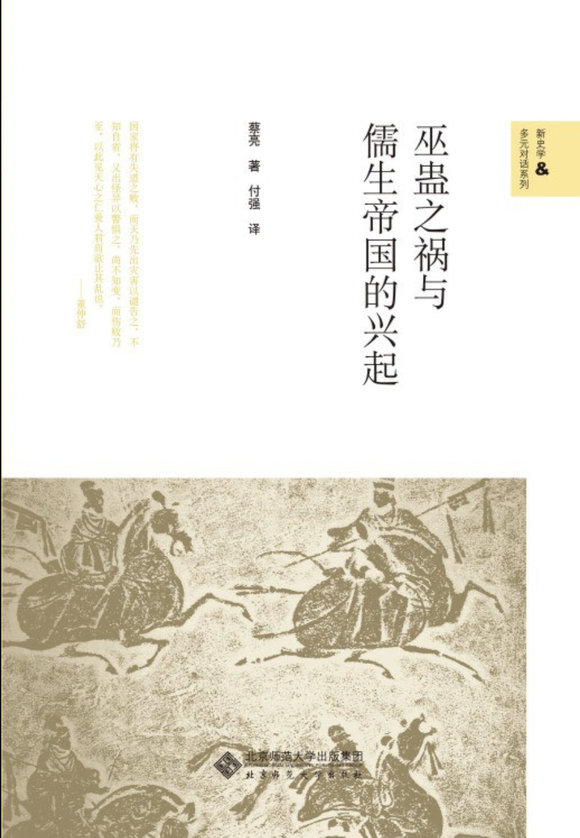
我的论述逻辑是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概括性的描述西汉政权的特点,即建国与建政——所谓“建国”就是政教体系的建立,所谓“建政”就是政权的组织方式,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的确立。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框架可能有一点局限性。
从这个简单的框架里来观察儒生政治,我认为可以有这么几点:
一是汉武帝时期已经开始抬高儒生地位。在我看来,董仲舒的作用其实并没有公孙弘(西汉丞相)大。儒生政治机制的形成在汉初就初见端倪,叔孙通(西汉待诏博士)最早的影响很有限的,只是制定了礼仪。后来经董仲舒和公孙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形成真正的阶层势力需要更长的时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史记》中是无从考证的,直到《汉书》中才被记载。我认为这有些类似于古史辨那般层层累积,随着历史朝着董仲舒理论的发展方向演进,他的观点逐渐为后代重视,以至于当代人认为儒生政治理论到董仲舒时期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西汉儒生真正介入政治,一定是在汉武帝后期以后。汉宣帝得以行王霸之道,正是说明儒生政治已成气候,以至于皇帝需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同时也说明了儒生还没能进入到左右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仍然需要和外戚联合。这可能与汉宣帝起势于民间、未能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有关。我比较赞同王葆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的观点,即汉宣帝之后,至元、成、哀时,儒生在国家政权中发挥支配性地位,此时西汉真正形成儒家政治。因此,到了西汉后期,汉宣帝的王霸平衡逐渐被打破。各种祭祀、宗庙等制度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直到演变到要建立纯粹的儒家理想国。
总之,我认为这个过程是逐渐形成、愈演愈烈的。
界面文化:在你的描述中,王莽仿佛和每一方势力都保持着忽远忽近的距离。你如何理解王莽权力倾向的阶段性变化?
张向荣:以往常见的叙述把王莽的权力欲夸张得太厉害,拔高他对西汉政权的夺取,把他描述成一个处心积虑、多年如一日、具有极强作伪能力的人,甚至庸俗化为一个“成功人士”,一个深谙上位之道,精通权术的胜利者。事实上,在我看来,王莽是一步步逐渐靠近权力中心的,他的野心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
王莽权力的阶段性变化是比较明显的。最开始,他只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外戚,有一定理想。尽管地位边缘,但仍然是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他可能在一开始没有过大的野心,只是在家乡环境中树立人设并累计人气和支持。因为王莽的父亲早逝,没有被封侯,所以他这一支是王氏家族里最弱的。父兄都去世得比较早,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成长环境对王莽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他个人的努力,恐怕各方势力都不会看见他,也就是你说的与各方势力都保持距离。而王莽意图“打扮”成儒生的角色,可能是周围家庭环境的影响,这包含家人的期许和他自身争取出人头地的希冀等。有一个细节是在汉哀帝即位后,王莽被免去大司马一职。返回长安后,他曾想托关系担任太常职位,太常是九卿,位不及大司马,只是普通的高级官员。这应该能说明,在汉哀帝时期王莽仍然没有称帝的野心。

我深信人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发展变化的。王莽真正有了当皇帝的念头应该是到汉平帝子婴时期,随着频繁出现的祥瑞意象和自身官职的不断变化。王莽才逐渐感知到自己要有称帝的自信心,或者说野心。儒家思想中对理想君主的设定是德位合一,基于此王莽试图从一个孔子式有德无位的圣人,转变成儒家叙事中有德有位的圣王。
界面文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在著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非个人的仪式性关系)与信-任型(个人的私人信任关系)两类。你如何看待王莽和西汉刘氏君主之间的关系?
张向荣:侯旭东老师关于西汉君臣关系的论述,于我有不小启发。《宠》一书使我意识到,对鲜活历史需要“深描”,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不能被各种抽象的、线性的叙述所框住。我在本书中也努力注意不要忽视人与人互动时的旁逸斜出,避免用有限的史料证明特定的观点。之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王莽和他的时代》,也是为了铺陈性地将王莽时代各个面向都呈现出来。遗憾的是,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理解古代史,可能避免不了历史的辉格解释(指忽视历史细节而进行价值判断),这也是我一直在反思的。
说回侯旭东老师的这个解释角度,我觉得王莽还是有些特殊的。在汉成帝时期,王莽作为王氏家族的外戚,任职大司马,他与汉成帝的关系应该是超出礼仪型君臣关系的。然而,王莽的接班主要得益于叔父辈的举荐与姑妈王政君(汉元帝刘奭的皇后,汉成帝刘骜的生母)的支持,以及竞争者淳于长(汉成帝时任卫尉,属九卿之一)的落败。没有史料能够证明王莽和汉成帝之间达成信任型关系。而汉成帝对张放(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袭封富平侯)、淳于长,则是很典型的信任型关系,他们陪着皇帝微服私访,淳于长还敢调戏汉成帝的废后,张放更是在汉成帝死后哭死。因此,我只能说,王莽有进入信任型关系的条件,但还没来得及展开,汉成帝就去世了。
汉哀帝与王莽应当属于礼仪型关系,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汉哀帝对王莽乃至王氏家族的一些赏赐与优待,目的是换取王氏家族退出政治舞台,这已经不属于侯旭东老师所说的那几条信任型关系的标准。而汉哀帝和董贤(汉哀帝时任大司马)的关系就毋庸赘言了。至于汉平帝、孺子婴(刘婴,汉宣帝的玄孙),都是王莽的傀儡,已经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了。侯旭东老师的这个角度,为我们理解王莽称帝后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这也解释了为何王莽被杀时,有很多年轻的官员甘愿陪他赴死。说明在建新代汉的过程中,王莽为自己构建了信任型的君臣关系。
界面文化:外戚干政是西汉皇权旁落的原因之一,也是王莽得以步入政治中心的背景。你如何理解外戚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张向荣:我认为是先建立王权才能有外戚和外戚政治。比如宗法封建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谈不上外戚,妻族多为诸侯的女性后代。只有王的兄弟可能有篡权的威胁。其次是西汉时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存在“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对母系家族的尊崇,才造成了外戚政治能变成稳定的机制。汉武帝也有意识的提升外戚地位,意在改变官僚机制运转,提高效率。
无论说外戚政治是作为帝制的附属物,还是作为汉朝女性地位的表现,还是汉朝现实政治的需要,都是有成立的可能性。王权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被突破的过程。为什么随着时代发展,封建专制主义反而越行越甚,其中缘由我们现在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总说秦皇汉武,是因为当时突破了西汉之初政治结构对皇帝的束缚。王权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但是弊端在于如果面临皇帝突然去世,诸侯王没有能力与外戚抗衡,皇权容易旁落,汉哀帝即是。

界面文化: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祀庙而做皇帝。王莽通过祭祀仪式、获祥瑞、明符命实现“天命转移”。你如何看待这些神圣意象?
张向荣:事实上,以祥瑞作为线索并不是我的初衷,而是在写作中不断发现这一意象,由此引起了我的兴趣。西汉时期,古代帝王传说和神圣性意象普遍存在。用儒家思想中的德位合一来解释这些可能更贴切一些,我认为这也是王莽的政治行为最根本的动机。王莽通过仪式将自己从普通的臣民变成王,或圣王。
王莽的受禅,并不是简单的由汉朝禅让给了他,而是顺应天命,上天的意志就体现在这些符命上。所以,王莽在建立新朝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向全国颁符命,这是在向国民宣告新朝的建立是遵循了天意,我认为这是王莽的基本逻辑。刘秀建立东汉后,也向天下颁布了类似的东西,不过他颁布的是图谶,其逻辑和王莽是一样的。不论是仪式还是神圣意象,都是为王朝赋予神圣性的努力。此后,在一些文学作品(如《隋唐演义》、《水浒传》等)特别是民间故事里,这类逻辑也不鲜见。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国家仪式与政治制度体系的结合?
张向荣:就起源来说,祭祀天地、宗庙这些仪式都很古老,尤其是西周的祭祀仪式给我一些启发。儒家是基于个体、家庭乃至家族伦理而所生发出的对理想秩序的一套见解。但儒家思想不是哲学那般只讲理论,也不是纯粹的道德,而是发明了礼,并通过礼的实践,来达成伦理的实现。所以,这一系列礼仪制度在儒家看来都是很重要的,并且有利于移风易俗、构建秩序、稳定人伦关系。西汉后期,这些仪式都被纳入到儒家改制的体系之中。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儒家思想已经从观念层面向物质层面进行了拓展。对王莽而言,他的上位过程需要不断地突破这些仪式,来证明自己代汉的合理性。

界面文化:在当代大众想象中,王莽的形象是单一的、负面的,受到帝制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你在写作时是否有意识地在重新塑造王莽?你如何看待活在人们固有印象中的历史人物形象?
张向荣:的确,王莽的形象在古代是相对单一、负面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使得王莽必须被看作是一个需要严加防守的篡位者。不过,大众对王莽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松动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对王莽的认识可谓五花八门。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王莽的文献和史料较为单一,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大家能阅读到的王莽的生平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对其评价则是南辕北辙。
有鉴于此,当我在书写这本书时,是有意识地不去重新塑造王莽。首先是因为文献史料的缘故,没法也没有必要为他翻案。关于王莽众说纷纭的评价,恰恰反映了大家对王莽时代可能缺少全面的认识,人物独立且分散。因此,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把王莽所处的时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祥瑞灾异等传统信仰体系以及西汉政权组织的特点等交代出来,有助于大家理解王莽出现的前因后果。在我看来,最好不要对历史人物存在一种“定论-翻案”的模式,而是尽可能地贴近他所生活的时代。
界面文化:如今越来越多的心态史学家利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你也在书中多次提及王莽不断变化的性格特点。你如何理解王莽的人格特点与心理界限?
张向荣:有一段时间,我阅读了许多关于神经症人格的作品。我认为讨论王莽,或者说古人的心理,无疑是一种冒险。但鉴于王莽的行为和性格,尤其是政治人格和生活人格之间的明显的冲突(例如王莽对酷刑的热衷,他的私生子,以及他对亲生子女的严酷对待),值得我冒险尝试。我注意到班固在描写王莽时特意描写了其早期的一些行为。但这些由不得我们猜测他具有严重的神经症人格或者说心理疾病。

我认为应当从儒家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从儒家对王莽心理的影响来看,其性格之所以有如上的表征,与他想要成为儒家道德君子乃至儒家圣人有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王莽的人设包袱太重。他把自己的人格与儒家理想中推崇的“完美道德”牢牢绑定在了一起。在王莽看来,既然儒家的理想是完美的、纯粹的,那么他的人格也必须如此,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家庭也是他个人的一部分。因此哪怕他的儿子有任何一点道德的过错,王莽便会迁罪于自己。王莽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人格上有了污点,而擦掉污点就意味着逼死儿子。
界面文化:除了王政君一直贯穿始终外,书中也有如赵飞燕、黄皇室主等多位重要的女性历史人物出场。你是否有意识地选择和描写女性角色以丰满王莽形象?
张向荣:是的!我很高兴,这是近一段时间来第一次终于有人注意到了我这个小小的心意。受制于古代社会发展,不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作品都来自于男性视角,特别体现在政治叙事上。王莽作为一名外戚,若没有女性家族成员的提携,是不可能有机会承担当时儒生政治的使命的。
我愿意较多地描绘这一时期的女性,并且在一些地方做了说明。譬如关于班固评价王政君是“妇人之仁”,我会在旁特意说明这是一种性别污蔑。王政君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这是因为她的人生历经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直至王莽建立新朝,享有很高的威望,尽管她本人并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也正因此,王政君能够一直支持王氏家族把持权力。当然,班固在这里并非评价王政君的性别,我认为“妇人之仁”在当时特指一种政治德行,即一种不够高、不够好的政治德行。在描写王莽的女儿时,我是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的。古代男性后代是王权潜在的继承人,可能会威胁到父亲的权力,女性后代则不然。我很感谢班固记载了那四个字——“敬、惮、伤、哀”——巧妙地概括出王莽对女儿的心境,饱含疼爱和畏惧。
可惜的是,当前的女性叙事有时还是逃不开男性叙事的框架,塑造女性角色时本质上还是在塑造男性或是一个无性别的角色。即使不考虑王莽,女性在当时的作用和点滴的事迹,也值得今天的读者去留意。
界面文化:本书的学术引用之丰富令人眼前一亮。你如何通过叙事平衡大众性和学术性?
张向荣:我觉得既然是非虚构写作,就要尽可能做到各处叙述都有史料文献依据。这包括两类,一类是文献性的、知识性的、观点性的,且较为前沿的成果;另一类,则是能够欧帮助自己思考的思想性著作。例如十年前我在写毕业论文时,讨论的是诗经在汉代政治中的作用,需要分析儒家对帝王的教育,因此参考阅读了色诺芬(古希腊历史学家)的《居鲁士的教育》、伊拉斯谟(中世纪尼德兰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基督君主的教育》、施特劳斯(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政治哲学史》等,寻求启发的灵感。
我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来叙述一个历史故事,确实有些不自量力。但我也恰恰要感谢中文系的阅读及训练,帮助我在保证叙述完整性时,还能突出其戏剧性,同时又尽量守住非虚构的底线。书到用时方恨少,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深刻的体验。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术界朋友、师长的帮助,总体上是背靠着前辈及同龄学者的大树才能够最终付梓。
界面文化:请推荐一些对你的写作有启发的非虚构作品。
张向荣:我认为非虚构写作的核心是要有作者自己的观点,同时平衡故事性。我很喜欢朱东润先生(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写的一套传记(包括《杜甫叙论》、《梅尧臣传》和《陆游传》等)。朱先生的写作有严肃的学术的观点,同时又能兼具大众性。此外,塔奇曼(美国历史学家)的《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都很有趣。她还有一本小册子,名为《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谈论非虚构写作的原则,我从中获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