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让我们的精神开始运作以驾驭喧闹的声音,我们通过在嘈杂的世界中制造音乐而生存。

图片来源:madjembe / Shutterstock
在城市文化兴起之前,母鸡咯咯叫的声音一定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烦恼之一。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与鸡共舞”,以公鸡的啼鸣划分时间。但是,家禽的咯咯叫声一定带来了一种持续的嘈杂。奇怪的是,这种令人厌恶的噪音竟然进入了大量的音乐曲目,从法国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1726年的《鸡》到中国流行歌手王蓉2014年的《小鸡小鸡》。
但家禽的叫声并不是唯一出现在音乐中的噪音。在各地的音乐文化中,生活中的噪音——无论是恼人的还是令人愉快的,都通过模仿或抽象的方式得到了呈现:舒伯特在《魔王》中使用奔跑的马匹声达到了令人不安的效果,这种声音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音乐中也能听到;图瓦人的喉音唱法经常模仿奔腾的水声和呼啸的风声;贝多芬对鸟鸣和雷雨进行管弦乐编曲……随着工具和机器的发展,人类创造的噪音也渗透到音乐中,舒伯特、德沃夏克和圣桑都曾经将纺车的重复噪音转化为悠扬的乐曲。

随着机器变得无孔不入且越来越吵,它在音乐中的存在也是如此。在作曲家史蒂夫·赖希1969年的作品《城市生活》中,汽车警报器的声音取代了拉莫《鸡》中母鸡的咯咯声,使城市声景更具美感。事实上,汽车警报器和鸡叫声有着共同的声音特征。两者都是一成不变的节奏,都有大量的噪音成分,高度重复却又不可预测——这正是噪音令人讨厌而其音乐用途令人喜爱的特点。
作曲家将环境噪音编织到他们的音乐结构中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它反映了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应付噪音的——如何将噪音转化为可接受的甚至是令人兴奋的事物。噪音代表无序和不确定,而我们试图从中找到连贯性。这是一个涉及对抗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进化适应性的过程,要求身体的自然节律来建立秩序。就像鼓声为我们准备了戏剧性元素一样,噪音让我们的精神开始运作以驾驭喧闹的声音,我们通过在嘈杂的世界中制造音乐而生存。
音乐和运动在生物学上是相通的。我们在音乐中前进,在音乐中跳舞,在音乐中摇婴儿入睡。我们在音乐中摇摆、跳动、晃动,但让我们动起来的,不仅仅是节奏与跟上节拍的关系。
噪音本身也产生一种运动反应,这个词的词源证明了这一点。希伯来语中的噪音“ra'ash”是摇晃的同义词,这个词出现在《圣经》中,通常描述愤怒和狂暴的破坏。噪音一词是在比如今安静得多的时代创造的,它的词源与拉丁文的“nausea”相同,而后者又源于希腊文的“naus”——船。噪音虽然是一种听觉现象,但与晕船有奇怪的关系,是听觉和前庭系统共同作用的奇怪结果。

耳朵将听觉和前庭机制结合起来是进化的一个奇特结果。在从海洋到陆地的过渡中,鱼类的鳃弓进化成了内耳骨,并将平衡与振动信号感觉结合起来。负责调节平衡的前庭器官球囊在过山车上会失控,并对声音产生反应。当我们听到的音乐响亮、动感、有节奏时,那种让我们沸腾的强大驱动力就源于前庭系统。正如作曲家约翰·亚当斯描述他的管弦乐作品《快速机器中的短途旅行》(A Short Ride in a Fast Machine)时所说的,“就像那种有人要求你乘坐一辆高级跑车,但你会希望自己当初没同意的感觉。”
除了与噪音有关的焦虑和混乱之外,长时间的吵闹噪音也会使身体产生困惑。从系统发育上看,听觉系统是从前庭系统进化而来的。除了耳蜗中探测声音的毛细胞外,前庭神经还含有对声音信号做出反应的纤维。在不常见的情况下,巨大且突然的噪音会产生一种不平衡感,可以转化为快速运动产生的同样令人不安的身体不稳定状态,这被视作是听觉眩晕。
我们通常很善于适应噪音,如果噪音音量不大,频率范围没有显著变化,并且没有突然的变化或中断,我们能够把它推到意识的深处。但是,一旦噪音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让我们不安。噪音的频谱特征是非周期性的,也就是说,噪音的信号没有必要的可辨认的重复模式,因此不能给我们传达某个音调。这让噪音变得令人困惑,我们不能唱出噪音的音高,也无法理解它。正如我们对无比混乱的事物通常的感受一样,噪音也是不愉快的。
噪音的内在混乱特征也挑战了我们的感知过程。噪音遮蔽和掩盖了交流,削弱了我们感知和解读有意义的听觉信号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无法识别或意想不到的噪音使我们感到焦虑。声音是造成惊悸的基本原因,听觉系统在焦虑和恐惧的神经元回路中起着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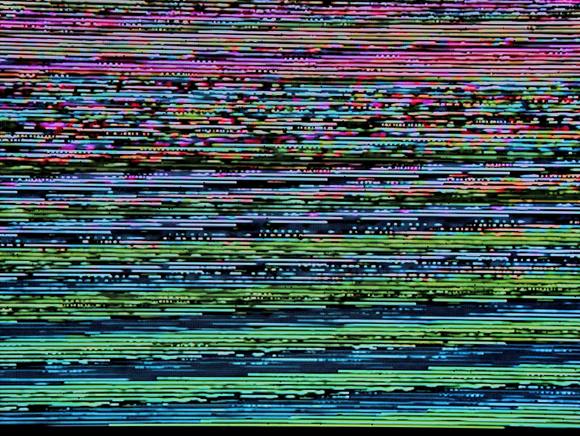
杏仁核是处理恐惧和情绪的关键,当带来恐惧的声音被获取并储存在记忆中时,杏仁核就会适应。尽管研究文献中有大量研究表明,生物体在相对较少的重复后,就可以通过听觉提示来预测困难,并在较长的时间内保留这种记忆,但其中所涉及的神经元网络和连接还不清楚。然而,创伤性事件会影响突触的强度和敏感性,使噪音在创伤后压力和焦虑症中成为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
政府职业健康和安全机构非常关注环境噪音的危害。它扰乱注意力,增加压力,并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压力相关疾病有关。一项针对唾液中皮质醇的研究表明,噪音与压力激素的释放有关,噪音引起的压力损害了前额叶皮层的思考和调节冲动反应的功能;高度环境噪音和嘈杂的音乐也会影响味觉和嗅觉的敏感性;甜和酸的味道在嘈杂的餐厅中与在安静的餐厅中不同。(一般来说,噪音会抑制味觉。但一项研究发现,白噪音的存在可以增强对甜味的感觉,白噪音提高了压力水平,因此影响了味觉感知。)
那么,噪音是一个警告系统。我们有意识地关注我们的周围环境,以识别威胁和机会。因此,我们不断寻求连贯的信息模式,并在嘈杂的条件下努力做到这一点。在帐篷外狂风大作、树枝颤动的夜晚,我们专注于脚步踩过树叶的沙沙声。我们特别集中注意力,努力在城市交通的喧嚣中听到对话。
尽管在嘈杂或高度回响的情况下,我们经常丧失对语言的理解,但我们设法通过编造丢失的声音来找回丢失的信息——在可理解性减弱的地方填补空白。当这些丢失的声音被重建时,噪音可以被有效抑制。
这种能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描述过,被称为“栅栏”效应(意指视觉系统通过填补栅栏后面的空白来保持一个完整的图像)或 “声音隧道”效应(指火车进出隧道时人们想象出来的连续性)。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恢复被周边咳嗽声掩盖的讲话,到被静电噪音破坏的歌曲片段的连续性。大脑甚至会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发明声音。
对雪貂(其听觉系统与人类相似)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初级听觉皮层如何在减弱周围噪音的同时提高所需信号的增益。研究人员测量了动物对声音的神经反应,发现动物对被噪音掩盖的声音的解读与对没被掩盖的声音的解读相似——大脑似乎是在抑制噪音以增强交流。
事实上,我们是如此坚定地要从噪音中提取意义,以至于当遭遇长时间的听觉混乱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听觉幻觉。我们想象嵌入在噪音中的虚幻事物——电话铃响、我们的名字被叫到,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被称为听觉空想性错视。

在感觉超载和被剥夺的情况下,人们会听到或看到想象中的结构和信息。鬼魂般的声音被认为是出自静电噪音的电子录音,这种现象被称为“电子语音现象”。同样,在持续的黑暗中,人们会体验到光幻视,迷幻般的光爆发往往呈现出人的形态,这种现象被称为“囚犯电影院”。
20世纪初,在战火纷飞的世界中,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研究了使人类能够在噪音中找到结构的基本原则。韦特海默的“格式塔组织原则”描述了头脑如何将不同物体按照相似性分组。他证明,如果模式表明存在联系或连续性,那么这些模式就可以被推断出来。韦特海默将格式塔组织原则的基本原则称为蕴含律,即通过重复、秩序或对称来寻求简单的趋势。
韦特海默的格式塔原则解释了人类如何在宇宙中划定恒星星座,以及如何在云层中想象生命形式。达芬奇注意到了在噪音中寻找结构的纯粹创造性,他从斑点表面的随机图案中获得了灵感。“看看溅上许多污渍的墙壁、或者各种颜色交杂的石头,”他写道,“如果你必须创作一些场景,你就可以从中看到与点缀着山、河、岩石、树木、大平原、山谷和山丘的风景的相似之处。”
达芬奇可能会同意,音乐的起源是一种在噪音中寻找模式的创作冲动。这是一种与跳动的心脏协调一致的节奏。从稀树草原上最早的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尖叫、喊叫、嘶吼、拍手、跺脚,创造噪音来赶走对手——带着威胁性的入侵者和想象中的鬼魂等。
人类在创造工具时总会产生噪音,他们创造的工具反过来在执行任务时也会产生噪音,比如打磨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专门的工具被制造出来,其唯一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制造噪音。在已知的最古老的乐器中就有制造噪音的工具——钹和手鼓。《圣经》告诉我们,它们发出的声音是为了取悦上帝。早期的打击乐器——二叠琴、刮片和膜鸣乐器——一边制造(有时是痛苦的)巨响,一边跟随身体的脉搏。这些乐器也是警报器,召唤人们去战斗。

随着乐器的发展,作曲家们找到了多种方法将环境声音编织到音乐中。土耳其的月牙铃——带有金属叮当声的杆子——在战场上和宫廷仪式上都会被摇响。月牙铃与低音鼓、铙钹和沙锤都是土耳其禁卫军乐队的乐器,其声音被纳入了18世纪的音乐中,首先作为“异国情调”奥斯曼音乐的参考,后来成为发展中的交响乐团中不可或缺的噪音组成部分。土耳其月牙铃的变体在各种文化中的运用比比皆是。来自英国的澳大利亚人改编了一种原住民乐器,并用啤酒瓶盖代替了发出响声的贝壳,他们把这种乐器称为“猴棍”。
许多作曲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了土耳其禁卫军乐队的噪音和片段,经常用副标题“alla Turca”的作品暗指奥斯曼风格。同时,作曲家对环境和人类的噪音,如雷声、风声和战斗的喧闹声的描绘越来越感兴趣。
音乐家很快发现了噪音中的讽刺因素:一些不连贯的声音——瀑布或流动的溪流——让人深感愉悦。混乱的随机性使噪音令人困惑,却可能是音乐的一个突出特点。人类一直都在寻求刺激,我们制造令人不安的情况,模拟危险和不确定性,刺激肾上腺素释放,加速心跳,加速呼吸、不平衡和眩晕——即传说中的冲动。
作曲家喜欢挖掘恐惧和悬念的内在情绪。威尔第《奥特罗》暴风雨般的开场,结合了撞击的铙钹和低沉持续的管风琴群,在巨大的歌剧院中隆隆作响,持续很长时间。低音经常被作为一种威胁性的提示,特别是在与模拟恐惧的生理反应的不规则节奏结合在一起时。约翰·威廉斯为《大白鲨》所作的配乐将与威胁相关的隆隆低频,与受威胁者的加速呼吸声结合起来。
由于机器和工厂设定了欧洲的声音和节奏,工业革命以及录音和无线电传输的发明,为音乐中噪音的使用增加了新的维度。1913年,未来派艺术家路易吉·鲁索洛写了一篇题为《噪音的艺术》(The Art of Noise)的宣言,其中,他呼吁将机械和城市工业化的声音融入音乐中,就像工业设备融入视觉艺术一样。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作曲家使用了机器的声音,如皮埃尔·舍费尔的具象音乐(musique concrète,指将来源各异的录音以创造性的后期制作技术,调变出传统乐器所不可能表现的音乐)中录制了火车声音,而其他人(如埃德加·瓦雷兹)合成的声音中并没有明显参考自然的声音。瓦雷兹称音乐为“有组织的声音”,有效地消除了音乐和噪音之间的区别。这一定义为作曲家们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作曲家约翰·凯奇则开创了前进的道路。
“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所听到的大多是噪音,”凯奇写道,“当我们忽视它时,它使我们感到不安。当我们倾听它时,却发现它是那样迷人。一辆卡车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的声音、电台之间的静电干扰声、雨声。我们想捕捉和控制这些声音——不是把它们作为音效,而是作为乐器。”
凯奇在他的著名作品《4'33"》中兑现了他的理念,在这部作品中,一位钢琴家静静地坐在她的乐器前,促使人们专注地倾听周围的噪音,在混乱中寻找意义。像凯奇这样的艺术家揭示了关于噪音的另一个真相:语境会影响情感价值。人类的听觉是善变的,昨天的噪音就是今天的艺术,而昨天的艺术就是今天的噪音。20世纪早期作曲家阿诺德·巴克斯将巴赫作品的最后几个乐章比作“缝纫机的运作”,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爵士将拨弦键琴的拨弦声描述为“两具骷髅交配的声音”。
技术创新——电力带来的录音、放大、过滤——给作曲家提供了各种新的方法,把噪音变成他们音乐中的表现力元素。失真和反馈噪音成为声音的雕刻工具。吉米·亨德里克斯对美国国歌的标志性演绎是那一代人的声音。
如今,极为强化的音响系统向观众投射出难以想象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的实验演变成了各种流派,感官不和谐是其中的常态,而不是例外。当今的噪音音乐子类型的清单长得离谱——每一种风格(黑暗氛围、强力噪音、噪音/冲击)、意识形态(军事工业)和技术(死呛)的细微差别都表明听众正在不断完善他们的听觉能力。
最终,音乐让我们面对模糊性,寻求解决方案,并在缺乏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通过沉迷于它的模糊性和含糊性,将混乱变成一种积极的情绪。回顾过去,只要有音乐存在,噪音就与音乐密不可分,包含了对鸟叫声、动物声音和街头小贩的叫声的模仿。说沉溺于噪音是我们应付噪音的方式,这听起来很讽刺,但事实如此。声音与身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本能的、令人迷惑的反应,从字面意义上让我们动了起来。
有一次,我坐在机场的登机口,噪音让我抓狂。我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取得了一些成效。飞机起飞时,之前只是令人讨厌的响声却变得不祥和具有威胁性,让我联想到飞机解体一切崩溃的转瞬即逝的画面。我对每一个无法识别的噪音都变得异常敏感。我戴上耳塞,听起了Kiss乐队的《Rock and Roll All Nite》。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