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在游戏之外、现实之中。

来源:视觉中国
按:前段时间,京东面向商家发布了一张游戏禁售名单,《侠盗猎车手》《动物森友会》等87款游戏在列,《荒野大镖客》《侠盗猎车手》等部分游戏被认为含有暴力因素。许多人愿意相信,游戏中的暴力和色情成分会促使儿童及青少年模仿,影响其心理健康,并可能导向犯罪。一些心理学研究也为这种论调背书。例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尔伯特·班杜拉就通过一组对比试验发现,观看过殴打充气小丑行为的儿童在沮丧生气时更容易模仿这一暴力行为。
还有一些类似的研究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但有批评家指出,这些试验将儿童的暂时攻击性和竞争性和暴力犯罪行为中的攻击性混淆了。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在进行范围更大、样本更多的研究后发现,视频游戏销售增加的时间段,犯罪率和犯罪致死人数实际上下降了。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有可信的研究证明玩暴力游戏和暴力犯罪行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和许多玩家的亲身体验一样,美国教育记者格雷格·托波通过研究调查发现,游戏者能够分清何为现实、何为幻觉,游戏世界中的某些行为或许会在现实的感觉中延宕,但这不代表游戏中的杀人抢劫行为会成真,说起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犯罪问题的因到底在哪里,他引用游戏研究学者詹姆斯·保罗·吉的一句话很有启示:“在暴力的家庭里把游戏当保姆用,游戏就是坏的。”
托波在《游戏改变教育》中回顾了暴力游戏与暴力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和批评,以及美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摘编了相关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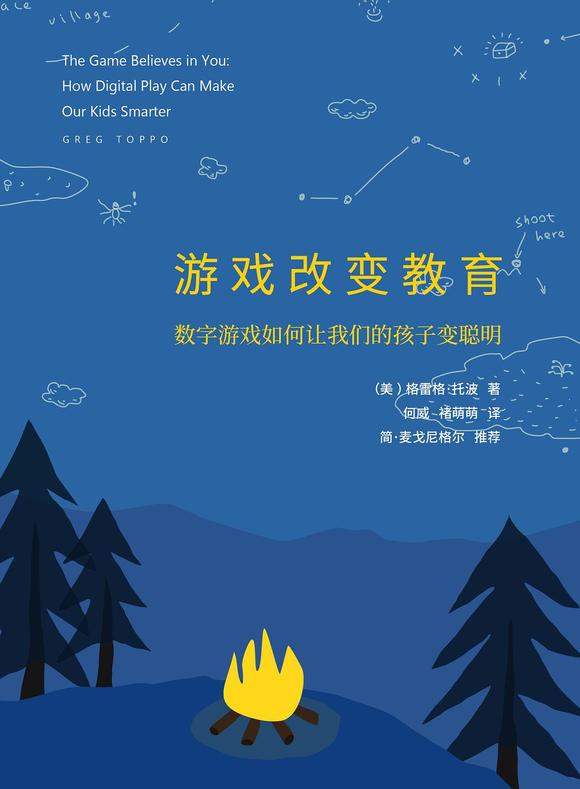
文 | [美]格雷格·托波 译 | 何威 褚萌萌
我是在关注教育游戏,而很多教育游戏是由教师设计的,绝大部分教育游戏当然也获得了教师们的赞同和许可。像《侠盗猎车手:罪恶都市》这样的具有开放世界特点、评级为成人级的游戏,很少会有老师布置学生们在课上玩或者留作课后作业。但当我告诉别人我在写一本关于游戏的书时,他们总希望我谈谈游戏暴力,以及他们看到的自己孩子沉迷于某个游戏的现象。他们想要我谈谈《杀手》《光环》《生化危机》或《行尸走肉》。他们想要我谈谈科伦拜恩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儿子那么不情愿停下《我的世界》游戏,先去完成家庭作业。家长们想要知道,他们纵容了自己孩子对游戏的热爱,其中还有些暴力游戏,这是否让他们成为了坏家长?
对此,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一个稍微长点的回答是“看情况”。一会儿我还会再做解释。但此时此刻,我觉得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几十年来,研究者们都没能在玩暴力游戏和表现出真实暴力行为之间找到可信的因果关系。一些统计学研究事实上还发现,加入暴力视频游戏的因素后,暴力行为呈下降趋势。这并不是说游戏没有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游戏是被设计来产生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大部分人认为的那种影响。
暴力媒介和暴力行为之间暗含的行为联系,长久以来便存于我们脑海中,如跗骨之蛆般难以剔除。这个观念至少产生于一百五十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教育家、品位锻造者和牧师们开始对一种粗俗的流行文化进行批评。届时,暴力的、色情的“一角钱小说”和“便士杂志”在社会上极为流行,定位高雅的《哈泼斯》杂志和《大西洋月刊》则不惜笔墨地谴责前者。在某期社论漫画中,一名出版人将垃圾小说递给了孩子们,他背后的标牌写道:“一把不错的手枪!如果每年都订阅的话。”作家和批评家哈罗德·谢克特曾在2005年写过一本关于暴力娱乐的社会历史学书《野蛮的消遣》(Savage Pastimes)。他指出,这种潮流甚至将文学圈一分为二。拉尔夫·瓦尔多·艾默生抱怨他那个时代的国民“每天都在便士报纸上读谋杀和铁路事故”;但纳撒尼尔·霍桑却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当他在海外担任美国领事时,他甚至请朋友将一摞摞的报纸船运到利物浦去给他看。艾米丽·迪金森热爱读“那些因铁路撞到一起而导致的搞笑事故,或者工厂里的绅士怎么一不当心把脑袋切掉的故事”。
进入20世纪,更多批评纷沓而至。1936年,天主教学者约翰·莱恩罗列了他称之为“美国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精神食粮”,这些精神食粮是从消费媒体中获得的。名单很长,包括如下:“虐待、食人、兽行。原始性冲动。折磨、杀戮、绑架。怪兽、疯子、半兽人。耸人听闻的情节故事;犯罪和罪犯的故事;在陌生之地和其他星球上的疯狂开发;海盗的故事;男英雄和女英雄的狂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故事;关于丛林野兽和人类的图文并茂的、惊心动魄的描绘;关于魔法和伪科学的奇妙之事。粗俗、廉价的幽默和更加廉价的智慧。为智商低下者的平均水平设计的伤感故事。思想与表达的丑陋。”他谈论的是日报上的四格连载漫画。
1947年,批评家和演员约翰·豪斯曼,也就是后来在《平步青云》(The Paper Chase)一片中定义了古板的学术界形象的演员,对大部分孩子在电视上看的卡通片提出了类似的指责。“我们孩子满心欢喜看的那些奇幻故事里充满着可怕的野蛮行径,”他写道,“现在的动画片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战场,脑子里只有一条筋的野人和永不退缩的野兽在其间互相追逐,撕咬、啃啮、扭斗,最后以残虐的狂暴将对方撕个粉碎。”
斯坦福的心理学家艾尔伯特·班杜拉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并为限制儿童对暴力媒体的接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做这些研究前,他已对儿童的暴力行为苦心孤诣研究了近二十年。通常来说,在孩子们表现出暴力行为后,对他们进行惩罚或奖赏会产生效果。1961年时,班杜拉想通过研究了解,观看别人在暴力行为后得到惩罚或奖赏,能否对观看者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革命性的。B.F.斯金纳及其同僚已经向世人展示,人们对正面的强化和负面的强化的反应都是可预料的:如果我揍自己的妹妹,就会被家长吼,所以也许我不应该揍妹妹。但如果我只是看别人因同样的行为受惩罚呢?那也会对我产生约束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别人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呢?
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学的附属幼儿园找到了72名学前儿童,最小的3岁,最大的5岁9个月,年龄中位数为4岁半。班杜拉的实验室助理一次带一名儿童进入游戏室,安排他们坐在小桌子前,教他们用土豆章印图画。随后一名成人进入游戏室,待在对面角落,带着一套万能工匠玩具套装、一根木槌和一个五英尺高的充气小丑不倒翁“波波”。这个不倒翁的底部是加重的,因此被击倒后会自己再竖立起来。这名成人要么对“波波”置之不理,以“安静、柔和的态度”拼装玩具套装;要么对充气小丑持续“施以暴力”:拳击充气小丑、把它打倒并坐在它身上、击打它的头部、把它踢得满屋子打转,同时嘴里说着“对鼻子一击”、“把它打倒”、“踢它”和“俘虏”之类的话。十分钟后,每个孩子都被带离去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相对更具吸引力的玩具”,例如一部救火车、一个火车头,一个彩色陀螺,以及一整套娃娃玩具。孩子们受邀玩这些玩具,但只玩了两分钟,就有一名实验室助理前来宣布所有这些玩具都是“她的最好的玩具”,不允许别人玩,并表示决定将这些玩具收起来给其他小朋友玩。之后,孩子们被带到第三个房间,这里有更多的玩具,有的“具有攻击性”,有的“不具攻击性”,它们包括:一组茶具、蜡笔、飞镖枪、一根木槌……和一个三英尺高的充气小丑。现在你知道这个实验要走向何方了。
刚刚玩到有趣的新玩具,玩具就被人抢走,这种沮丧感使得那些目睹了“波波”被暴力对待的学前儿童,比那些没有看到暴力行为的儿童,更容易把气撒在小号“波波”身上。如果在前一个房间里打充气小丑的人是男性,男孩就会有两倍的可能性表现出暴力行为。班杜拉在1963年重复了这个实验,加入了暴力击打充气小丑的电影版和卡通版材料,并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结论看起来很明确:在真实生活、电影或卡通中观看不受约束的暴力行为,会使我们变得更暴力,因为它们提供了“社会脚本”(social scripts)来指引我们的行为。班杜拉的研究打开了“媒体效果”研究的大门,这类研究延续至今。

但问题在于,许多这类研究的结果是误导人的,更糟糕地说还是危险的。批评家杰拉尔德·琼斯在2003年的《杀死怪兽》(Killing Monsters)一书中,写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提倡让孩子接触“奇幻、超级英雄和虚构的暴力”。他这样来看待“波波”:“没有证据表明,击打充气小丑与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有任何关系。”他写道,“没有证据表明,喜欢击打充气小丑的孩子更可能在操场上有暴力行为,或者更容易在青少年期犯罪。”倒是有道听途说的证据表明,打小丑反而是有益处的。然而,打小丑中发生的事情被一代代研究者记录下来,当做“被强化的攻击性”的证据。琼斯以及其他人还说,在许多案例中,研究者挖掘的是实验对象暂时的攻击性,但却给它贴上了错误的标签,认为它可能导致暴力行为;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他们挖掘的是天性中的竞争性,却也称之为攻击性。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只是将所发现的不快和不安解读为攻击行为。在班杜拉首次充气小丑实验十多年后开展的一项研究经常被人引用。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观看了《罗杰斯的邻居》(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的学前儿童,比其他儿童表现出三倍的攻击性。琼斯认为,该实验强制儿童在规定时间看电视,因此实验本身可能已经让儿童感到焦虑或者愤怒。“我喜爱弗雷德·罗杰斯,”琼斯写道,“但我怀疑,如果我更想出去玩的时候,却被迫坐在一个陌生房间的硬塑料椅上盯着罗杰斯,那我也会表现得有攻击性。”
儿童心理学家劳伦斯·库特纳和媒体研究者谢里尔·奥尔森写道,媒体暴力和现实世界暴力之间的关联是从“差劲的或者不相关的研究、稀里糊涂的思考和简单化的新闻报道中”得出的。在某个案例中他们发现,曾发布理性媒体使用指南的美国儿科学会(AAP)在2001年断言,“超过3500个研究调查了媒体暴力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其中只有18个研究没有找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这个数字被当做媒体研究的真理。但当库特纳和奥尔森搜索这个数字的来源时,他们发现这并不是来自于某项研究,而是来自一本1999年出版的名叫《停止教孩子杀戮》的书的脚注里。这本书将暴力电影、电视和视频游戏和军队在越战时期的脱敏训练相提并论。本书的作者是退休的美国军队中士戴夫·格罗斯曼,他以称视频游戏为“凶杀模拟器”而闻名。他在一篇1998年发表于瑞典的文章中找到了这个数据。文章署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文章并没有提供有关“正相关关系”断言的任何信息,或者是谁如何取得3500这个数字的信息。直到今天,当你用Google搜索“3500个研究”时,你仍会得到25万的搜索结果,其中绝大部分都不加批判地提供了美国儿科学会的声明。
视频游戏已经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自1996年以来销售已经翻番。随着游戏的愈发流行,青年中的暴力是否也同步翻番了呢?事实上,正好相反:根据官方数据,从1994年到2010年,青少年犯罪的数字减少了一半多。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德认为,如果短期攻击性行为是个问题,它就应该很快在犯罪率上表现出来。沃德在2011年提出,随着国内视频游戏商店的增多,犯罪率和犯罪致死人数上都出现了“显著的”减少。而与此相比,他发现体育用品店或电影院的新开张,对于减少犯罪率和犯罪致死人数来说,要么效果更小,要么毫无效果。沃德及其两位同事研究游戏的规模时,还发现暴力游戏的高销售率事实上对应着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的下降。在另一方面,非暴力游戏的销售对犯罪率并无影响。

但如果媒体能教我们成为更好的人,难道它不会教我们成为更差的人吗?这不可能是一条单行道吧?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道格拉斯·A.金泰尔写道,不管我们反复练习什么,练习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如果我们练的是攻击性的思维方式、感觉和反应,“那么我们就会更擅长这些”。他说,尽管很难归结于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当我们“练习对敌人保持警惕,并对潜在的攻击威胁做出迅速反应时,我们正在演练这一脚本”。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他和同事发现暴力视频游戏“看起来是攻击行为的模范教师”。他们发现,玩大量暴力视频游戏的人,和同时玩暴力和非暴力游戏、或只玩非暴力游戏的人相比,“看起来能更好地转化攻击性认知和行为”。他们还发现,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中玩暴力游戏频率更高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归因偏差”,即对敌人很警惕,并和老师产生更多的口角。
认知科学家达芙妮·贝弗利尔和心理学家C.肖恩·格林在这一点上有所让步,但他们更为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单单暴力视频游戏本身“不太可能将一个没有其他风险因素的孩子转变为一名狂热的杀手”。但是在那些拥有其他许多风险因素的孩子身上,暴力视频游戏的效果“可能足以产生实际上负面的后果”。在这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不停止担心孩子们的媒体使用,而去处理那些风险因素?
游戏研究学者詹姆斯·保罗·吉认为,游戏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一切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们。如果适度玩游戏,并得到成人的指导或者朋友的协助,游戏就是有益的,具有持续的认知效应和社会效果。“在暴力的家庭里把游戏当保姆用,游戏就是坏的。”他说。当被问到,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的原因与视频游戏有关,他给出了最好猜测:没有,或者五、六个。我们真的无从得知,因为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玩视频游戏,这真是太神奇了。”
詹金斯可能提供了这个谜题的最佳答案。“当媒体在强化我们已有的价值观时,它是我们生活中最强有力的,”他写道,“当与我们价值观不符时,则最无力。”如果我确实相信我需要对真实生活中的敌人保持高度警觉的话,玩过的游戏就会有效地作用于我。如果我不这么想的话,游戏的作用微乎其微。游戏不会改变我的人格。詹金斯写道,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对视频游戏的反应和他或她对真实世界的创伤的反应方式一样的话,那这个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情绪障碍的症状。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暴力游戏实际上可以被用作一种负担得起的、有效的诊断工具。但除此之外,用充气小丑玩具来标记真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的媒体效果研究,是有问题的。“孩子们去击打一个本来就是用来被击打的玩具,此时他们仍旧处在游戏的‘魔圈’之中,也仍然要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其行为,”他写道,“这样的研究只能向我们展现出,暴力游戏会带来更多的暴力游戏。”
20世纪60年代,当班杜拉展开媒体效果研究时,伟大的英国民俗学家艾奥娜和彼得·奥佩夫妇花费数年去观察和研究孩子们的户外游戏。他们观看孩子们玩游戏,这些游戏大多有《地下触碰》(Underground Tig)、《煮锅里的女巫》(Witches in the Gluepots)这样的名字。他们总结道:“一个真正的游戏是能够释放灵魂的。它没有温情脉脉,只有游戏本身能触发的想象中的人物。”当儿童痴迷于这些游戏时,他们退出了俗常的世界,“他们生存的界限变成了邮筒这边的两条人行道,他们的现实变成了躲避追逐者触碰的激动。”尽管这项研究似乎是一种延伸,但我们也应当把同样的规则用于青少年玩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在一个孩子能够全心投入而无需向他人解释的游戏中,”奥佩夫妇写道,“他能成为一个好的玩家,无需思考自己是否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他发现自己成为别人的有用的拍档,哪怕那个人是他平时害怕的人。”
最后我要清楚地说明,从外部看起来似乎是杀戮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知名游戏理论家布莱恩·萨顿-史密斯说,从某个角度看,正好相反。无论是在现实游戏中还是视频游戏中,孩子们玩耍时的打斗,都常常只是一种模拟,效果可控,不想要伤害真实生活中的对手。“这也许是一种打斗的展示,”他写道,“但它也是打斗的对立面,因为参与者们不是彼此的敌人,也不想互相伤害。游戏者们总是会使用特殊的面具或者标志来代表不同的种群,其传达的信息是,自己的目的只是玩耍。相比真实的打斗,打斗游戏只是一种模拟和类比,而且它更多地是在展示打斗的意义,而不是一场真实战斗的演练。这更多地关乎意义,而非攻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手指指错了人。当我们担心暴力游戏会将我们的孩子变成杀手的时候,难道不正是我们自己,才是那种没法分清幻想与现实的人吗?孩子们早已知道这个区别。我们才是不能区分两者的人。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游戏改变教育》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