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丰富的记者兼作家芬坦·奥图尔通过深入探究爱尔兰60年来变革和繁荣的神话,为他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爱尔兰描绘了一幅丰富且细致入微的图画。

1981年,贝尔法斯特,支持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鲍比·桑兹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的游行。图片来源:Jacob Sutton/Gamma-Rapho/Getty Images
“我这一生,直到1980年,一直被告知要把自己看作是某件事的终结和另一件事的开始。”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写道。奥图尔的新作《我们不了解自己》(We Don’t Know Ourselves: A Personal History of Ireland Since 1958)内容丰富、具有权威性且充满睿思才情,从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历程这一独特视角,对现代爱尔兰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同时对爱尔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变革提供了深刻而且精彩的分析。
他写道,爱尔兰“当年以一个停滞不前和无足轻重的形象进入了战后迅速发展的世界”。爱尔兰有着很高的移民率,婚姻率却低得吓人。在1949-1956年间,当时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GDP普遍增长了42%,英国增长了21%,爱尔兰只增长了8%。1961年,爱尔兰的人口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只有210万。那时的爱尔兰面临着抉择:“是接受并开放自由贸易,还是继续保持作为一个受保护但日益孤立的地区。”
1958年,也就是奥图尔出生的那一年,被称作“现代爱尔兰的建筑师”的时任财政部长T·K·惠特克(TK Whitaker),撰写了一份名为《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的文件,目的是促使爱尔兰的经济从贸易保护主义走向开放的自由贸易,从而获得经济的增长。理论上,这一举措应该能够将爱尔兰引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但实际上,这份计划只是帮助爱尔兰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事实证明,仅仅靠一份计划还不足以将整个国家引向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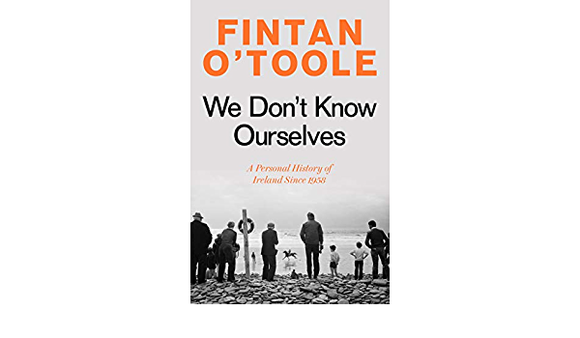
如果说奥图尔的书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任何事都很难做到简单的泾渭分明,任何事实都不一定值得完全相信,同样,任何谎言也不会百分百全是虚假的。如果发现有的政客说了与他自己之前的言论完全相反的话,奥图尔写道:“至于那些政治方面的谎言,通常总有一些真相存在于某处等待被发现,而谎言恰好是真相的反面。但是这类谎言只是一种自由漂浮的实体,真相和谎言不过是两个相反的概念符号,并没有真正的所指。”当谈到一桩涉及谋杀和司法部长辞职的奇怪政治丑闻时,他写道:“真相本身缺乏可信度。”
在爱尔兰,那些支持经济改革的年轻政客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是不可以信任的。1962年,当时被视为改革派政治家的查尔斯·豪伊(Charles Haughey)拜访了都柏林大主教,表示他对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的小说《孤独的女孩》(The Lonely Girl)“非常厌恶和抗拒”。对此,奥图尔写道:“豪伊对伪善的精通,已经达到了能够十分精妙又有权威地运用的程度,实在令人着迷。”
在这本书中,奥图尔清楚地剖析了爱尔兰与美国之间的奇特关系。当爱尔兰在1961年拥有了自己的电视台时,超过一半的电视节目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于是,《Cisco Kid》、 唐娜·瑞德、《艾德先生》和江湖奇士(Bat Masterson)等这些美国娱乐节目和人物自此进入了爱尔兰人的梦境。1963年6月,当约翰·肯尼迪在爱尔兰总统官邸参加一场游园会时,人群将他团团围住。当时的一家报纸这样报道:“这简直是粗鲁、不礼貌、无知和缺乏教养的表现。”奥图尔写道:“那时的爱尔兰社会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才是恰当和得体的,于是形成了一股几乎失控的力量。”

尽管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底层的人仍然感到沉重的压迫感。奥图尔引用了一名非婚怀孕的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词:“我得知,像我这样身份的人生下来的婴儿通常会被装进棕色的纸袋里,然后遗弃在厕所里,而我也决定这么做。因此,我开始随身携带一枚硬币,随时为进入厕所生孩子做好准备。”
但是,当变革真的到来时,它却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形式。当奥图尔还是一名学习爱尔兰语的学生的时候,他去了西科克,在那里他见到了爱尔兰音乐家肖恩·奥瑞雅达(Seán Ó Riada)。这位音乐家带领当地的唱诗班,致力于改变传统的爱尔兰民间音乐:“他们的音乐旋律悠长且呈延绵不绝,因为是齐声合唱,所以听起来似乎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当你继续仔细聆听,又感觉旋律渐渐释放开来,展现出轻柔但克制的装饰音,然后再次回归之前徐缓悠长的线性旋律。”与此同一时期,美国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席卷了整个爱尔兰,舞厅里基本都在播放来自美国乡村音乐之都纳什维尔的音乐和最新流行的热门歌曲。“到1960年代中期,爱尔兰有近700支专业乐队仅靠在舞厅进行巡回演出为生。”
“那时我们相信南方是自由的,”奥图尔写道,“北方则是不自由的。”不过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任何类似这样的句子,都是为了表现讽刺意味或产生歧义而有意为之。当爱尔兰的女权主义者在南方为争取避孕权而发起抗议运动时,他们发现北方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了数个光年。
奥图尔意识到,因为远离民族主义运动,他更直接体会到了1980年前20年时间里,爱尔兰南方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所发生的变化。他写道:“爱尔兰已经从‘牛就是命根子’的农业经济,转变到几乎成为国际工业秩序的一部分。”1972年,爱尔兰出口了价值3500万英镑的电子产品;到了1982年,这类产品的出口价值已经高达每年10亿英镑。
爱尔兰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几乎完全是由来自国外的投资推动的。2017年,“美国对爱尔兰的直接投资存量总计达4570亿美元,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和瑞典的投资存量的总和还要多。”然而,在爱尔兰收集统计数据,尤其是基于年度GDP的统计数据,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5年,爱尔兰的GDP增长了26%,但正如奥图尔书中所写,“那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奇迹。”
但是按照奥图尔的分析,奇迹本身就是一种海市蜃楼。奇怪的是,另外一些统计数据确实是真实可信的:例如1995-2000年间爱尔兰出口总额确实翻了一番,1988-2007年间爱尔兰的就业人数也翻了一番。
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奥图尔写道:“旧的体系内部正在崩塌,但新的形式还没有完全诞生。”他的这本书找到了爱尔兰引发内部崩塌的力量,并且为理解过去60年爱尔兰暗流涌动的复杂状况以及令人困惑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合理而有趣的方式。
本文作者Colm Tóibín是一位爱尔兰作家,他2008年出版的小说《布鲁克林》被评为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空巢家庭》曾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奖短名单。2006年,他被任命为爱尔兰艺术委员会成员,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尔兰文学讲师。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