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的,既有在课堂上教过我们的人,也有一些远方的、与我们素未谋面的人。

图片来源:图虫
004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栏目“编辑部聊天室”。每个周日,界面文化为大家揭晓一次编辑部聊天记录。独自写稿,不如聊天。我们将围绕当周聊天室主持人选定的话题展开笔谈,或严肃,或娱乐,神侃间云游四方。鉴于主持人们各有所好,聊天室话题可能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和社会热点事件,也可能从一口路边小吃、一次夜游散步、一场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开去。
本期聊天室由文捷主持,想要讨论“人生导师”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9月10日教师节刚刚过去。教师是我们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家长以外的重要权威人物。他们既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言传身教中让我们体会什么是好的品格,由此成为我们整条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当然,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的,除了在课堂上教过我们的人,还有一些远方的、与我们素未谋面的人。他们以语言、以态度、以人格魅力给我们思想上的启迪,改变了我们,塑造了我们。
潘文捷:我遇到过一些很好的老师——比如说一位小学老师在几个学生起纠纷的时候,并不认为这只是孩子之间的打闹就随便打发了,而是仔细聆听每个孩子的发言,并不因为哪一方人多,或者哪一方的音量更大就偏袒哪一方;高中时有一位班主任,没有因为我在他的科目上成绩不够好就对我冷眼相待,反而让我当课代表,以此激励我学习(没有亲戚关系,也没送礼)。这些都是我一直牢记在心的,想起他们,我就觉得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给别人带来温暖和激励。
但是并不是每位老师都那么可爱。有的老师虽然教学水平很强,但是对校园暴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时不时踩一踩被孤立的同学;有的老师对孩子赏罚分明——对家长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学生格外青睐,对家境普通的学生连对方问一道题该怎么解都懒得回答……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和家长选择对老师“溜须拍马”,一些人选择对老师的恶劣行为忍气吞声。有时候哪怕我不是那个受害者,我也会感到很无奈和难过。我想,这些老师只能说是拥有了“老师”这个职业,并不能真正算得上是为人师表,而且甚至起到反作用——让孩子们看到,去讨权威的欢心比做正直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重要。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导师”——让我警告自己永远不要变成那样。
林子人: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人生导师就是电影《死亡诗社》中的文学老师基汀先生——他鼓励学生“离经叛道”,在文学世界中徜徉,勇敢追问生命意义。很幸运的是,我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生导师,他就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郭老师让语文课变成我每个上学日最期待的课:他会将许多课本以外的内容引入课堂——其他的文学文本、报纸杂志甚至电影——很多时候,语文课不是老师灌输、学生听讲,而是学生们各抒己见的研讨会;我们举办过诗歌创作比赛、组织过作文比赛投稿、排演过《雷雨》的话剧,还以媒体上的特稿为模板做过调查然后撰写(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研究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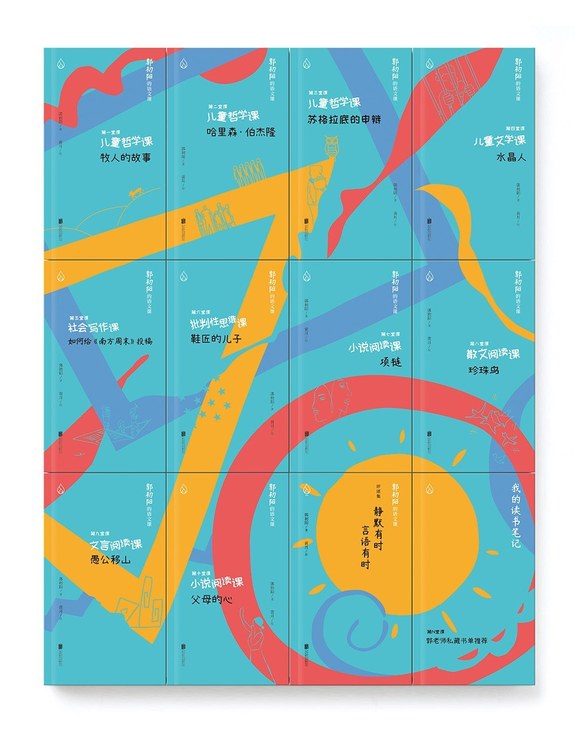
回想过去,我觉得郭老师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没有把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当小孩子,一直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对待我们,相信我们的智识能力能够参与思考和讨论真实的社会议题。在三观还在逐渐形成中的十几岁的年纪里,学生能够从一位老师那里得到的最好的馈赠,就是获得某种智识上的开放性和不断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好奇心。是这种开放性和好奇心驱动着我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自己。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
叶青:学校里的老师,我遇到过两种“好老师”,一种是大家长式的“我都是为了你好”的老师。比如我初中的科学老师,每次上课前都要抽背知识点,答不出便直尺抽掌心伺候。还有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因为我成绩下滑,打了我一巴掌,结果她自己哭了。他们二人可能都觉得,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学生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是怒其不争,但他们的做法只让我变得更加抵触学习。
另一种好老师和子人的语文老师类似,他们更倾向于引领学生,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像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我本来特别讨厌英语——背不完的单词、(在当时看来)毫无逻辑的语法、拗口的读音。但她上英语课不是照本宣科,有时会抽出一些课(即便是在学业繁重的高三)来教我们唱一些英文老歌,介绍英文电影和美剧给我们看。我开始觉得,学习英文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它慢慢变成了让我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如今我从事跟英语有关的工作,偶尔听到《Hey Jude》还是会想起大家在教室里合唱的场景。而反观初中和小学,我记得的似乎只有一片空白和身体上的疼痛了。

董子琪:特别奇怪,我喜欢听人说教,特别是说一不二讲大道理的那种。最早发现喜欢这点是在初中班主任开班会,别人都很讨厌班会,觉得浪费时间,不能说话也不能做题,可我却觉得说教有一种美感,什么都不用做,容许你听着听着就走神放空,同时还得到一种坚定的道德方向感。因为说教不光是激励学习的“天道酬勤”“笨鸟先飞”云云,还包括为人的修养劝诫乃至警告——“你家交的五千块钱赞助费要扔水里了。”实际上,我又是不会听得进去道理的主体,只喜欢班主任说教的感人姿态,有教无类,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同时又为自己的感动感到惭愧——班里其他等待踢毽子和刷题的同学高兴吗?
这样立场鲜明的说教在上大学之后消失了,文学系的老师尊重学生崇尚自由,在推荐书时都会说,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读什么都是一样好,这反而让人觉得迷惑。我原来问过一位老师,总这样建议学生,难道不太过相对主义了吗?潜在的问题是,如果所有文本都一样好,荒草与经典没有区别,那么文心和诗品不就没有意义了吗?这实在是矛盾的,从初中的强制说教到大学的放任自流,我懂后面遇到的才是良师,他们想要为学生保留一丝属于灵魂的自由,前者也许只想收获一模一样的绵羊(又没有聪明到辨识出绵羊中的伪装者),而那东飘西荡的自由又注定是让人的骨头都变得“懒散”的,因为不如“你家交的五千块扔水里了”那么粗暴、勒出青筋般的清晰。
好像我见识到的两种老师就是这样,良师充分地信任学生,让他们有选择的余地和犯错的空间,但彼此的交流像是一场彼此都很欣赏但逐渐陷入迷惘泥沼的seminar,而初中班主任这样兼带体罚和辱骂的老师是如此迫切地希望你集中注意力、抛掉羞耻心跟随他一起战斗,如果听从这种指导,你会变得足够有效率,因为缺乏具体的感受成为幸福又自足的人。
黄月:“老师”这个词通货膨胀了,年过三十,叫过老师的人不少,被叫老师的场合和次数也多了。倒不一定要把心思集中在这个称呼上,如果生活中真的有机会可以向很多人学习很多事情,比如跟A学习力量训练技巧、跟B学习鸡枞烹饪方式、跟C学习流行文化趋势,真正能实现具体场合下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多美好的一件事。我觉得我这份编辑工作的乐趣之一也正在于此,看不同记者的稿子也是认知、理解和学习的过程,学到一些我没有读过的书、我没有听过的事情、我没有想过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她们都是我的老师。
至于那些在9月10日过节的我的真正的老师们,他们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人。有为了保住班级名次和奖金千方百计把成绩最差的学生开除的数学老师,也有脾气一上来抡起课本就砸学生脑袋的物理老师,有常年受学年主任和其他老师排挤、但在边缘位置上自得其乐享受和学生们相处的语文老师,也有虽身处边远的东北小镇、但没有一天不早起看英语新闻背英语难词看英文经典的英语老师。在这些老师的课堂上,我还是个小孩。时至今日,我依然和其中一些老师保持联络,或是偶然听人提起ta们,认识最久的一位老师几乎见证了我从6岁到今天的成长变化,而我反过来也是ta们的见证者,看着ta们变老,幸福或者波折,我们之间最后结成了某种比师生关系更为复杂的关系。
叶青:就像黄月说的,牛老师、尤老师、刘老师,各类老师真的太多了。在媒体行业更是如此,开场白永远是X老师好,前几年刚工作的时候我特别不习惯,每次对方叫我叶老师,我都会一阵莫名心虚,心想我何德何能,能冠上老师这个称呼,您还是叫我小叶吧。
潘文捷:在一位班主任的高压之下,我开始寻求远方的慰藉,并寻求到了我第一位可以说是“学术偶像”也可以说是“人生导师”。令人伤感的是,我最初的人生导师也遭遇了“人设坍塌”。那是我中学的时候,读到一本尼采研究著作,被作者的文笔和思考深深打动,打开了和教科书上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的大门,那段时间沉迷于思考,考试时在作文纸上奋笔疾书,抒发自己对尼采思想以及对这位作者的崇拜之情,超出了十多行后,糊上草稿纸继续洋洋洒洒。
上大学后,我得知了这位学者对待自己妻女的事迹。一开始还残存幻想,认为这些可能是谣言,后来尤其是亲眼看到这位导师发出的微博中,有“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之类的字句。
人生导师的垮掉可能正如同粉丝眼中的偶像塌房。我在这件事里学到的是,不要把任何人神化。不要对人们期待太高,他们都是普通人,而且一个人的成就和人品是应该分开看待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人生导师都会有阴暗一面,远非如此,我就从书本和现实中遇到过一些了不起的人,不论是哪方面都可以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更加明白的一点是,在尊重人生导师指引的同时,也不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放得渺小。同时,我还学会了不去过分寻求一个远方的素未谋面的“导师”来充当人生困境的拯救者,而是从身边的人、同龄的人身上明白更多。

陈佳靖:前不久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胡续冬逝世,我看到很多他的学生在社交网络上悼念他,有人提到,胡续冬之所以特别受学生们爱戴,是因为他和其他老师在对待学生的方式上有明显不同。从学术水平、授课能力以及个人素养来说,北大优秀的老师数不胜数,放眼全国、全世界也是同样,但很少有老师和学生能在校园之外建立起深厚而长久的关系。胡续冬对很多学生来说不仅仅是教授知识的老师,也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据说很多学生毕业多年后,哪怕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会找他帮忙,他都乐意为之。这种不设期限、超越校园之外的师生关系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和我保持联系很久一位老师曾经说,她现在已经不像过去教我们的时候那么能投入感情了。她的意思是说,当然还是要认真教课,尽可能成为学生的启蒙和向导,但这种关系可能仅限于几个学年。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时代的变化——她的学生对学校的期待变了,家长对老师的要求也变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家长除了定期参加家长会或某些特殊情况被“请”去学校之外,几乎不会和老师有直接的接触,学校里发生的无论是学习问题还是个人问题都是老师和学生在沟通和处理。但如今,我的这位老师每天都疲于应付家长发来的消息,学生也学会了请父母来学校帮自己出面解决问题。老师的主要职责似乎从教书育人变成了监督和汇报,老师这一身份不再被天然地信任、尊重和仰赖。
姜妍:羡慕子人在初中时代碰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我就比较惨了。初中的班主任是一位数学老师,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位很擅长对学生进行精神PUA的老师,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这道题连弱智都会。她经常在黑板上写一道题,然后学生全体起立,做出来的人才可以坐下,她再从坐下的人中选出一位她认为是假装做出题的孩子到黑板上解题。她还会把全班同学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选出几位小组长,轮流从黑板上挑选组员。她经常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数学竞赛,所以最后数学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名字就会被剩在黑板上,非常刺眼。这位老师还喜欢在同学间发扬互相检举的风气,在背后打小报告的同学都会得到她的表扬与鼓励。

赵蕴娴:我还是要提到我妈。倒不是说我把她当作老师,而是我一直隐约感觉到,自己成年以前和老师的关系总有她介入。因为小时候是转校借读,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平时在家又有点沉默阴郁,我妈总怀疑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校内,于是就悄悄拜托老师,对我多加留意。但情况恰恰相反,我在学校里很活跃,至今为止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校园生活有何异常,或许我从小到大的几位班主任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总感觉她们对我有一点特别的关注,但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很少干涉我,就好像我们默契地达成了一致,以应对我妈的担忧和焦虑。每每出现点到即止、心照不宣的时刻,我都会有一种街头小混混和相熟的警察交换眼神的快感。
可能大部分人的生活里都很难出现郭初阳那样完全把自己和小孩对等的老师,遇到姜妍说的那种PUA式教师倒是不少,不过我想还有一类老师或许是我班主任这样的。在家长面前,她们保持了成人与教师的威严,行使着管教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中间有很多可以滑动的地方,老师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在管教,有时候可能也只是一种表演,小孩或许还是她们的同谋,合作或是对抗,可能受是否有第三方存在的影响。
姜妍:我觉得“老师”和“导师”在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就像黄月说的,只要在生活中能给予我某些灵感,让我觉得在某件事上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人,都是我广义上的老师。但是像文捷说到的“人生导师”,其实多少包含了一种“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的概念,这里也包含着自觉不自觉的学习和模仿,所以才会有之后对她来说的人设崩塌的幻灭感。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个时代性的特点,比如说,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为大多数年轻人心目中的人生导师。我猜想,应该并不来自知识界。
抱歉我要再次提及唐诺的《声誉》这本书(因为不久前在讨论一星运动的时候刚刚引用过),这本书想要讨论的三个关键词是声誉、权势和财富,在思维和工作领域相对应的是历史学、政治学(也许已转向大众传播)和经济学(也许已是金融了)。我们从这三个领域的冷热消长,就可以看出三者在现实中的相关变动。或者我们再看看在生活里,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节目中更愿意使用“导师”的概念,也大概可以推测出个一二。
今天是一个历史已经式微的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和资本无限膨胀的时代。唐诺在书中说,他高中时台湾地区流行存在主义哲学,校园里总会看到有人拿着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书走路,因为那时候人们仍然相信能读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好的、高端的,仍相信世间有些你得仰头看它、带着虔敬畏惧之心的好东西,这样,这些好东西就有了机会,人自身也有了机会,生命景观不至于这么扁平,这么荒凉空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