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说,自然界的事物是没有内在意义的,而把握自然最重要的方式是观看。


成名于20世纪的佩索阿与16世纪的伟大诗人卡蒙斯并称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评价说:“佩索阿是令人惊奇的葡萄牙语诗人,此人在幻想创作上超过了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声誉,是因为佩索阿以迷人的“异名书写”筑造了一个富饶神秘的文学宇宙。据不完全统计,佩索阿使用过的“异名”至少有一百多个,其中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甚至还有占星家、心理学家、记者等。这些“异名”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假名”或“笔名”,而是代表了一个个拥有不同人格、职业、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的个体。在佩索阿的不同作品中,他们甚至会彼此通信和交往。
除了写作《惶然录》(又名《不安之书》)的索莱斯之外,佩索阿使用的最重要的异名有三个,分别是诗人卡埃罗、冈波斯和雷耶斯。其中,卡埃罗是冈波斯的导师,被其他异名者尊为大师。他最大的特点是倾心于自然,著名的组诗《牧羊人》就出自他之手。在佩索阿笔下,卡埃罗长着金头发、蓝眼睛,是个孤儿,只完成了小学教育,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农庄度过。
近日出版的《我将宇宙随身携带》收录了卡埃罗创作的所有诗歌,包括《牧羊人》《恋爱中的牧羊人》《牧羊人续编》三部分。卡埃罗奉行感官现实主义,抗拒象征主义诗歌的神秘和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因此,他的诗几乎从不使用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意象,给人一种自然、纯真的亲切感。正如他在《神秘的诗人》一诗中所写:“神秘的诗人说花可以感觉……但是如果花可以感觉,它们就不是花了,它们将会成为人”。在他看来,感觉与思想是对立的,因此要真正把握自然,就要摈弃思想,只凭感觉真实地看待万物。
在《牧羊人》中,卡埃罗一再强调对自然的感觉式把握,反对思想式认识。对他来说,自然界的事物是没有内在意义的,而把握自然最重要的方式是观看——“我观看,事物存在。我思想,只有我存在。”正因摒弃了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来认识事物,卡埃罗才被佩索阿以雷耶斯的名义描述为一个“客观诗人”,“这个人描述世界却不假思索,并创立了一种宇宙的观念—— 一种完全抵抗解释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卡埃罗也是佩索阿思想上的一个分身,阅读卡埃罗是我们理解作家的重要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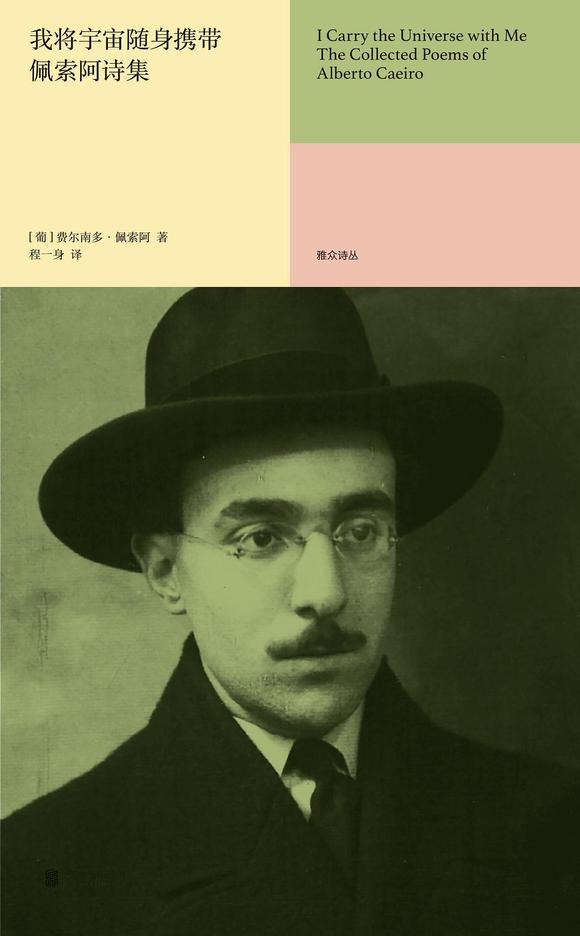
我是一个牧羊人。
羊群是我的思想
而我的思想都是感觉。
我思考用眼睛和耳朵
用手和脚
用鼻子和嘴巴。
思考一朵花就是看它并嗅它
吃一块水果就是了解它的意义。
因此,在一个热天
我由于太喜欢它而感到悲哀,
于是,我纵躺在草地上
合上热辣辣的眼睛,
我感到我的整个身体躺在现实上
我因体验到真理而快乐起来。
如果我能咬整个世界一口
用我的腭品味它
如果大地是可咬入之物
那一瞬间我会更快乐……
但我并不总想快乐。
有时陷入不快
非常自然……
并非每天都是晴朗的。
如果长期不下雨,你就会祈求它来临。
因此,我对待不幸和幸福
很自然,就像有人发现
有高山与平原
有大岩石与草地
并不奇怪一样……
在幸福与不幸中
你需要的是自然和平静,
像有人观看一样感受,
像有人走路一样思考,
当死亡来临,记住死亡的日子,
落日是美丽的,无尽的夜晚是美丽的……
这是它存在的方式,也是我应有的方式……
那个自娱自乐的小孩
用一根麦秆吹出那些肥皂泡
显然是一部完整的哲学。
像自然一样清澈,无用,转瞬飞逝,
属于养眼之物,
它们就是它们所是的东西
一个个既小又圆的精确气体,
没有人,甚至这个吹气泡的小孩,
也不能妄称气泡比它们自身显示的更多。
在透明的空气中,有些气泡难以看到。
它们就像微风,几乎连花都吹不动
而我们只知道它在吹
因为有的事物在我们心里变得明亮
可以更透明地接受一切。
有些诗人是艺术家
他们制作诗歌
就像木匠使用木板!……
不知道如何开花多么悲哀!
必须把诗句放在诗句上,就像有人砌墙,
观看它是否好,如果不好就把它拆掉!……
唯一有艺术性的房子是整个地球
它富于变化,总是很好,而且总是同一个。
我考虑它,不像有的人思考,而像有的人不思考,
我观花而微笑……
我不知道它们是否理解我
或者我是否理解它们,
但我知道真理存在于它们和我之中
存在于我们共有的神性中
让我们在地球上行走和生活
偎依着穿过满意的季节
让风歌唱着催我们入眠
并且在睡眠中不会做梦。
明月高悬夜空,眼下是春天。
我想起了你,内心是完整的。
一股轻风穿过空旷的田野向我吹拂。
我想起了你,轻唤你的名字。我不是我了:我很幸福。
明天你会来和我一起去田野里采花
我会和你一起穿过田野,看你采花。
我已经看到你明天和我一起在田野里采花,
但是,当你明天来到并真的和我一起采花时,
对我来说,那将是真实的快乐,也是全新的事情。
恋爱中的牧羊人丢失了他的牧羊棍,
他的羊群在山坡上走散,
因为想得太多,他甚至没有吹奏随身携带的长笛。
没有人来到他身边,或从他身边离去。他再也找不到他的牧羊棍。
别人咒骂他,为他牧羊。
最终却无人爱他。
当他从山坡和假相上站起来,他看到了一切:
巨大的山谷照常充满同样的绿色,
远处的高山比任何感觉更真实,
所有现实,连同天空、空气和牧场,都存在着,
久违的空气再次清凉地进入他的肺叶
感觉空气正在他胸中重新打开悲伤的自由。
我生活的最终(我不知道什么是“终”)价值是什么?
一个伙计说:“我挣了300000元。”
另一个伙计说:“我享受了3000天的荣誉。”
还有个伙计说:“我良心好,这就够了……”
如果他们来问我做了什么,
我会说:“我观看事物,仅此而已。
因此我将宇宙随身携带在口袋里。”
如果上帝问我:“你从事物中看见了什么?”
我会回答:“只是事物本身。你不能把任何别的东西置于事物中。”
因为上帝持同样的观点,他会使我成为一种新的圣人。
一想到事物,我就背叛了它。
当它在我前面时,我才应该想到它,
不是思想,而是观看,
不是用思想,而是用眼睛。
可见的事物存在于被观看中,
为眼睛而存在的事物不必为思想而存在;
我整个儿沉浸其中是想而不看的时候。
我观看,事物存在。
我思想,只有我存在。
本文诗歌部分选自《我将宇宙随身携带:佩索阿诗集》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