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借助畅销书籍深入人心,只是其主调还是温情和美德,并没有直接播散火种,但它召唤出了改变不堪现状的思想。

编者按:书籍与革命有何关系?这是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长达半个多世纪孜孜不倦寻求解答的问题。在《启蒙运动的生意》《法国大革命的畅销禁书》之后,他的关注点扩散到了大革命前几十年的整体书籍世界。借着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记录和信札整理出的流通书籍清单和畅销书单,达恩顿对“书籍与革命”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启蒙思想借助畅销书籍深入人心,只是其主调还是温情和美德,并没有直接播散火种,但它召唤出了改变不堪现状的思想。书商们实际是间接为革命铺垫了道路。
文 | 刘永华(《读书》2021年7期新刊)
二十世纪初,法国史学家莫尔内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其成果后来以《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为名于一九三三年出版。莫氏研究了十八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清点时人阅读的图书。在这些目录中,他发现启蒙哲人的书籍颇为罕见。卢梭《社会契约论》这本大革命的“圣经”仅出现过一册。因此,他认为,大革命不是“卢梭的错”,也不是“伏尔泰的错”。

莫尔内的资料和看法,后来证明存在漏洞。比如他的调查结束于一七八〇年,那年卢梭著作的首批版本才刚刚问世。他忽视了《社会契约论》的通俗本,而这在大革命前是确定无疑的畅销书。再说,拍卖藏书无法体现阅读的全貌。尽管如此,莫尔内追问的问题却具有典范价值。书籍是否引发革命?这个问题不仅对思考大革命有意义,也是其他重要革命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甚至也是重大社会文化转型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妨称之为“莫尔内命题”。六十年代中叶以来的一系列研究,尤其是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和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的论著,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开展的。夏蒂埃的一本著作拈出“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一语作为书名,可以说是向莫尔内致敬。而达恩顿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埋首瑞士纳沙泰尔市档案馆,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进行了经年累月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它们不仅深入论述了十八世纪书籍的出版、销售等情况,也诠释了书籍与大革命的关系。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纳沙泰尔是一个遥远的陌生城市,但在欧洲书籍史研究上,却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地方。法国大革命前数十年,受法国特殊书报专卖制度和审查制度的影响,在法国边境以外,从事盗版书和禁书生意的出版社纷纷创立。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鲁塞尔,越过莱茵河延伸到瑞士,再往南延伸至时为教皇属地的阿维尼翁,这几十家出版社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它们几乎出版了启蒙运动的所有著作和一七五〇至一七八九年间在法国流通的大多数其他类型的图书。在这些出版商当中,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完整保存至今,这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商业信札、账簿、货运记录、订货登记册、印刷厂工头的付款账本等。在其他出版社档案基本散佚的情况下,这些档案为了解大革命前几十年的书籍世界及其对十八世纪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证据。
达恩顿在档案基础上撰写的一系列论著,最为重要的是他自己所称的“三部曲”:第一部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〇〇)》,第二部是一九九六年印行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而二〇一八年问世、二〇二一年译为中文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以下称《图书世界》,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是最后一部。此外,他还撰写了《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九八二年)和新作《盗版与出版:启蒙时代的书业》(二〇二一年二月,中译本已列入出版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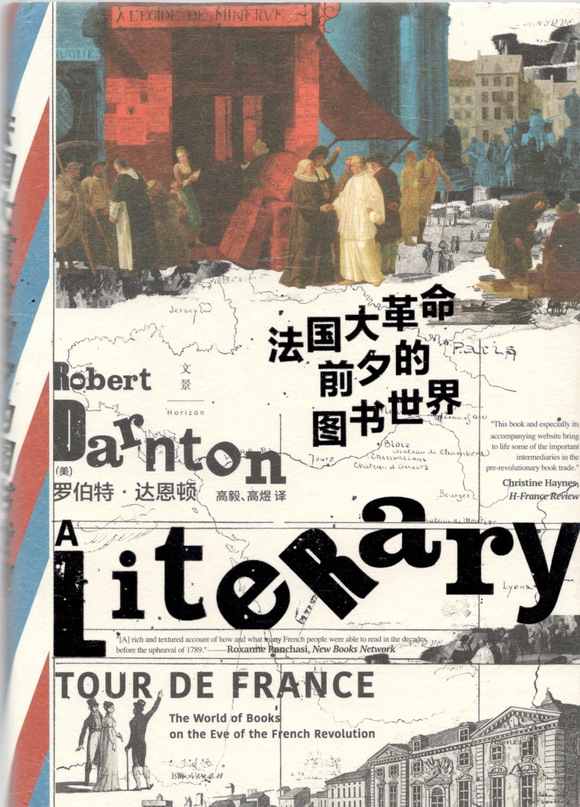
“三部曲”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书籍与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重要社会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的生意》讨论的是一部著作的出版史;《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的主题是各种禁书的扩散与影响;而《图书世界》则透过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大革命前夕外省流通的各种书籍及其销售状况。本文着重介绍三部曲的最后一本,看达恩顿如何由书籍贸易回应“莫尔内之问”。
《图书世界》一书,无论在史料利用、谋篇布局,还是核心问题的处理上,都有独具匠心之处。
纳沙泰尔档案保存了将近五万封信札,其中包含几千封来自每个与图书行业有联系的人写的信札,这些人包括作者、出版商、印刷商、纸商、铸字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车车夫、货栈主、旅行推销员、图书代理商、审稿人、读者,特别是法国几乎所有城镇的书商。本书系统利用了这些信札,从中选出二十二位销售商和偷运者,对他们的生平和售书生涯进行重点考察。这些书商来自法国各地,信息较为分散。为串联这些信息,也为从一个不同于书商信札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书业从业者及其所涉书籍贸易,本书系统利用了纳沙泰尔一位销售代表的笔记和信札。在十八世纪的欧洲,销售代表在书籍销售中有着特殊位置。每隔一两年,出版商就会挑选一名可靠的职员,派他出差了解跟书籍制作与销售有关的事务,如处理账目纠纷、寻求新的纸张来源,乃至了解和处理图书生意的其他所有重要方面。这些代表举足轻重,“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没有哪一家大出版商不靠销售代表就能做成生意”(23页)。
这位销售代表是二十九岁的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Jean-Fran. ois Favarger)。一七七八年七月五日,他骑马动身,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某日返回纳沙泰尔。达恩顿指出,等他走完这段长达一千九百多公里的旅程时,“他所了解的有关图书贸易的东西,比迄今为止任何历史学家可能希望了解的都多”(6页)。幸运的是,他留下了一本记载详尽的日志和大量内容翔实的信札及路上开销的账簿。他的法国之行留下的记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图书文化景观”(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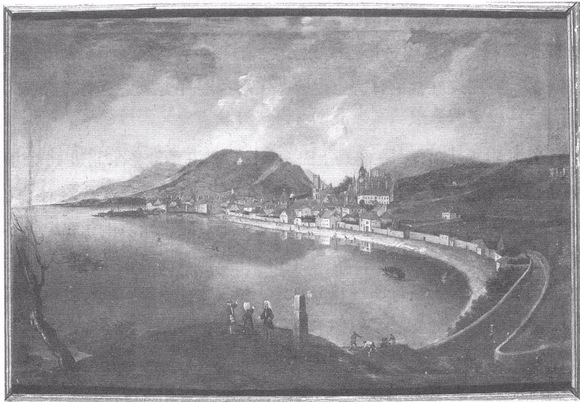
在长达五个月的旅程中,法瓦尔热“推销书籍,收账,安排货运,视察印刷厂,调查市场需求,评估生意规模,对一百多位书商的品质做出评价”(6页)。本书追随着法瓦尔热的足迹,不仅描述了沿途城市、市镇的图书贸易状况,而且结合这些贸易中心的主要特色,分别论述了图书流通与销售的不同面向:蓬塔利耶,偷运和越境;隆勒索涅,评估书店等级;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推销与收账;里昂,国内走私;阿维尼翁,交换贸易;南部、西南部各城,书店的生存困境;卢丹,沿街兜售与毛细管分销体系;中部地区,高端与低端市场;贝赞松,兴隆的书籍销售。如此,透过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作者有条不紊地论述了当时书籍流通与销售的几个重要面向:书市的不同层级、书商的不同等级和读者的不同层次。
根据本书的论述,不同城市在书籍流通中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比如,大革命前,里昂、阿维尼翁既是重要的书籍贸易中心,也是重要的出版中心,两地出版商都靠盗版书过日子。与此不同,卢瓦尔河谷的卢丹,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长期只有大约四千人居住,但在图书销售中,却起着联结瑞士出版商兼批发商和法国零售摊贩的枢纽作用。经由这个市镇,来自瑞士的盗版书有可能渗入图书市场体系的末梢,步入乡村集市乃至村落。因此,里昂和阿维尼翁与卢丹代表了书市的两极。
在以往的书籍史研究中,很少关注书商群体,但本书试图证明,这些为图书贸易四处奔波的从业者,“在十八世纪法国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故事属于最广义的书籍史”(397页)。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3页)。这一点作者做到了。法瓦尔热与途经城镇的各种书商打交道,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评估他们的等级,根据经济实力和诚信度,这些书商被评为“佳”“一般”和“差”三个等级。他看到,每个城镇都有一两家强势的书商和几家在破产边缘挣扎求生的书商。两者对书的需求颇有差别,前者较少或从不涉足禁书销售,他们善于密切追踪市场需求,规避风险;后者则相反,受生活所迫,他们甘冒风险。至于读者的层次,在本书处理的档案中只是时有所见。如卢丹的吉尔是一个售书摊贩,他的资产负债表表明,跟他打交道的读者包括乡绅、乡村牧师及领主、市长、法院推事、律师等。
作者论述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不只是为了描述书市、书商和读者的层级,复活书业从业者,其背后的核心意图,是更立体地呈现跟纳沙泰尔打交道的书商,进而说明,与这家出版商有过联系的书商,并不限于某一层次,而是包括了不同层次大大小小的书商。在讨论卢丹的流动商贩时,作者指出:“这些人留下的踪迹很少,但是在图书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就像血液里的红血球,把书籍传遍图书贸易的毛细管分销体系。”(275页)这就为排除读者对本书结论的质疑预先做出了说明。换句话说,法瓦尔热眼中看到的,并非法国图书市场的冰山一角,而是牵涉销售体系的不同层级。
在处理书籍的种类时,本书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如何跨越一家出版商的书单和整个法国流通书籍之间的巨大鸿沟?固然,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文献资料,在两个方面反映了市场对图书的需求:一是大革命前三十年间从法国所有城市寄来的附带订单的信札,二是记录有订单和发运货物的各种账簿。这些信息为了解当时书籍的销路提供了直接证据。不过,这些毕竟只是来自一家出版商的书单,如何能够体现法国图书贸易的全貌?
达恩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样显示了他的巧思。首先他指出,当时并不存在能够反映图书贸易全貌的档案,图书专卖登记制度将所有未提交给审查官要求正式批准的书籍都排除在外,而提交上去请求其他类别许可的书籍记录,并不指明实际印刷的是什么书,也不会提及印数和销量。而且,“在法国以外印刷而在王国内出售的书籍,其数量之庞大简直无法估计”。据达恩顿推测:“在一七六九到一七八九年间,它们至少占据着图书发行量的半壁江山。”(343页)那么,如何解决上述难题呢?达恩顿侧重从两个方面来推进这个问题的思考。

其一,书籍盗印透露出书籍销售的好坏。纳沙泰尔出版的书,很少是原版书,而是重印那些已经畅销的书籍。在挑选这些书籍时,出版商细心研究了市场行情,并根据每天从庞大的通信网络获得的信息来做出选择。它也听取零售书商对重印书籍的建议。从这种意义上说,纳沙泰尔的盗印书目,其实就相当于畅销书单。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图书交换机制放大了纳沙泰尔书目的“代表性”。达恩顿在清理出版社书目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出版社推销的书籍种类,远远超出了自身印刷机的产出。为什么?这就涉及以往法国书籍史学者从未注意过的图书交换机制。出版商以通常一千册的印数印刷一版书籍时,一般要拿出很大一部分,通常是一百册以上,跟一家或多家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交换他们存货中的各类书籍。阿维尼翁在书籍流通中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地是书商们交换书籍的一个重要地点。出版社从交换伙伴那里选择书籍时,只挑选那些它认为会畅销的书籍。
这个机制对于纳沙泰尔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小心谨慎地发展图书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既实现了其存货的价值最大化和品种丰富化,同时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347页)。一七七三年,这家出版商声称:“在法国上市的书籍中,没有什么重要书籍是我们不能提供的。”一七八五年,它的书目涵盖了七百种书,而到了一七八七年,它仓库中存储的书籍品种已达一千五百种之多。对于今日的研究者而言,这一机制带来的结果,亦即交换后形成的书单,恰恰有助于超越一家出版商提供的一管之见,降低了这家出版社印行书籍的权重,这样“统计基础就非常坚实了,足以支持一些一般性的结论”(348—3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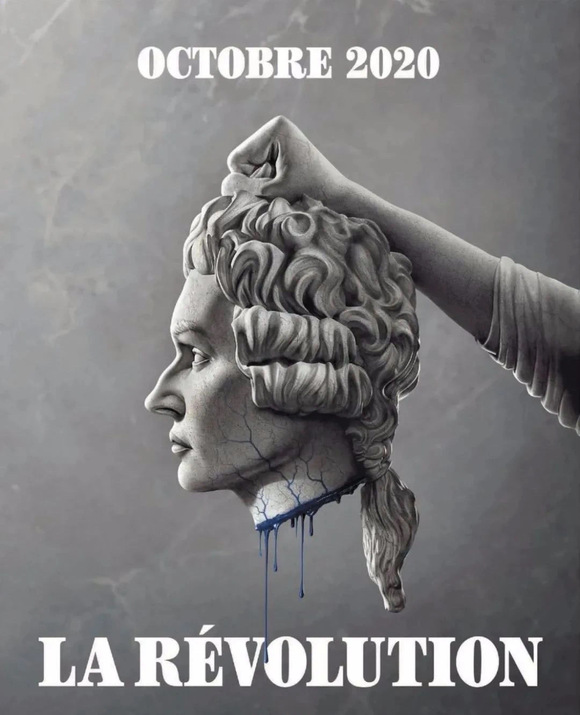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加选择地把出版社记录的每一项销售都计算起来进行汇总统计,达恩顿认为这种尝试是“注定有缺陷的”(355页)。为确定一位书商的订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说明他的生意,达恩顿首先对足量的订单进行汇总,同时阅读随订单一起寄来的信札。在仔细研究信札的基础上,重构销售的环境,限定其销售范围,确定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性质。通过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本书对书籍销售和需求做出了推论,其结果是一份大革命前夕法国流通书籍的清单。这份书单是由十八家法国书商在一七六九到一七八九年间订购的书籍,共涵盖了一千一百四十五种书籍。达恩顿提供了每种书的需求量,他指出这些数据虽不能从字面上解读,不过“它们代表着一些专业人员的评判,他们是以在十八世纪的社会条件感知图书需求并予以满足为业的专家”(360页)。对这些需求量进行整合后,就得出了一份“畅销书”书单。为防止统计的偏差,这份书单没有列入纳沙泰尔自身出版的书籍。最终的书单共包含了三十一种书。
这份畅销书单包含的范围很广,计有政治毁谤类、启蒙主义类、虚构类等十一类之多。毁谤性书籍是抨击路易十五及其情妇和大臣的书籍,此类书籍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对法国读者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启蒙哲人的书籍在畅销书单上表现突出,重要的有梅西耶的《二四四〇年》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跟莫尔内的看法相反,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也有很大的需求,各种无神论、反基督书籍也相当畅销。可以预想,一般虚构类作品也颇为畅销,其中比较畅销的有色情小说、言情小说以及当代作家的剧作。记述远途旅行的文学作品,对于十八世纪的读者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后来,游记类图书逐渐演变成历史、地理类图书,其中比较受欢迎的有帕拉、比兴的书和多产的普及读物作家米约的一系列著作等,不过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没有获得多少订单。法律和政治理论类书中,比较有销路的是德瓦特尔的《国际法,或自然法原则》、斯密《国富论》第四篇第七章的单行本等。此外,科学和医学类,各种辞典、参考书籍和自助手册,儿童类,政治和时事类,以及共济会和巫术类等几类图书,也有不错的销路。
对于本书运用的方法,夏蒂埃和其他强调阅读史的学者也许会提出质疑,这些书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读者的反应?一部没有研究阅读的著作,能回答书籍与大革命的关系吗?在读完本书后,我觉得达恩顿在书中提出的辩解还是有说服力的:他承认“这种书籍传播研究远不彻底,它忽略了被看作书籍传播方面最重要的内容: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反响”,但他同时指出,“我不怀疑研究这些内容的重要性”,“专心研究这些主题,就算无法回答两百多年前人们如何‘消费’图书这个关键问题,也有可能提出有关书籍传播的一些可靠结论”(3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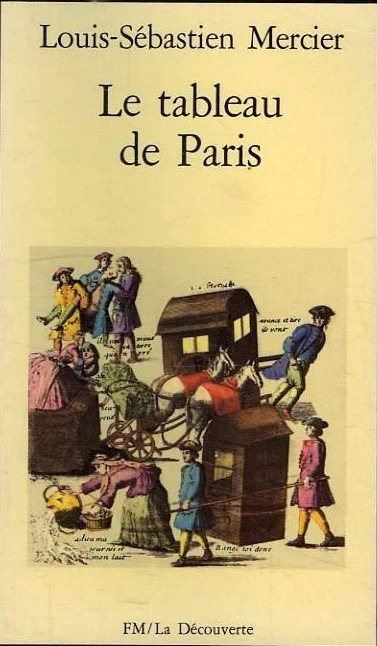
应该说,对于本书的书单和数据,达恩顿是颇为谨慎的。不过也应指出,出版社自身的判断和定位,还是有可能影响到书单的内容。纳沙泰尔会以自身印制的书籍,去交换廉价的特鲁瓦蓝皮本通俗读物吗?可能性不大。书中虽然讨论了以卢丹为中心的毛细管分销体系,但在本书描述的图书世界中,这只不过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此外,本书似乎关注的是大革命前三十年出版的新书,那么旧书呢?它们事实上也在被流通、阅读。也就是说,达恩顿的书单体现的可能更多是中上层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且难以反映旧书流通、阅读的情况。
这些书籍与革命有何关系?达恩顿指出:“关于书籍需求的统计表明,启蒙思想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旧制度时期的文化。”最能证明启蒙思想普及情况的著作,当属梅西耶的《二四四〇年》,这部顶级畅销书展现了一幅按卢梭式原则治理社会的美好图景,与梅西耶另一部揭露当时社会秩序残酷不平等的畅销书《巴黎图景》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启蒙著作并非借由直接抛撒火种来为革命铺路。正如达恩顿指出的,“书籍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其中的主调还是呼唤温情(sensiblerie)和美德。……最畅销的书籍传达的不是明确的政治信息,而是与既定秩序格格不入的一般观点”,“这些书籍尽管五花八门,却都传达了一种灌注着隐藏信息的世界观:眼前的世界不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另一种现实正在头脑中建构。随着书籍自一七六九年以来在商业渠道的传播,到一七八九年,思想即将变成行动”。经由这种迂回的方式,卢梭、伏尔泰与大革命有了潜在关联。从这种意义上说,“那些把满足读者对书籍的需求当作生意的图书贸易从业者们”,实际上“正在为一场革命铺垫道路”(398页)。而最终,他们赖以生存的书籍世界,也在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