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切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

杭州保姆纵火案当事人林生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6月30日深夜,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当事人林生斌在微博上宣布走出妻儿亡故的阴影,再婚生女。这条微博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近年来中文互联网内最大的舆情反转。一夜之间,林生斌就从网友眼中的“圣父”变成了众人唾弃的“渣男”,关于他的种种争议持续发酵。
2017年6月22日凌晨,保姆莫焕晶在杭州“蓝色钱江”公寓人为纵火,户主林生斌的妻子朱小贞和三个孩子不幸丧生。惨案发生后,林生斌的积极维权让社区消防设施与城市治理的漏洞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视——这可以说是这起震惊全国的恶性事件最积极的意义,也是林当初得到众多网友声援的最直接原因。然而,这四年来,随着林或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塑造了“悲情英雄”“深情丈夫”的形象,他用为思念亡故妻子开设的微博账号公开喜讯的行为被许多网友视作“人设崩塌”。
“人设崩塌”后,一切关于林的信息似乎都可以化作他负心寡情、居心叵测的证据——人性中的勇敢与怯懦、向往永恒与见异思迁、利他主义与机会主义本就犬牙交错,人们赫然发现一个多年来被认为是“完美”的公众人物其实也有道德瑕疵,为此产生愤怒情绪和逆反心理,并非难以让人理解。但始料未及的是,网友关注的焦点竟往阴谋论和迷信的方向奔去。“纵火案是林生斌故意为之”的论调在社交网络上比比皆是,坊间甚至还流传起了其为了镇压冤魂捐“锁魂井”、树“锁魂墓”的推测。信誓旦旦地传播阴谋论的网友,不仅把早已被辟谣的一些谣言又翻了出来,而且完全罔顾莫焕晶刑事判决书中的官方结论。

“大众是个怪物……它可能刚刚还在且歌且舞,转脸就能生气发怒,将一切全都砸毁。”法国大众研究心理学家迈赫迪·穆萨伊德(Mehdi Moussaïd)在《新乌合之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长久以来,大众的集体行动和时不时爆发的激情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目标,他们的研究或许能解释“林生斌人设崩塌”事件中的种种乱象:在互联网信息洪流时代,我们为何如此容易相信阴谋论?
剑桥大学“病毒式营销”研究者锡南·阿拉尔(Sinan Aral)和他的同事在一年时间里跟踪了300万网络用户传播的上千条信息,并在2018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得出结论,谣言的传播速度是真相的六倍。穆萨伊德援引了这则研究指出,与真实的新闻相比,假新闻传播得更远、更快,且触及的受众更广泛多元。事实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是假新闻和谣言的极佳温床。
这与社交媒体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指出,在社交媒体崛起之前,人们主要依靠公共媒介(报纸、杂志和广播)接触来源广泛的信息,与他人共享经验和信息披露。而今,公共媒介虽然仍在互联网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们的重要性已在不断下降。
与之相对的,是传播选项的激增和网络用户定制信息能力的增强——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线上新闻媒体,都以更好地服务用户个人兴趣为宗旨来设计和引导用户体验。桑斯坦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产品设计逻辑是最大化地利用人类的趋同性(homophily)——即想要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联系和纽带的强烈倾向——通过某种控制架构(architecture of control)将趣味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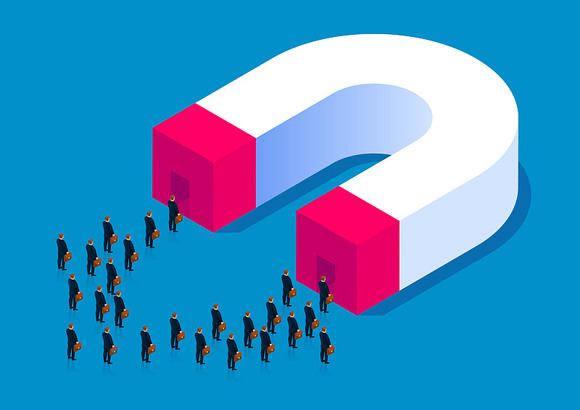
桑斯坦警告我们,迎合趋同性的产品设计逻辑导致了网络公共领域的一个残酷事实:“虚假的消息传播迅速,只要人们在阅读想法类似的人所写的东西或者与其交谈,群体极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群体极化(polarization),指的是经过协商之后,人们极有可能朝着群体成员最初倾向的方向发展出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对社交媒体用户而言,一种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想法相似的人在彼此讨论后得出一种印证此前想法的、更为极端的结论,在具有鲜明身份认同的群体中尤为如此。
大量研究表明,三个原因导致了群体极化。第一,群体极化的核心要素是存在一个有限论据池(limited argument pool),如果群体成员已经有了特定的倾向,他们会朝着同一方向开展大量讨论,而对相反的观点讨论极少,这意味着,一个群体的主流倾向往往会扭曲在其中传播的信息。第二,人们会出于声誉考虑,向优势立场所在的方向调整自己的立场,而持少数派立场的人往往会保持沉默,随着时间推移,后者的立场会在公共领域消失。第三,想法相似的人在讨论时会帮助彼此获得自信,他们因此更加相信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因而也更加极端。
正如“林生斌人设崩塌”事件所反映的,网络用户的观点有时会出现急剧转折,桑斯坦称之为信息“引爆点”现象:在得到新信息后,人们在选择相信、做出新的判断或行动时往往存在不同的“阈值”。随着“低阈值”的人倒向一个阵营,一个赞同新判断的重要群体会逐渐形成,当该群体达到一个临界数量时,会在更大范围内促成大群体、社会甚至国家的“引爆”。这一过程就会产生社会流瀑效应(social cascades),即在信息驱动下,社会群体向着某种信仰或行动的方向快速且急剧地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流瀑效应中存在的从众心理和信息扭曲。桑斯坦强调,群体中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人做了独立的决定,其他人则是在从众,因此某个群体释放的信号即使强烈,其实也只体现小部分人的判断。锡南·阿拉尔团队的另外一个实验证实了社交媒体中从众心理的存在。研究者随机抽取了10万条新闻,每篇文章刚发出来,研究者就先去打第一个分数。结果显示,如果首条评价是肯定的,这条新闻的总平均分会提高25%,无论随后跟进了多少真实的网民评价。这种滚雪球效应同时意味着,信息总是会被传播群体中的主流重新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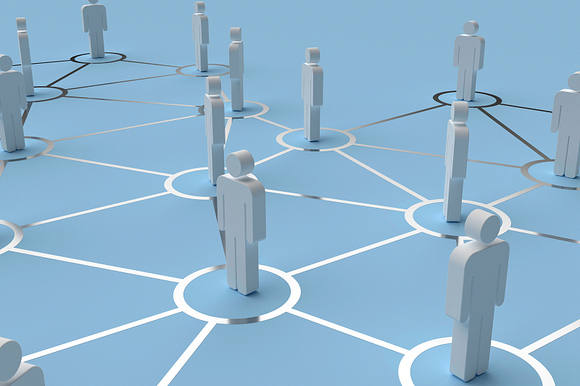
桑斯坦指出,互联网在大大增加信息和观点多样性的同时,也加剧了出现相互背离的流瀑的可能性——在一个四分五裂的言论市场里,局部流瀑会将人们引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即使只是“转发”这一个动作,就会将社交媒体用户分成不同的同质社群。针对推特和脸书的研究都发现,用户倾向于转发自己认同的内容,于是人们在转发内容时创造了自己的回音室,在分享自己认可的信息的同时忽略自己反对的信息。这一切的结果是,在想法相似的社群内,“哪怕毫无根据,阴谋论也会在这些社群中迅速传播。”
阴谋论的盛行背后是“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这一人性弱点使然。当你做出一个决定后,不管你的信息多么有限,你都倾向于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该决定,并忽略或不接受反面证据。在《专家之死》一书中,作者托马斯·M.尼克尔斯(Thomas M. Nichols)指出,民间传说、迷信和阴谋论都是证实性偏见的典型例子,其中阴谋论是最极端的情况:
“阴谋论令人沮丧恰恰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每一个反驳都只会触发一个更复杂的理论。阴谋论者操纵一切存在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解释,但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没有证据当作更有力的佐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切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
在桑斯坦看来,证实性偏见最强大的驱动力是由利益群体、回音室和身份观相互促进创造的铁三角:“利益群体利用社交媒体支持他们喜欢的世界观,同时也产生或强化了身份观。回音室在增强那些群体权威的同时,也使得那些观念根深蒂固。”在围绕林生斌再婚生子产生的种种讨论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蹭流量的自媒体发布各种标题耸动的内容并被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秉持特定价值观的群体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批判林,并在回应室效应下拒绝接受哪怕是更温和一点的观点。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指出,人的思维装置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直觉,直觉是大脑思考的第一系统,它帮助我们进行快速判断,但往往也会让我们陷入过度自信、极端推测和预估偏差中;自觉的思考是第二系统,它是第一系统的补充和修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运行的是第一系统,只有当我们发现问题和异常时才会启动第二系统。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支持上述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指出,道德上的直觉总是自动自发地产生,而完整的推理却很难发挥作用,而且往往来自那些最初的直觉。“道德直觉”带来的影响是,它们会将有相同道德信仰的人联结起来,但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人们组合成各个政治群体,分享着各自的道德信仰。不过,一旦他们形成了某一特定的道德信仰,就会对其他的道德信仰视而不见。”这意味着,道德层面的讨论几乎总是很难形成共识,因为它们“大多是事后空无一物的编造,只为了迎合一个或多个直觉目标”。

对人性有深刻洞察的文学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T.S.艾略特所说,“当我们不知道,或者当我们知道得还不够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以情感来代替思考。”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注定无法保持理性、独立思考?
美国贝勒大学荣誉学院人文学科杰出教授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认为,我们需要承认完全脱离他人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每个人的所思所想都不可避免地是对他人想法和言行的回应——偏见也是我们减轻认知负荷的客观需求,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坚定自觉思考的意志,而非逃避思考。我们或许难以控制思维的第一系统(直觉),但我们可以改变和训练它,培养新的思维习惯,学习辨别真正的偏见和让我们产生误解的错误想法。
在这之中,趋同性或许是我们需要学会正视和克制的最大诱惑。从众心理是如此普遍,寻求他人的认同近乎于我们的本能,在一个有意或蓄意杜绝异端的社会里,从众的压力往往也是最大的。这意味着,独立思考的重要前提是能够辨别社会压力,抵制“寻求认同的本能”。
诚然,在群情激奋之中,我们是很难保持理性的。徐贲指出,当人们急切地需要应对某件事情、某种状况、某个问题时,一旦得到某种解释,往往会不去分辨它究竟是否合理,这给歪理带来了可乘之机——
“歪理不仅能利用人们求放心,求安全,‘反正无害’的心理,还能利用人们对‘出气’、‘解恨’、‘痛快’的需要。如果能满足这类心理需要,哪怕一个人显而易见是在谩骂和破口大骂,哪怕他根本不是讲理,要解恨或痛快的听者也还是会觉得有道理。”
我们因此也需要从社会维度去思考“林生斌人设崩塌”事件为何能够激起那么多人的强烈反应,并让其中许多人对阴谋论深信不疑。尼克尔斯认为,当个人陷入悲伤和困顿的时候,即便没有原因,也会想尽办法找到原因——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社会紧张严重的时期往往会加强稀奇古怪的阴谋论和破绽百出的推理的吸引力。在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阴谋论对象大多是战争的后果与高速工业化的出现,而今则是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紊乱。

林生斌引起的种种争议最终走向这般迷信和阴谋论的境地,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发生在清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巫术大恐慌。当时,一股名为“叫魂”的妖风令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在官府发起对妖术的清缴时,普通人开始自发指控他人暗中使用妖术。汉学家孔飞力认为,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出的其实是时人的无权无势状态,以“叫魂”罪名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突然获得的一种权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而它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从叫魂案发生的1768年至今,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封建帝制脱胎换骨为一个拥抱科学、理性、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现代国家,这同时也是一段长远的精神历程。在21世纪的今天,“镇魂”一说的大流行或许也在提醒我们,某种社会运作的逻辑恐怕具有着超越时代的恒久影响力。
参考资料:
【法】迈赫迪·穆萨伊德.《新乌合之众》.中信出版集团.2021.
【美】凯斯·桑斯坦.《标签: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
【美】艾伦·雅各布斯.《喧哗的大多数:如何在互联网信息洪流时代保持清醒》.中信出版集团.2020.
【美】托马斯·M.尼克尔斯.《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中信出版集团.2019.
【美】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2014.
【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中信出版社.201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