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精神饥荒是一条出路,将个人烦闷纳入各种主义中,汇成社会总体性的问题,是另外一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前后的青年人也面对许多苦恼。在近期出版的《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一书中,梁启超试图回应青年人普遍关心的三个问题——在外界诱惑和压迫无法忽视的时刻,如何保持个人的人格?在人生遭遇忧患痛苦之时,如何才能获取精神的安慰?在学问和事业遭遇挫折时,如何才能继续向前?
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王汎森在研究近现代思想史的著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提出,人们往往强调新文化运动之后守旧派的苦闷,事实上,当时的新青年也同样感到烦闷和茫然。1920、1930年代青年的文字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苦闷”,刊物中常常出现的就是“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这一类字眼。陈独秀的《自杀论——思想界与青年自杀》回应的是由于困惑而出现的青年自杀事件,钱穆也有文章分析一个学生的自杀,讲“怎样生活”成为了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原因同样在于过去旧的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体系的建立还遥遥无期,当时家庭的父老兄弟已经失去了指导子弟的权威和自信,青年不能从生活环境中获得“生活上的习惯和信仰的可靠基础”。
面对新旧之交的青年的苦闷,当时的知识人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对于当下的我们又有哪些启发?
梁启超认为,青年人的困惑是当时满足于贩卖智识的学校无法回答的。 仅仅追求知识而忽略精神,这正是全世界青年困苦尤其是中国青年困苦的原因,因为他们面对的政治社会尤为不安定,环顾四周更无精神可寄托。这一点反思在更早的《欧游心影录》中已有体现。1919年梁启超抵达伦敦游历欧洲,目睹欧洲一战情形,反思欧洲思潮,特别提出反对“科学万能论”:“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在新旧交替之时,宗教与旧哲学被科学全然打败,人的价值和信仰岌岌可危。所谓人类心灵也不过是物质运动现象的一种,梁启超说,旧信仰荡然无存,新权威却未能完全树立,这便是“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正因此危机,全社会才陷入“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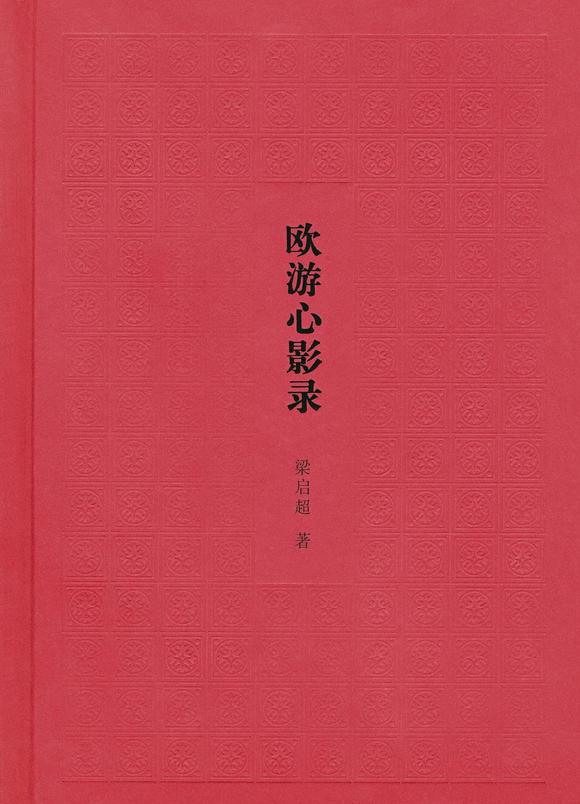
至于这一危机的影响深远,在他看来,信仰必然法则的机械的人生观最终将导致“强权主义”“乐利主义”横行,人们相信,“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好像千千万万的人来到世界,都只是为了抢面包吃。
在教育方面,梁启超将教育分为知育、情育、意育,分别对应着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知育教导人们学识和智慧,仁育指导学生不计较成败得失,意育指的则是意志锻炼和自制能力。在他看来,现代学校贩卖的不过是知、情、意中的“知”,而这“知”仅有常识和学识,缺少总体的智慧,简直是“智识杂货铺”。向来人们只重视智识饥荒,却无视精神饥荒,却不知“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
青年自身如何要应对这样的精神危机?梁启超的劝告虽然是原则性的,亦有着可实践感。他从《论语》与《老子》化出“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和在事上磨炼的做法。梁启超反复提出的是,中国传统学说可以用来弥补或是克服西方机械、唯物的科学说法,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孔、老、墨三家虽然学说各不相同,但在理想与实际一致方面是共通的,讲大的自我和小的自我、灵的自我与物的自我的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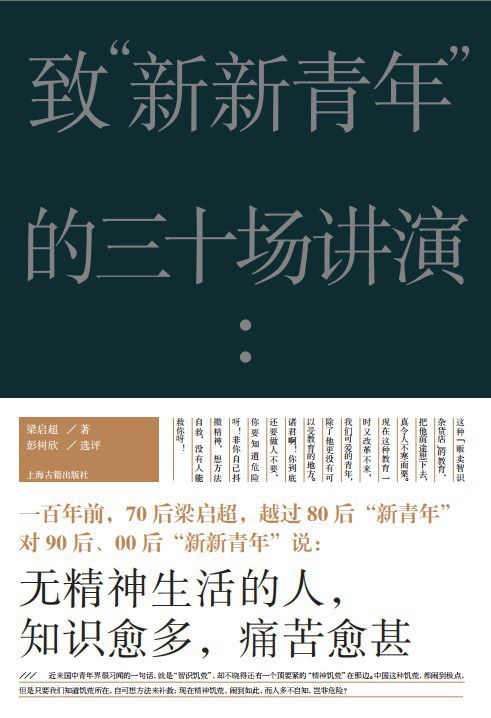
“知不可而为”语出《论语·宪问篇》,指的是做事情即使知道不能得到预料的后果,甚至没有结果,应该做的还是应当去做。成败得失的算盘不必打得太精密,一来因为世间的成败都是相对的,二来趋利避害的人总要面对无限的犹疑和惊恐。梁启超引用孔子所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倡导做事应当为了喜欢和乐趣,而并非因为外部鞭策,正因为有此态度,事事才能变得“不亦乐乎”,减去许多惑、忧和惧,将精神安定住。“为而不有”讲的是不以占有为目的,不为了金钱、名誉等目的去作为,这是梁启超对老子思想的概括。在“为而不有”的过程中,实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就是,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要给予人,自己却更多。“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本质上都是将无聊的关于人生利弊的计较一扫而空。
梁启超重视创造与劳作的乐趣,总将趣味放在第一,反对毫无趣味的倦怠劳作。在1903年游历过北美大陆之后,他比较了海外华人之于西方人之不足,最终举出四点。前三点分别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最后一点最为根本,在于无高尚目的。所谓“高尚目的”是对空间上的衣食住之外的更大目的,是在时间上的现在安富尊荣之外的更大目的,有了这个高尚目的,人们才能继续进步,否则就会为仅仅是自身的利益、当下的得失纠结停滞,“故其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

梁启超特别注意到,20世纪初北美华人工作时间通常较长,终日劳作,较少趣味,而财富上也并不富裕。他认为,这是因为重复倦怠的劳作是人生堕落的原因: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 (《新大陆游记》)
厌倦是人生堕落的初始,这一思想在梁启超对青年人的演讲中有直接的体现,因为人生总是要劳作来维持生命的,如果厌倦劳作,那等于活活将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梁启超也承认,对现在环境的不满乃至厌倦是人类常有的心理,厌倦而不能逃脱往往是苦恼的根源,然而,肉体上既已被环境捆死,那么就要宣告精神上的独立,如文学上想象的桃花源、哲学家的乌托邦,都是超越现实世界的自由天地。还有,对于厌倦根本的救治办法是从劳作中看出快乐,“看得像雪一般亮,信得像铁一般坚”,从自己的劳作中得到快乐,形成一个别人抢不走夺不去的“自己的园地”。
梁启超为青年的困惑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不管是知不可而为、为而不有,还是趣味主义,都主要建立在对西方流行的“科学万能论”的反思之上以及对传统资源的再运用,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成为了他演讲的重要纲领之一。如果将视野扩大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我们不难发现,提出方案的不止梁启超一人。
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一章,王汎森从新文化运动之后青年界常见的烦闷和虚无入手,发现了各种“主义”对青年精神领域的作用。王汎森写道,晚清以来,中国读书人的世界逐渐出现两个轨迹,一个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是群体国家的,这两个轨迹有时有交会之处,“主义”恰好提供了将两个轨迹合为一体的机会。有意思的是,所谓“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剧本,也变成了文化剧本,为青年生活的困惑和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将从个人到国家到全人类的命运,形成贯通而又排他的义理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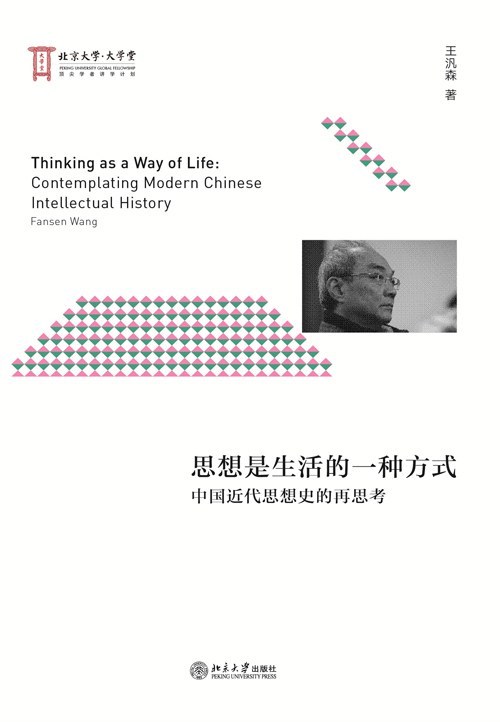
如王汎森所说,青年最常见的苦闷之一就是爱情,新文化运动将青年从旧家庭与婚姻中解放,解放之后又生出许多问题,婚姻与家庭的问题困扰着许多人,“主义”的倡导者将恋爱与经济结合、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结合,指出了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的方法。当时的进步杂志《中国青年》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一篇名为《恋爱问题》的文章提到青年渴望爱的洗礼,但“要找到真正的恋爱,还得要大家先去改造社会经济,干社会革命的工作”。
在爱情以外,青年另一常见苦闷就是升学与出路,王汎森举例《中国青年》还有一封信件询问应当如何面对付不起学费要退学的境地,回信颇具代表性。回信认为,许多青年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只看见个人和家庭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劝青年先找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苟延残喘”,在期间尽力赞助革命运动,因为只有改造了国家,才能使得事业安定而报酬丰厚。
王汎森提出,“主义”时代常见的便是将个人的烦闷挫折转喻为国家的命运,就像郁达夫小说《沉沦》所写,受到日本艺伎冷淡的中国留学生感叹自己情感的不幸是由国家的衰弱导致的。主义之所以吸引人,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还在于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联结,将已经打乱的了、无所适从的苦闷与烦恼的人生与日常生活转化为有意义的集体活动,就像《中国青年》中的问答展现的个人困惑、生活遭遇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最终引向了共同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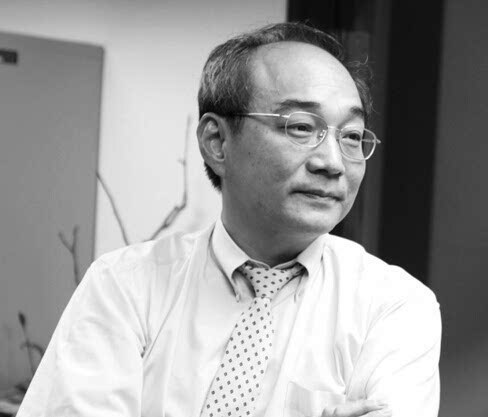
正如上文所说,梁启超在游览欧洲后已经发现了“科学万能论”的不足,发现一般人渴望的价值、意义和方向会因为不够科学而被放弃。王汎森说,《欧游心影录》后来引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凸显出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世界与科学世界是否是分开的。科学派宣称,世界是一元的,没有主观的价值世界,一切都可以纳入大自然的规律中;玄学派则认为科学和人生、价值与事实、精神与物质不能混为一谈,人生观的问题是主观的,不能用科学规律来解决。之后逐渐地出现了声称可以结合科学与价值的论述——陈独秀提出社会科学,同时结合科学与价值、客观与主观、自由与必然,既是科学的,又是人生的,因此可以作为人生问题的指导。王汎森写道,这也引起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由文学、哲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向,青年人纷纷由渴望研究文学哲学转向社会科学,期待用社会科学解决各种问题,社会科学此时成为了思想界的宠儿与权威,它超过了学术,是与人生道路、政治社会、国家命运乃至整个世界都相扣的新科学。1920年代的左翼刊物宣扬社会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改造社会事业,还可以解决“动荡不宁的病症”。
针对“动荡不宁”对症下药是重要的,王汎森写道,在这个阶段,价值体系需要通行需要有两个原则:一,必须与现实的政治救赎密切相关;二,必须提供一种确定性,不能再继续“问题化”,这样对不确定的年代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青年的苦闷最终被引向社会整体问题,就像那时的人们认为的,青年的苦闷是由缺陷的社会所给予的,要找到“中心思想”和“中心行动”才能解决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