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理想的母乳喂养决策是母亲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权衡做出符合自己利益和孩子需求的选择。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林子人
“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是最佳的婴儿喂养方式。6个月后在婴儿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建议持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更长时间”,这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母乳喂养的行动指南,它已经得到很多国家政府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世界卫生大会在2012年提出,到2025年,全球0至6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要达到50%。中国2017年制定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也提出了同样的目标,并将完成这一目标的年份提前至2020年。
实际上,从90年代起,中国就已加入国际母乳喂养倡导运动的浪潮中。通过官方、非官方机构以及医疗部门的宣传推广及制度安排,借由各种科学数据和论证的加持,母乳喂养已经被建构成一种最优的婴幼儿喂养方式,形成了“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这一伦理的核心是保障婴幼儿的健康与福祉。
然而,母乳喂养不仅与婴幼儿的健康有关,哺乳作为一种行为实践更关乎母职和女性体验,母亲作为生育主体的经验应该受到足够的关注。从近代到现代,中国女性的哺育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压力?母乳喂养作为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性的母职实践,作为母亲的女性在这其中又有多少自由?
在自然界,母亲亲自哺育幼儿是普遍规律,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以雌性哺乳动物最独特的器官——乳房——作为分类标准。在其1758年出版的著作《自然系统》中,林奈以“哺乳动物”这一分类名词取代“胎生动物”,首次把人类归入哺乳纲。但在人类社会,哺乳行为作为女性生物性和社会性母职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
牛乳与奶粉是现代社会婴幼儿常见的食物,但牛乳哺育进入近代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同时,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各种话语共同争夺和建构何种哺育方式是最好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讲师卢淑樱在《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中探究了牛乳哺育在近代兴起的原因,以及哺育方式的转变对母亲角色的影响。
母乳哺育虽然是最基本的婴儿哺育方法,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未强调母亲非授乳不可,乳母代劳是普遍的现象。即使母亲没有足够的乳汁哺育婴儿,也没有能力聘请乳母代劳,亦有谷物浆作为代乳品。直到19世纪末亡国灭种危机下,部分士大夫把国家积弱的责任归咎于妇女——如要拯救中国,首在改造妇女,于是女性的身体、行为和思想成为被规训的对象。
此时,日本家政学传入中国,其中育儿被认为是妇女的首要义务,授乳更被形容为妇女的天职。家政学者认为,“不自乳者,母子亲爱之情,必不能厚”,妇女亲自授乳可以增进感情。家政学也参考了近代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来印证母乳哺育的好处。母乳哺育顿成良母的标准、强国强种的方法。进入民国后,妇女身体国家化的过程不断加剧。为遏止妇女束胸的歪风,地方以至中央政府立例查禁女学生束缚双乳。
19世纪以来,随着洋商来华日增,乳牛、牛乳产品以及相关的饮食文化、知识和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不过在母乳哺育当道的20世纪初,民众以强国保种的思维衡量批评牛乳的功效,认为牛乳只是不得已之选。但1910年代末西方营养学界却兴起一种以进食牛乳多寡衡量国家强弱的学说,奶粉商的商业广告以“科学和文明”的话语推销牛乳,强调这种重视营养和卫生的科学化育儿法有强国强种实效,并暗示可以给予母亲更大的自由和活动空间以招揽新式的“现代母亲”。强有力的营销话语终于让奶粉打入中国市场,牛乳哺育得以在中国萌芽滋长。

可以说,牛乳喂养和母乳喂养在近代中国变革的背景下出现,共同借用国族和科学的话语强调其有益之处。然而,在母亲哺育的活动中,母亲拥有多少自主权呢?卢淑樱研究了民国时期母亲的哺育选择和母职实践的个案,发现随着当时社会风气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女性开始踏足职场,面对母职和职业的抉择,女性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挣扎。
一些在职女性不愿因生儿育女断送事业,而选择使用牛乳代替,但罪己的愧疚心却屡次出现在民国时期在职女性的育婴日记中。即使少数享有哺育自主权的母亲也并不一定由衷地认同自己的抉择,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使女性不自觉地认同和默默承受着哺育婴儿的重担。卢淑樱认为,尽管婴儿哺育涉及母亲的身体和个人感受,但在父权当道的20世纪前期,母亲哺育自主的机会可谓是微乎其微。
西方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商业化奶粉急剧改变了人类哺育下一代的方式,许多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母乳喂养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奶粉采用量不断攀升的情况。随着对儿童福利的关注提升,以及营养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研究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国际上出现了倡导母乳的运动,重新逆转社会风潮,人们开始探讨女性的哺乳权利和婴儿获得母乳喂养的权利。
现代营养学认为母乳基本上涵盖了婴儿出生期间需要的所有营养素,而且还含有一些免疫相关的物质,帮助对抗微生物感染的同时,也防止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给机体带来伤害。也就是说,母乳不仅能提供生命早期的营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免疫稳态的保护作用,这是任何配方奶粉都无法取代的。
心理学也支持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心理健康和情感发展有深远影响。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认为,如果母亲能够做到令孩子满意的哺乳,同时又跟婴儿融为一体,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直到她跟婴儿都觉得彼此是完整的个体为止,那么婴儿的情感发展就已经朝健康的方向走了好长一段路,并成为婴儿日后在世上独立生存的基础。
在母乳喂养的议题上,科学主义的塑造举足轻重,事实上,这一塑造从近代就已经开始了,而现代越来越多的学科越来越精细地参与到研究母乳喂养的好处中。营养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科学成果共同建构出“母乳无可替代”的科学话语,将母乳喂养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里马·阿普尔(Rima Apple)认为,科学、医学在现代陆续介入了妇女的育儿工作,取代女性亲属作为育儿知识的权威之余,更标志着科学化母性(scientific motherhood)的确立。

1981年世界卫生大会发布的《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旨在通过严格规范母乳代用品的销售,降低母乳代用品销售对母乳喂养的干扰。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提出《伊诺森蒂宣言》(Innocenti Declaration),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支持、保护、促进婴儿享受母乳喂养,并就此启动了一系列倡议。由此,母乳喂养成为全球化战略,母乳喂养率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宣扬奶粉、奶瓶的人工喂养理念则被各国纷纷限制、审查与反思。
中国从90年代以来就与国际接轨。1990年,每年的5月20日被定为“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1991年中国成为《伊诺森蒂宣言》执行国,199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将母乳喂养理念纳入了公共政策,“促进母乳喂养的10项措施落实”以及“积极创建爱婴医院”也被写入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规划。相关研究指出,“母乳喂养”被视为关乎人口健康与国民素质的重要措施,融入国家整体健康和发展政策之中,是应对“母乳喂养”全球化战略的措施。于是,“母乳喂养”不再是一个私人的喂养方式选择,而成为了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这仍然部分延续着近代国族主义的话语,同时也是中国在女性身体上追赶现代化的努力——母亲角色与现代性问题始终纠缠在一起。
“母乳最优”背后还暗含着另一层含义:母乳喂养等于好妈妈。由于母乳只有母亲可以提供,母乳喂养的职责也理应由母亲来承担。新晋妈妈在家休产假时,一切外在价值感来源被切断,只剩下孩子这唯一的标准,而能否产出足够且优质的母乳,似乎能够评判新生母亲是否是“好妈妈”。
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杜鹃在研究“母乳最优”哺育伦理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妈妈,感受到她们在这一伦理之下的痛苦、挣扎和无奈。她的一位受访者因为得了乳腺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萌生了断奶的想法,却被她的婆婆指责“有奶不喂就不配当妈”。
由于母亲所摄入的食物成分可能经由母体吸收进入乳汁,从而对婴儿的身体产生影响,许多母亲选择忌口,而如果母乳喂养的婴儿出了什么健康问题,首先就可能怪罪于母亲的奶水出了问题。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写下她做母亲的体验。当她的女儿患上肠绞痛时,她的保健员怀疑是她的奶水有问题,她被建议回想过去24小时内自己吃过什么、喝过什么。“我想象着自己开始腐烂,蔓延到她的地盘,直至她的血管和身体隐秘处。我希望我的毒刺从她无辜的体内取出。”直到她的保健员终于离开,她抱着宝宝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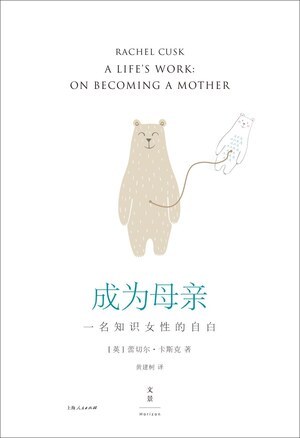
杜鹃认为,“母乳最优”的哺育理念已然成为一种对女性哺育行为的道德期许甚至是规范,如果母亲不能提供给孩子这种最优食物,那么她的母爱将是不完整的,进而她的母亲身份也是不合格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母爱10平方”运动的海报上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来证明非母乳喂养的问题:“和纯母乳喂养的宝宝相比,非纯母乳喂养的宝宝死于肺炎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5倍,死于腹泻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1倍;入院几率是前者的5倍;患有严重营养不良的几率超出前者10%”;“母乳是无菌的,100% 安全。婴幼儿配方奶粉可能受到下列危险物质污染:三聚氰胺,各种细菌微生物,霉变,金属及玻璃颗粒,双酚A,聚乙烯咔唑,镉和其他重金属”等。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问题奶粉事件始终刺激着母亲们敏感的神经,而权威机构借助科学主义的话语推波助澜,强化了奶粉的风险,以证实母乳喂养的不可替代性。母乳喂养重新成为了最安全的选择,这进一步迫使母亲们践行纯母乳喂养来保证婴幼儿的健康。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天然渴望成为母亲,她们照顾婴儿的能力会自动出现并且享受照顾婴儿的过程;同样,社会也普遍接受“哺乳是天性”的说法,哺乳被视为新生儿母亲的本能,但这实际上是对母职的浪漫化想象。哺乳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孩子含住乳头,而是包含一系列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如何保持恰当的哺乳姿势、如何让孩子正确地衔乳、如何避免孩子呛奶、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吃饱了、如何给孩子拍嗝等。但很少有女性在生产前得到足够的母乳喂养知识和实践技巧,当下母乳喂养宣传过多提到母乳喂养的好处,却没有告诉妈妈们母乳喂养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对问题的方法。在哺乳天性说和“母乳最优”的理念之下,一些不能顺利哺乳的母亲不愿意或无法向他人求助,承受着巨大的焦虑和压力。
在母亲们的身体经验中,哺乳可能并不必然是一件愉悦和亲密的亲子活动。社会对哺乳期女性的母职要求造成了一种“以哺乳为中心”的身体,许多母亲形容自己变成了“行走的奶瓶”,也有母亲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困住,不得自由”。女性在哺乳期还会经历涨奶、堵奶、乳头皲裂、乳腺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新生婴儿每隔两三小时就需要喂养一次,这让大部分母亲都会经历严重的睡眠不足。但这些负面经验从未在“母乳最优”的论述中出现。
鉴于传统的“母亲应该为孩子牺牲”、“为母则刚”的观念,以及乳房被赋予的性的意味,这些女性哺乳时的身体经验都无法得到重视和公开讨论,女性被迫默默忍受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周培勤说:“在’母职迷思’的社会规范之下,妈妈们往往会尽力展演成功、愉快而自豪的母亲形象,她们的不愉快经历被进一步屏蔽。”
杜鹃分析“母乳最优”哺育伦理时指出,母乳哺育与其他母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要求物质性母职和精神性母职的高度重合。物质性母职指养育过程中的物质投入,具体到哺育方式上就是指母乳,精神性母职则是指哺育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亲子关系的建立,母乳喂养被宣传为母爱,可以带来“善良、柔韧和安全感”,它需要在实际的母乳喂养互动中才能实现。“母乳最优”使得母亲和母乳必须双重在场,无法通过其他养育策略来摆脱或转移照料负担。这一单一的哺育伦理忽视了母乳喂养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使得因各种实际情况无法实现母乳喂养的女性感到内疚、沮丧和边缘化,从而加剧了母职对女性的压迫。
根据调查,虽然当代中国女性纯母乳喂养意愿很高,实际纯母乳喂养率却很低。201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婴儿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为29.2%,低于43%的世界平均水平。当大部分成为母亲的女性已经接受了“母乳最优”的理念时,在现实中实践母乳喂养却会遭遇重重困难。
要实现新生儿前六个月纯母乳喂养,首先要保证女性拥有至少六个月的产假,而中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的基础产假为98天,这意味着在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许多职场母亲就要回到工作岗位,“背奶”成为大多数坚持母乳喂养的职场母亲唯一的选择。所谓“背奶”,指的是妈妈上班期间利用吸乳器将母乳吸出来,储存在存储容器中,并放入冰包或冰箱冷藏保存,下班时再把母乳背回家,这样在妈妈上班期间,其他的照顾者就可以用奶瓶来给孩子喂母乳。
“一个背奶包、两大包冰块、电动吸奶器、四个储存袋,清点好了7点准时出门……一早起床,6点左右哺乳孩子一次,到了单位,上午10点、下午2点左右用吸奶器各吸一次……每天要争取吸出来350毫升,留作第二天白天孩子的口粮……下班回家,第一时间就要喂孩子,补上黄昏的一餐。”这是努力平衡职场与母乳喂养的“背奶妈妈”们的日常。
然而大部分职场母亲得不到公共场所或工作单位等空间的设施支持,不得不面对诸多不便和挑战。2019年1月曾有广州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议案中提及,在广州市选择背奶的人群中,仅有3%的用人单位设有哺乳室,85%的“背奶妈妈”只能在洗手间或隐蔽无人的办公室里进行吸奶。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2019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中国大陆所有城市在地图上标注出的母婴室数量为2643间,其中只有7座城市拥有超过100间母婴室——而同一时期东京一座城市的母婴室数量是5092间。

缺少足够的母婴室使母亲们面临着暴露身体的尴尬。《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显示,60.2%的母亲曾因为在公众场所哺乳不便而减少了外出,还有27.2%的母亲因为公众场所哺乳不便而给孩子喂婴儿配方奶粉。女性的乳房在实现其哺乳的生理功能之前,往往先与情欲、性感等想象相关联,女性的身体也由此成为性化的身体,而非是自然的身体。因此在当今社会文化中,公共场合哺乳并不被视为自然的行为,而是涉及乳房作为身体隐私被暴露的问题。当母亲需要在公共场合哺乳时,不仅会感受到身体隐私被窥视的困窘和不安,同时还可能面临“有碍公共道德”的谴责。
2020年10月抖音上一则视频引发热议,一位杭州“背奶妈妈”将手机镜头对准两个密封奶袋,她说:“这就是中国的高铁,有着冰箱,放着饮料,放两袋母乳,怎么都不行。”高铁工作人员以食品安全的理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有网友评论称“我要买东西吃知道是跟别人的母乳放一块的,我想呕,太膈应。”“今天母乳,明天口水,后天血液,然后就是大便小便了……”仅仅因为“占用”公共资源的“企图”,那位杭州妈妈被斥为“巨婴”,并最终道歉。从公共设施到公众态度,尽管“母乳最优”已经深入人心,母乳喂养在中国社会却依然缺乏友善、支持的环境。
2000年“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主题是“母乳喂养:你的权利”,这是自1990年设立该宣传日以来唯一一次在主题词中提及母亲的权利,其他的主题词无外乎母婴的“幸福”和“健康”。
在成为母亲后,女性的身体变成了“母乳最优”论述的实践场域。她们的日常经验无不围绕着“哺乳的身体”而展开。在这里,“母乳最优”已经不单单是客观的科学判断,而是女性不得不面对的压迫性话语。女性的身体因为哺乳而被异化为优先满足婴儿所需的“母亲的身体”,而女性自身的需求则常常被忽略或牺牲掉。

卢淑樱认为近代哺育方式的变革以及母亲角色的转型一直受到父权制、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的交叉影响。她发现近代关于中国婴儿哺育的研究较少提及母亲哺育方式自主权的问题。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中国,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如何在育儿的过程中掌握身体的自主权,一直都是想要为人母的女性需要解决的难题。
2018年7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要求删除论坛决议中关于政府应“保护、宣传、支持母乳喂养”的表述以及限制“母乳替代品营销误导”的段落,受到了《纽约时报》以及众多医学专家的反对。但主导修改决议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在回复媒体的邮件中解释说:“最初起草的决议给想要为孩子提供营养的母亲们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我们注意到,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进行母乳喂养。这些女性应该有选择和获得婴儿健康替代品的机会,不应因为这样做受到指责。”
无独有偶,在《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进入立场程序的一审阶段,也出现了一段戏剧性的波折。有立法专家提出,“在婴儿出生后的前六个月,推行纯母乳喂养”,“推行”应改为“应当”,出发点是优先保护弱小新生儿的健康权。广州母乳爱志愿服务队队长徐靓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们希望尊重每个妈妈母乳与否的权利,我们相信不管采取何种喂养方式,妈妈都是爱孩子的。‘应当’显然过于严厉,而且无从执法。”
“女性有权利决定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母乳喂养不仅涉及到婴儿的利益,更与新妈妈的身心健康权益密切相关,新妈妈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从促进母婴双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慎重选择。”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心理咨询师沈荟馨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张征是一位国际认证泌乳顾问(IBCLC),她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自己虽然是母乳喂养的支持者,但应该尊重妈妈们喂养方式的选择,“只有先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孩子,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滋养。一个快乐自信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或许比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杜鹃认为,真正理想的母乳喂养决策是母亲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权衡做出符合自己利益和孩子需求的选择,而不是被任何权威机构的指导建议所裹挟,被主流的喂养方式所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要在肯定母亲哺育劳动价值的基础上,为女性赢得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为各种形式的母职实践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
参考资料:
《母乳还是牛奶?对作为“母亲”的女性来说,从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https://mp.weixin.qq.com/s/oaGxm7QznfpSE0wsUr-7rw
《没有足够的母乳,就不是好妈妈?| 母乳妈妈们的“血泪”故事》
https://mp.weixin.qq.com/s/gGRUuJuY9rl-b-f7kPEkGA
《我是个“背奶妈妈”,我需要“公共冰箱”》
https://mp.weixin.qq.com/s/-QdZfoQqly1RfaWtPOXplw
卢淑樱.《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杜鹃.《“母乳最优”哺育伦理与整体性母职的建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4):54-64.
周培勤.《学哺乳:基于网络社区中妈妈关于母乳喂养讨论的话语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9(5):21-33.
许怡,刘亚.《母职初体验: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8):95-106.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母乳喂养因素调查报告(会议版)》.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