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普利策获奖作家谈了谈写作第二部小说的困难、用幽默探讨创伤,以及回归“更高效的美国帝国主义”。

阮清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我的叙述者是一个有两种思想和两张面孔的人,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图片来源:Joyce Kim/New York Times/Redux/Eyevine
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的第二部小说《践诺者》(The Committed)是他的成名作《同情者》的续篇。《同情者》是一部以越南战争为背景的间谍惊悚小说,既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也是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同情者》奠定了阮清越的文学明星地位,也让他成为了全世界流离失所者的代言人。在《践诺者》中,他的无名主人公以难民身份来到20世纪70年代的巴黎,在贩毒的黑帮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阮清越是南加州大学英语与美国研究、种族与比较文学的教授,也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评论员。
你曾说过,你写作第一部小说很轻松。在获得普利策奖后,写第二部小说是什么感觉?
阮清越:这当然更具挑战性,不一定是因为期望值的提高,而是因为我为普利策奖做的各种宣传。做采访、讲座,这些活动耗费了我的精力。写《同情者》的时候,我有两年的时间完全专注于此,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而写《践诺者》的时候,我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写,因为有很多干扰。
那么,你是如何克服这种脱节感的?
阮清越: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到了!这本小说有大纲,我一般都会忠实地按照大纲来写。我会50页、50页地写作,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前是这样。接下来几年,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混乱,那时我写了这本书的中间部分。到最后,我终于想明白怎样平衡对我提出的各种要求,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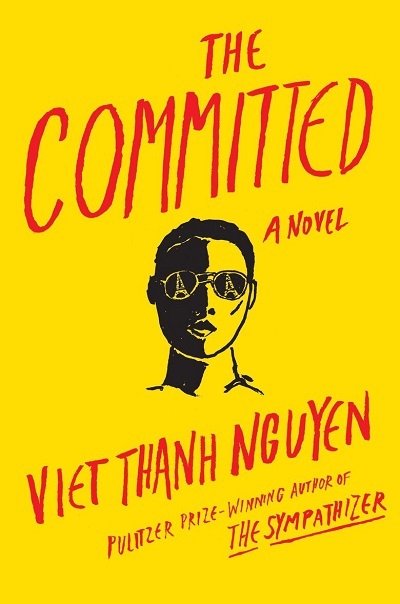
你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
阮清越:在这两本小说中,叙述者是一个有两种思想和两张面孔的人,我也差不多是这样。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难民在美国成长的感受。作为一个越南人和美国亚裔,我总是从内外两个角度审视自己。无论我身处何地,总觉得自己流离失所,总觉得不自在。在《同情者》中,我把这种感觉融入了小说,将其夸张地表现出来,让这些感觉和主人公的处境更戏剧化。在《践诺者》中我继续了这一过程。我也曾在巴黎和法国生活过,我也思考过主人公针对法国种族主义和法国殖民主义方面所做出的思考。在这部续集中,我还想让人们更加关注主人公对女性和性的态度:他对女性的物化倾向。这也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的革命政治的一部分,而在这第二部小说中,他开始有所意识了。
在两部小说中,你经常用幽默来引出创伤。你的主人公似乎曾经被流离失所的感觉所折磨,又总是同样地被他的困境所逗乐。
阮清越:在审视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局势时,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拿来取笑。关键总是要在喜剧和点睛之笔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也要立足于历史和政治。每一个低级笑话,比如说关于身体的笑话,都立足于这样的问题中:这些更强大的权力是如何准确地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运作的,并试图让我们忽略那些确实就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它们,因为它们已经被正常化了,但如果我们去掉这些正常化的视角,幽默感就会显现出来。

《同情者》在2015年出版时,你成为了难民危机的重要代言人。你认为我们从那个时候以及叙利亚内战的余波中学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阮清越:难民危机还在继续:一方面,政治和经济根源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动的恐惧依然存在。2015年前后,大约有6000万人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8000万。从这些数据中,我看不出我们在处理这些危机方面做得更好了。
对你来说,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阮清越:就叫它殖民化吧。这是如今很多问题的简写。难民危机、毒品战争、种族间的暴力。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我们所处的这段长达五百年的历史史诗——殖民化。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洲现代性的兴起紧密相连,并发展到美国。而即使去殖民化已经合法地发生了,但如果从被殖民国家是否真的摆脱了外国统治这层意义上说,去殖民化实际上还没有发生。前殖民地国家在文化和政治上仍有创伤,他们仍然有从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社会等级结构和自我仇恨的心理结构。而不管是西欧国家还是美国,这些前殖民大国仍然拥有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所有财富和权力。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力量是殖民化运作的根本,并且仍然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和内心。
《承诺》中的主人公似乎一直在纠结于典型的后殖民作家,尤其是弗朗茨·法农和艾梅·塞泽尔。这两位中哪位对你的思想影响最大?
阮清越:法农。我一直在回味《黑皮肤,白面具》这本书,因为它描述了被殖民的状况,尤其是对男人而言。(对女性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它试图解答的是种族与普遍性之间的问题,而法农在书中说的一切放在现在也是绝对贴切的。既想做普通人、又完全清楚不能摆脱种族主义赋予你的皮肤,他很精准地描述了这种两难的境地。
拜登已经在轰炸叙利亚了。说到美国帝国主义,你相信拜登在任何方面都会是一个比特朗普更好的总统吗?
阮清越:不,我不这么认为。我敢肯定,华盛顿的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共和党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拜登带来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更高效的回归。我松了一口气,是因为我不用再惦记着特朗普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政策,以及我认为他的对亿万富翁友好的经济政策。但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下,美国仍将延续一贯的方式。拜登几乎立即将轰炸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这既是可以预见的,同时也是非常可悲的。
你此刻在读什么书?
阮清越: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是今年普利策委员会的一员,我正在阅读所有的普利策提名作品,它们都写得很棒——但提名的书籍也是保密的。
好吧,那30年前,在你20岁出头的时候,读的是谁的书?
阮清越:托尼・莫里森、詹姆斯·鲍德温、拉尔夫·埃里森,还有美国黑人作家。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真正的冲击是长大后发现还有亚裔美国作家。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上了大学才发现其实亚裔美国人已经写了近一个世纪了。包括第一位华裔美国作家苏新发;卡洛斯·卜娄杉,第一批主要的菲律宾裔美国作家之一;约翰·冈田,第一个写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的作家。
如果你被困在荒岛上,只能读一本书,会是哪一本?
阮清越:《堂吉诃德》。
现在你出名了,你的学生会不会更关注你?
阮清越:我不知道。我的解答时间(学生可以预订一个时段,与教授谈论他们的学习进度)并没有学生光顾。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