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恋情不仅孕育了文学经典《奥兰多》,也为女性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

弗吉尼亚·伍尔夫(左)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约1940年。图片来源:AP/Getty Images
当我还在读本科,刚以女同性恋身份出柜的时候,我时常溜到一个光线昏暗的偏僻之处——图书馆的书架之间,在那里,我知道我会找到其他和我一样的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不是我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同伴,但她肯定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
我是在她儿子奈杰尔·尼科尔森1973年出版的《婚姻的肖像》(Portrait of a Marriage)一书中找到她的,这本书讲述了他父母持久而开放的关系。我了解到,维塔和她的丈夫——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各自都有过多次婚外情,大部分是和同性。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仍然对彼此、孩子和他们著名的花园忠贞不渝。书中还收录了在与哈罗德结婚初期,维塔对自己与维奥莱特·凯普尔的痴情关系的描述。我被维塔在巴黎的形象所吸引,她用卡其布色头巾包住头,假装是男人(这在一战结束后并不罕见),并和她的情人一起在街上漫步。这个女人是谁?
在书的最后,作者对母亲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恋情进行了简要的描述。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伍尔夫的任何作品,但我许多朋友的墙上都有一张她的明信片,是她二十岁时在贝尔斯福德拍摄的空灵肖像。她的脆弱之美符合此时正在凝聚的悲剧叙事和女权主义女英雄的叙事:她是个天才、她被继兄猥亵过、她与某种精神疾病作斗争,最后,在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几本书后,她淹死了自己。在某些圈子里,一个更有争议的说法是,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女同性恋,她都是相当有个性的。令我感动的是,小时候,奈杰尔·尼科尔森和他的哥哥本能地被弗吉尼亚吸引。“我们知道她会注意到我们,会有那么一刻,她会不理会我母亲(‘维塔,走开!你没看见我在和本和奈杰尔说话吗?’)。”在《婚姻的肖像》中,我了解了一些关于维塔和哈罗德如何协调维塔与弗吉尼亚的关系,但我发现自己希望有更多的渠道来了解这两个值得怀疑的女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细节。
几年后,我的愿望实现了,维塔写给弗吉尼亚的信出版了。那时我已经读过几本弗吉尼亚的书,因此,观察这两位作家如何达到这种深刻的亲密关系(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与某人建立这样的亲密关系),就更有意义了。他们对彼此的热情让我感觉到,他们为所有女性开辟的新领域与我息息相关:弗吉尼亚用她的作品,维塔用她的世界。那时我才20多岁,尽管这个爱情故事在书页中那么栩栩如生,但感觉就像发生在很久以前,发生在古老的过去。
人到中年,我重读了一遍这些信。如果我对信件之间的连续相关性有任何怀疑,那么在我自己私密生活中的一段棘手时期,当我发现两个不同的女人引用了同一段话时,这种怀疑就烟消云散了。不过这一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维塔和弗吉尼亚如何在保持亲密联系的同时,兼顾她们梦幻般忙碌生活中的所有元素:公共需求、创造性工作、家庭和社会义务,以及包括与丈夫的关系在内的其他关系。

现在,我已经60岁了,比弗吉尼亚去世时大一岁,比维塔死于癌症时的年龄小十岁,我被信中的另一个方面所打动:她在面对损失、疾病、幻灭和变化时,仍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疏离之后,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她们的个人和思想自由受到的威胁越来越近,两人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密切。弗吉尼亚和维塔相爱,距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奇怪的是,这感觉比我年轻的时候近了许多。也许是因为这是年龄的视角,也许是因为世界似乎又一次接近另一个拐点。但这也是对弗吉尼亚和维塔的一种赞美,她们无畏地抛弃旧有的关系形式和传统,即兴创造新的东西。
我年轻时读过的那版书信主要是维塔写给弗吉尼亚的,但也包括一些弗吉尼亚写给维塔的信件摘录。新出版的《情书:维塔与弗吉尼亚》(Love Letters: Vita and Virginia)虽然不是她们通信的完整汇编,但重点在于两人之间更令人欣喜的书信交流。而更精彩的是,书信集囊括了两人的日记,以及维塔写给哈罗德的信。这些时不时的视角转变为弗吉尼亚和维塔的关系提供了更完整的画面,也为这段已经像一部精心策划的小说一样引人入胜的叙事增添了动力。
如果维塔和弗吉尼亚之间的通信是一部小说,那么它会因为主人公的名字过于显著而受到批评。一位女主角涌动着生命力,大步跨越半个世界再回来;另一位主要生活在自己想象的荒野中。弗吉尼亚与丈夫伦纳德的婚姻是贞洁的,尽管她在一开始就勇敢地尝试了“交媾”。(“这,”维塔转述给哈罗德,“是一次可怕的失败,而且很快就被放弃了。”)但弗吉尼亚和伦纳德有着属于他们的一种亲密关系——他是她的第一个读者,并在她崩溃的时候照顾她。他们没有孩子,但他们共同的企业霍加斯出版社为世界带来了许多重要的书籍。
当维塔和弗吉尼亚在1922年底相遇时,维塔30岁,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弗吉尼亚40岁,她的小说和散文刚刚开始得到认可;维塔是贵族和社会名流,弗吉尼亚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破屋居民。那时,布鲁姆斯伯里是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艺术家和良心反对者的巢穴。当然,维塔此时更出名的是她的情人和她的花园,而不是她的书,而弗吉尼亚已经进入了大众视线。但在当时,弗吉尼亚得知维塔竟然听说过她的名字时,非常激动。随着两个女人的称呼从“尼科尔森夫人”“伍尔夫夫人”转为“亲爱的”“最亲爱的”,再到一连串的绰号和头像,一场伟大的文学情缘就此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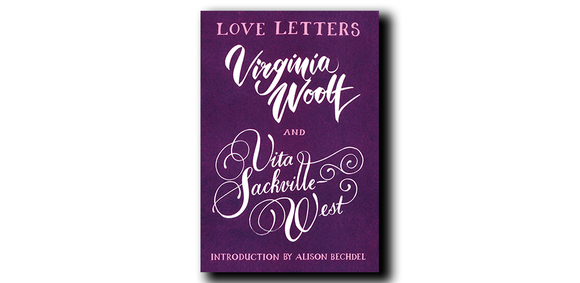
虽然他们早期的信件已经闪现着调情的火花,但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升温。维塔在他们见面后不久就与一个男人发生了纠葛——这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变化。而弗吉尼亚对这个“可能喜欢我的女同性恋”也很警惕,“虽然我已经老了。”但一旦弗吉尼亚邀请维塔向霍加斯出版社投稿一部小说,而维塔也将《厄瓜多尔的诱惑者》(Seducers in Ecuador)寄给了她,二人相互吸引的步伐就加快了。1925年,弗吉尼亚在写完《普通读者》和《达洛卫夫人》之后疲惫不堪,这两本书让维塔目瞪口呆,也加剧了弗吉尼亚之于她的神秘感。但当弗吉尼亚得知维塔将前往德黑兰与哈罗德会合几个月时,她的离开似乎让他们俩都兴奋起来。
当维塔踏上旅途,她们交换的信件都是关于怀念的杰作。两人在火车上持续通信,其中来自弗吉尼亚的一封只有短短数语:“是的是的是的,我确实喜欢你。我不敢写出更强烈的字眼。”维塔计算着他们下一次相见的时间(48万秒)。这些信是如此令人陶醉,以至于当维塔最终回到英国时,反而显得虎头蛇尾。但这当然是书信体叙事的本质。读者最希望的事情是主角们最后在一起,但这却是读者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她们的书信在此后停止了。
从一开始,两位女性就完全清楚自己在对方身上渴望什么。弗吉尼亚爱的是维塔的身体,维塔爱的是弗吉尼亚的头脑。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写道,“她像雄鹿或赛马一样……没有非常敏锐的大脑,但她的身体是完美的。”弗吉尼亚所说的“身体”不仅仅是指维塔的实际身体,而是正如她后来所阐述的那样,“她的能力,能在任何公司胜任,能代表她的国家,能访问查茨沃斯,把银餐具、仆人以及宠物狗管理得井井有条,再加上她的母性(但她对儿子们有点冷淡和不近人情),总之,她是(我从未能成为的)一个真正的女人。”
维塔在给哈罗德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弗吉尼亚的第一印象。“起初你觉得她很平凡,然后就会有一种精神上的美感强加给你。”维塔一直竭力说服哈罗德,她对弗吉尼亚的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而精神上的东西是一种智力上的东西……”她高兴地向他报告说,与弗吉尼亚的谈话使她感到“我心灵的边缘好像被一块磨石抵住了”。虽然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对维塔的写作进行了一些暗讽,但维塔对弗吉尼亚的作品却充满了敬佩之情,而她更值得称道的一个特点是,她能够不嫉妒地欣赏弗吉尼亚的卓越才华。事实上,她会和伦纳德一起致力于保护和培养弗吉尼亚的才华。维塔在给哈罗德的信中说,“(弗吉尼亚)给我一种温柔的感觉,我想,这是因为她有着硬朗和柔软的有趣结合——她心灵的坚硬,以及她对再次发疯的恐惧。”
正是这种温柔和需要被关怀的动态关系,构成了维塔和弗吉尼亚联系的真正核心。当她们的关系接近肉体关系时,弗吉尼亚在日记中描述道,维塔是“如此地给予我母性的保护,不知为什么,这是我一直以来最希望从每个人那里得到的”。弗吉尼亚的亲生母亲在她童年一直缺席,在弗吉尼亚13岁时过世。维塔自恋的母亲,在信中是一个强大的存在,或许也是维塔用她的照顾方式让人们不敢过于靠近的原因。两个女人都是专家,都很擅长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当维塔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弗吉尼亚找人为她誊写时,弗吉尼亚非常反感,几封信之后,维塔才设法让她平复下来。然而,利用维塔为她誊写正是弗吉尼亚接下来要做的事,以最明目张胆、最奇幻的方式。

“……一本从1500年开始一直写到今天的传记,叫做《奥兰多:维塔》,只不过换了性别。我想,为了享受,我应该让自己在一周内把它完成。”虽然在1927年秋天,当维塔与另一个女人好上之后,弗吉尼亚就开始紧张地、几乎是自动地突击写作《奥兰多》,但这本书似乎在五年前他们两人相遇的那一刻就开始酝酿了。弗吉尼亚被维塔的贵族血统所吸引,曾向她索要了一本《克诺尔与萨克维尔家族》(Knole and the Sackvilles),一本关于维塔祖居的历史。几周后,在维塔和哈罗德第一次与弗吉尼亚和伦纳德共进晚餐后,不守陈规的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写道:“像我这样势利的人,我追溯到她五百年前的激情,它们在我眼里是如此浪漫,就像老黄酒一样。”1924年,弗吉尼亚访问克诺尔时,奥兰多已经有了雏形。“你漫步在数英里长的画廊里,扫过无尽的珍宝,包括莎士比亚可能坐过的椅子,还有挂毯、画作、用半截橡树制成的地板……”
《奥兰多》这幅梦幻般的画像,以传记的形式漫游英国历史和文学,它是虚构的,却又是真实的,其主题既不固定于时间,也不固定于性别,它无法被归类。这本书是弗吉尼亚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书,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其八卦因素:弗吉尼亚把它献给了维塔,甚至还附上了她的照片,所以这本书以谁为原型并不是个秘密。但《奥兰多》的畅销也因为它是如此出色和新颖。我们很难理解,在那样一个更为保守的年代,弗吉尼亚怎么能如此自在地把玩性身份认同这个主题,并为自己发明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奥兰多从男性到女性的流畅蜕变,既预见到了后来的理论转变,也使得我们对性和性别的思考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奥兰多》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女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但它又是如此巧妙而错综复杂,以至于逃过了《寂寞之井》(拉德克利夫·霍尔创作的自传式小说)的命运。同年出版的《寂寞之井》被审判并认定为淫秽作品。不过,弗吉尼亚《奥兰多》的最大胜利,也许是维塔喜欢它。尽管《奥兰多》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嫉妒而写成,并无情地切中了维塔的个性核心,但也反映了维塔一直认为在某种层面上自己是颇具英雄气概的贵族——如果她生为男性,她就会继承克诺尔,她父亲去世后,房子和头衔就正式传给了她的叔叔——但在《奥兰多》中,弗吉尼亚光荣地将它们归还给了维塔。

多年来,关于弗吉尼亚和维塔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每部作品都捕捉到了两人的某些特质。在BBC2的剧集《婚姻的肖像》中,珍妮特·麦克蒂尔饰演的维塔体现了王尔德式的雌雄同体。莎莉·波特导演的《奥兰多》中,蒂尔达·斯文顿展现了她的女性特质。戴着假鼻子的妮可·基德曼在《时时刻刻》中饰演的是一个受尽折磨的弗吉尼亚,而伊丽莎白·德比茨基在钱亚·波顿最近导演的《维塔与弗吉尼亚》中,饰演的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维塔。当然,即使是最出色的表演,也无法像弗吉尼亚和维塔自己的文字那样,传达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写信的方式、笔尖在纸上的摩擦、速度慢到足以让人形成实际的思想,已经不流行了。如果弗吉尼亚和维塔有智能手机,那们我们的手指会划过一连串的色情短信缩写、晦涩难懂的表情符号、《泰晤士报》的书评和推特链接,以及无穷无尽的阿尔萨斯和西班牙猎犬的照片,而不是这些华丽的书信。幸运的是,即使多年来她们之间的感情从激荡转为平静,她们依然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他们的通信热情洋溢,博学多才,动人而俏皮。信中充满了八卦、欲望、嫉妒和写作技巧。也许最令人高兴的是,她们的措辞经常令人捧腹大笑。弗吉尼亚在日记中思考, “我爱上她了吗?但什么是爱呢?”在这些信件中,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有些离奇的回答。
本文摘自《情书:维塔与弗吉尼亚》导言,作者艾莉森·贝奇德尔是一位美国图像小说家,她提出了著名的贝克德尔测验。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