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倪湛舸认为,网络类型小说值得最好的理论和方法。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有必要把耽美小说当成小说研究,它们值得最好的理论和方法。”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倪湛舸这样写道。日前,在以施存蛰堂号命名的“北山讲堂”,她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之邀发表了《革命加恋爱再加机甲和丧尸——网络类型小说研究方法论初探》的演讲,为听众讲解了网络类型小说的读法。
倪湛舸近年来关注网络类型小说的研究,对修真、耽美和盗墓类均有涉及,本次讲座主要以两部耽美小说Priest《杀破狼》和非天夜翔《2013/末日曙光》为例,探讨了网络类型小说研究的方法论。她指出,阅读网络类型小说的三大工具是细读、远读和机读。在这些阅读方法的指导下,她分析了两部小说的世界构建和欲望集合并指出,随着娱乐成为重要产业,类型文学发展成为了跨媒体叙事,世界构建成为了重心,人物和情节都成为了世界构建的一部分,人物已不再只是理性主体,而主要起到欲望通道的作用。
在欲望引导和世界构建直接合流的倾向中,以这两部小说为代表的耽美小说形成了一种“革命+恋爱”的套路。这类耽美小说回避色情描写,并打出了“家国天下”的安全牌,这既可以说是一种求生策略,也是“家国天下”这种文化DNA在耽美小说中的体现。不仅如此,两部小说还试图以儒家的伦理-政治-宇宙观念改造蒸汽朋克和丧尸末日这两个以重组社会结构为已任的外来新类型,回到中国儒家传统和人伦,使得革命题材不可避免地向恋爱发展,从而打破了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中公域和私域之间的壁垒。

倪湛舸在讲座中梳理了幻想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她看到,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是在客观历史中、理性范畴内的虚构。中国人熟悉的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学是这种潮流的延续,其主流就是启蒙和救亡,负担着现代主体构建的任务。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贸易资本主义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出现,类型文学作为大众娱乐方式出现,这些文本的想象空间突破了客观历史和理性范畴,因此处于边缘地位。这种边缘化也是因为它们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不直接参与资本增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化起步,娱乐逐渐成为核心产业,类型文学也随之开始主流化。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数码资本主义年代,类型文学发展成为了跨媒体叙事,重心从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转移到世界构建,例如漫威宇宙从六七十年代的漫画拓展到了全方位的创意产业,叙事不再依赖单一文本、单一作者、单一媒介,而可以进行广泛的蔓延。网络类型小说属于这个潮流,其人物和情节也大多服从于世界构建和其背后的资本扩张,但这些小说同时也蕴含着非资本主义甚至反资本主义的潜力。
以《杀破狼》和《2013》为例,在世界构建方面,两部小说写的都是架空的中国,都经历了世界格局的变动。《杀破狼》架空中国近现代史,核心矛盾是新能源引发的中欧大战,讲述了中国如何从帝国进入到“天下”视野中的民族国家。《2013》则架空了中国当代史,2012年是故事中丧尸爆发的年头,2013是后末日时期开始重建国家的节点。
《2013》也关心国族构建,讲的是如何突破民族国家的格局,进入到后民族国家的“天下”。两个小说虽然有类似的结构,但是两者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一个是进入、维护民族国家制度并在其内部进行改良;另一个则是要直接打破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并进行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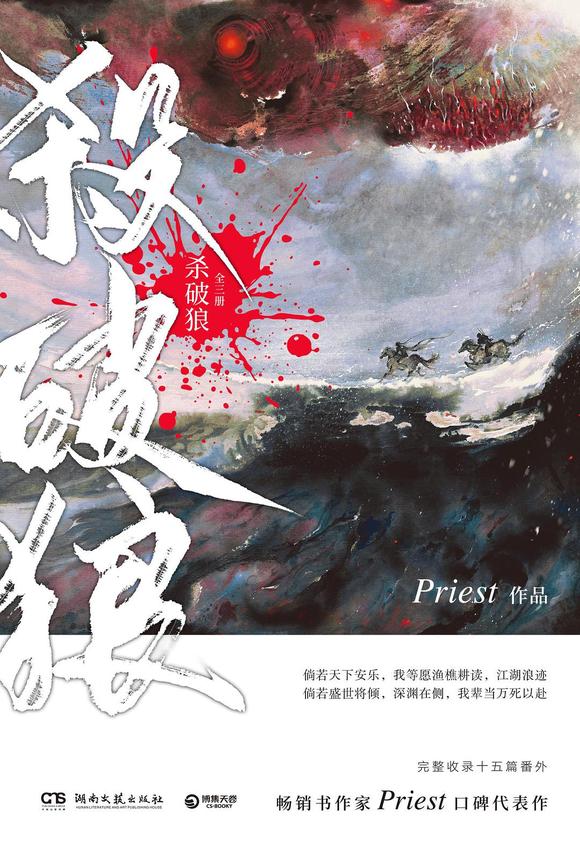
不仅世界构建变成了重心,人物也从理性主体变成了欲望通道。倪湛舸看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及至今,现实主义文学都是主流,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塑造要完成(或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社会性的成长和精神层面的训诫。类型文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在二十一世纪主流化。兴起之初,作为对启蒙运动和工业化的回应,它收容不符合现代标准的欲望、观念、行为,为新兴的无产、中产阶级提供消遣娱乐。如今,创意产业正在成为数码资本新的增值点,而创意产业剥削的是人的欲望,类型小说的人物起到的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欲望通道的作用。
《杀破狼》《2013》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军事-工业-信息综合体,前者军事对应的是军人,工业对应的是技师,信息对应的是政治经济的改革派,几个主人公从事的工作分别对应了这几个方面;后者也类似,只不过把发展经济的改革派置换成了关心生态的科学家。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线索直接从属于危机时刻的救亡图存,两部小说都有个人欲望和整体世界直接合流的倾向。
在《杀破狼》里,主角有这样的宣言:
“我想有一天国家昌明发达,百姓人人有事可做,四海安定,我的将军不必死守边关,想……解开皇权与紫流金之间的死结,想让那些地上跑的火机都在田间地头,天上飞的长鸢中坐满了拖家带口回家探亲的寻常旅人……每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活。”
《2013》里,也有这样的对话:
“国家在哪里?它不是一个虚幻的名词。”赖杰漠然道:“蒙烽中士,它是这个农场,农场里的所有人,也包括你的爱人。”“南到南沙群岛,北到漠河,你所站的地方,你在逃亡里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满目疮痍的故乡,变成废墟的城市,就是你的祖国。”
由此可见,两部小说的重心就是“修身”和“平天下”,两者之间出现了家国。恋爱故事和革命故事要处理的是国族构建的问题。两个故事都触及了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深入探讨,其在阶级和民族问题上的复杂性被回避了。倪湛舸认为这和耽美原创的尴尬处境有关,它们把感情纠结简单化,回避或删除性描写,为了突出主要矛盾而打出“家国天下”的安全牌,成为中国版的同志民族主义(homonationalism,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同性恋议题和民族主义挂钩,使得同性恋议题得到一定的正当性)。同志民族主义是耽美小说的一种求生策略,但也并不完全是策略,因为“家国天下”是一种文化DNA,中国民间确实有传统文化重建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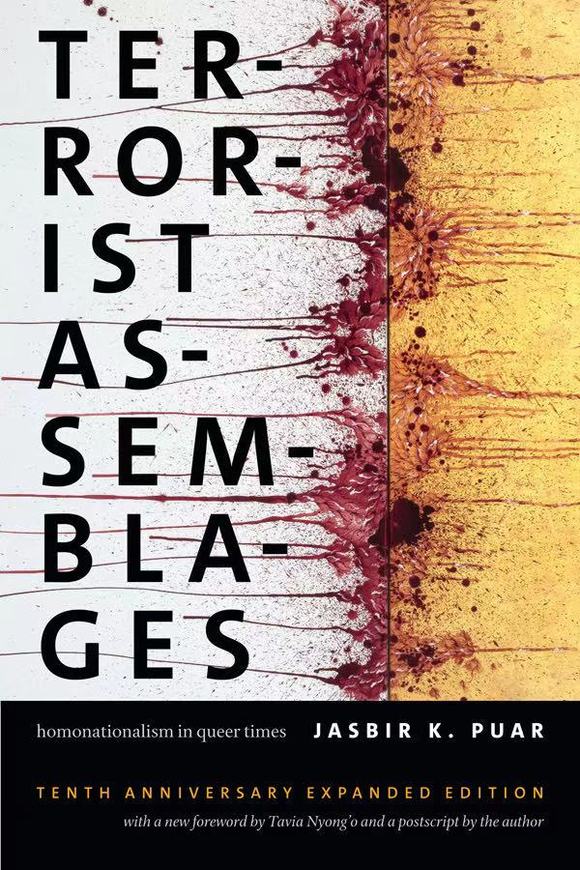
恋爱为什么可以上升到革命的高度?倪湛舸看到,耽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言情文学,且有色情成分,而言情(色情)文学是有乌托邦冲动的。她说,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曾编写一本书《情史》,提出“情教”概念,把情和儒家的政治秩序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研究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文学的Steven Marcus,研究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女性色情文学的Amalia Ziv认为,色情文学描写的过程中,为了凸显欲,要建造相对封闭且脱离现实的环境,所以色情文学自带乌托邦冲动。耽美小说的“纯爱”符合情教的话语,因为情教就是要推崇情而压制欲,在这两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情”的救世和创世功能。情起到了拯救的作用,革命的原动力其实是恋爱,恋爱不仅仅是在私人领域的狭义的感情,它变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
除了从“恋爱”到“革命”的内在逻辑,倪湛舸还从远读视野中的类型史来梳理了“革命”到“恋爱”的内在逻辑。她看到,蒸汽朋克和丧尸末日都是美国流行文化中的类型,它们进入中国之后,最先汉化它们的是女频作者、耽美作者,而不是通常理解中的科幻作者。小说以儒家的伦理-政治-宇宙观念改造外来类型,回到中国传统就会回到人伦,加上耽美小说本身又会带着情教的主题,所以革命题材就不可避免地向恋爱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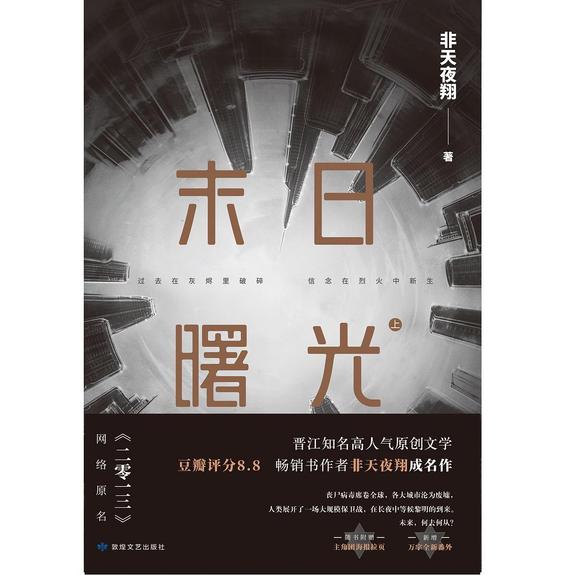
讲座中,华东师范大学国汉学院教授毛尖对用“恋爱+革命”这种模式来解读网络类型文学存有质疑。“恋爱+革命是套路,还是文学史前情提要?”“恋爱+革命” 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特定词汇,适用于研究网络文学吗?她认为,网络类型小说中,世界创造大于人物,类型决定风格,叙事基本被类型决定。看不太出里面有真正的革命,基本都是政变,爱情也是一种政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互相隐喻。毛尖因此认为,与其说是革命加恋爱,不如说是张恨水模式——大量耽美的爱情模式其实是很主流的写法,没有当年同性恋小说的先锋性,很民国套路,当然,“这里使用套路,没有贬义。”革命有一个秩序摧毁问题,网络文学则经常是重回秩序。而回到形式和套路,网络小说确实也有革命的形式,有不少推翻皇帝的故事,“但一个推翻皇帝的故事可能是革命,篇篇都推翻皇帝就是套路了。”
对此,倪湛舸提出,我们不妨打开“革命”的概念。这两部网络小说里谈到的革命的概念已经不是国族构建年代的革命,这个革命是革命的本意——革新、天命——是做整体性变化的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革命”被解读成救亡图存、国族构建。但是,现在的“革命”不仅是要处理国族的问题,也要处理主体构建和国族构建受到全球资本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网络文学捕捉到了。
在数码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年轻一代通过娱乐参与资本生产,参与资本生产的过程中也在追求一定意义上的反思。”她说,自己在网文的讨论区中就看到很多读者的相关讨论,“网络文学是在新的时代探讨新的问题。在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上,严肃文学反而是落后的。”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也很复杂,必须深入到具体文本内部做细致考察,不能以保守或进步一概而论。网络文学也必须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上研究,现有的思路只关注它的媒体生态,被忽视的是网络文学与明清民国通俗小说、英美类型文学之间的继承和变化关系,而网络文学与所谓的严肃文学之间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正如同英美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与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的流行小说其实是并生互利的,而非通常想象那样的井水不犯河水。

网络类型小说该怎样读?“耽美研究一般偏重于做粉丝经济、性别政治,对小说文本本身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我们首先要看小说,所以要细读。”倪湛舸说,小说进行细读,即对小说文本的观察、分析和阐释。其次,针对“类型”,读者还可以进行远读。对小于文本的主题、技法等写作要素的演变研究,对大于文本的类型史和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的梳理。不仅如此,由于网络类型小说的“网络”特质,还有“机读”这一读法,即把网络文学数据化,建立对套路和类型的理解。“机读必须和细读和远读相结合。机读只拿到数据,不进行阐释是没有意义的。三者必须齐头并进。”
她指出,细读一方面是关注字、句、段落、篇章,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人物、情节、叙述视角、环境在内的叙事整体。尤其是在21世纪的网络类型小说中,人物和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在远读时,她重点考察了两部小说小于文本的主题,即革命加恋爱,和大于文本的类型——蒸汽朋克(《杀破狼》)、丧尸末日(《2013》)、耽美原创(两者皆是)。
毛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细读、远读这些方法也还是有自己的边界,即便莫莱蒂的《远读》,处理的也常常是《哈姆雷特》这些文本。而对于网络小说来说,她提出,情节是最小的语义项,“网文是大剂量写,我们也是大剂量服用,基本也是快进读法,真心很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认为,网络小说还是适合用“群读”用游戏法则用套路来研究,这个不是低看网文,而是觉得,大规模机甲和丧尸来袭,就应该有“机甲和丧尸”研究法。
但是,因为网络类型小说太多太杂,我们看到的套路不是全貌,即使能把套路确定下来,文本和读者的互动也是多元的,是套路不可能涵盖的。倪湛舸据此认为,细读是必须的。而且,细读和远读结合向来都是英美流行文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她还看到,很多网络类型小说的作者本身会做细读。他们通过细读研究自己的写法,这种写法虽然更在意故事的讲法、塑造套路化的人物,但终究是为他们写作打下基础的阅读方法。而研究这类小说,要把自己带入作者视角、读者视角。在网络小说的讨论区,经常可以看到读者针对具体细节做多角度的细读和讨论。所以,细读的概念也需要被打开,它不仅是抠字眼,也需要关注整体文本,和读者、作者进行互动,和类型以及文化史思想史进行互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董丽敏说,她不反对细读、远读、机读,但是她认为细和远之间,似乎缺少一个中间过渡。“有没有一套方法对某一个类型有效,还是说所有方法对所有类型都有效?”倪湛舸回应称,针对不同的类型小说有必要建立起不同的细读模式。很多耽美小说经得起狭义的“文学”细读,但是修真小说动辄几百万字,读者就是要跟着小说画地图,关注以升级为主的人物成长。因此修真小说的细读需要在情节设置、人物之外的世界观建构上做更多的观察。她还指出,盗墓小说是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和夺宝奇兵类型的盗墓故事的融合,小说篇幅随着类型的发展和成熟越来越长,经历了一个类型成长的过程。修真小说类似,因为写作经常跨越数月数年,具体的写作风格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也是只能依赖细读才能发现的。因此,网络文学研究如果要继续推进,离不开细读,“不同类型的不同细读方法需要群策群力,”细读还需要远读、机读和更多读法的配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新兴的网络文学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合作,跨学科研究与跨媒体现象之间的匹配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