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散文集《在巨人国》中,每当克瑙斯高将目光投向具体、感性以及个人化的东西时,都会滑向苍白无力的抽象。他的散文涉猎虽广,但却有盲目贪多之嫌。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死忠粉丝想必会欣赏他的童年回忆 摄影:Federico Gambarini/dpa/AFP via Getty
小说集现在很流行。二十世纪的小说有一种木偶戏般的矫揉造作,它业已令人生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系列本身就是对此的一种回应——进而令文坛对迄今仍属边缘的体裁产生了新的兴趣。试水者不少,成功者寥寥。克瑙斯高的新文集融文学、当代艺术、摄影、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与天马行空的遐想为一体,但就这一文体而言,克瑙斯高还称不上是一流作家。
克瑙斯高2011年时完成了自传体史诗六部曲,号称创作生涯已经圆满,但《在巨人国》(In the Land of the Cyclops)却令人不禁对此生疑。自那以后,他的任何作品都带有增补本或杂文集的味道——尤其是他与人合著的那本电子邮件集《主客场》(Home and Away),长达400页,主要谈足球。在“四季四部曲”(The Seasons Quartet)里,死气沉沉的克瑙斯高给每一天都想了一个替代性的称谓或物件(疼痛、纽扣、阴唇),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俨然他闻名世界这件事本身就能使他获得理解。他沉迷于一种天真的眼光,将日常琐事悉数神圣化,某些时候还很像马丁·艾米斯的小说《信息》(The Information)里描绘的那些可笑的作家,这种人吃了一炮走红的甜头,随便看什么东西都能强行加戏,以凸显自己也拥有文学泰斗的那种孩童一般的好奇心。
接下来的部分是对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小说《投降》(Submission)的长篇评论,在开头,克瑙斯高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以前从来没读过维勒贝克的书,就好像我们对这个不够格的评论者的兴趣会比他的评论对象更大似的。他对《包法利夫人》的把握要稍好一些,评论同胞克努特·汉姆生(二人原籍皆为挪威——译注)《肮脏的现代主义》(Dirty Modernism)的长文写得也要扎实不少。一篇有关在贝鲁特读克尔凯郭尔(Kierkgaard)的文章开头亦坦承了克瑙斯高对这位丹麦哲学家(某位责任编辑也确实很喜欢标题上的对仗——克瑙斯高论克尔凯郭尔)的认识还比较粗浅。他对克尔凯郭尔思想的解读基本在别处都能找到——且没有一处能在生动性上与他那件万分折磨人的轶事相比:向一位有战争后遗症的中东节(Middle Eastern festival)观众朗读《我的奋斗》里的一篇文章,其中克瑙斯高为取悦一名女性而自打了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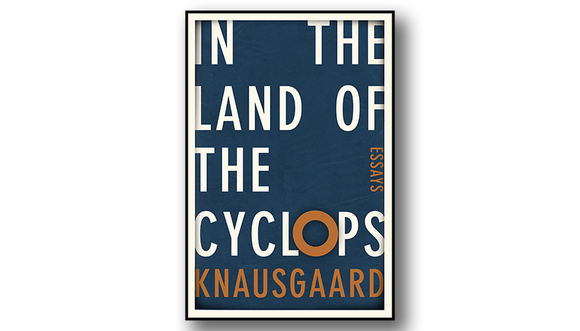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奋斗》里最出色的章节是在丑闻和淫秽色情的层面上创作的——讲了几千页的北欧真人秀电视节目,行文风格叽叽喳喳、喋喋不休。克瑙斯高谈艺术和摄影的章节本来还可以做到引人入胜(提到了辛迪·舍曼、安塞尔姆·基弗和弗兰瑟斯卡·伍德曼等人),然而他身为小说家却非要摆出一副哲学家的批判姿态,给读者的感觉就像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特殊主义者努力要成为柏拉图式的普遍主义者。每当他将目光投向具体、感性以及个人化的东西时,都会滑向苍白无力的抽象。他的散文涉猎虽广,但却有盲目贪多之嫌。《宇宙愚人》(Idiots of the Cosmos)一文游弋于身份政治、《战争与和平》、帕斯卡尔对无限的恐惧、北极光和其它一大堆话题之间,但谈出了深度的话题却一个也没有。没有了重构或想象的世界(关于童年、少年和成年)来支撑其感受力,他的思想就变得很散乱了,缺少章法且无足轻重。说难听一点,作为散文家的克瑙斯高就是个自娱自乐的话痨。
与标题同名的《我的奋斗》是个例外,透出一股好战的气息。此文初读起来像是对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的一种讽喻,读到很后面你才会发现他其实在谈瑞典。克瑙斯高的第二故乡似乎将一种严苛而烦人的平庸推到了极点。带着一种谨慎的义愤,他详细讲述了官方媒体如何把自己污蔑为恋童癖、厌女者及纳粹分子,更把他与安德斯·布雷维克相提并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就写了一本小说而已。”他还老调重弹,称当今的北欧自命清高,导致某些常识性的立场也需要辩护了:艺术应当表现杂乱的现实而不仅仅是理想;虚拟的描绘并不蕴涵纵容的举动,等等。显然,他对这些事耿耿于怀:《主客场》也曾严厉批评瑞典自由派的不宽容及自居正人君子的做派(用的例子是:某个持女权主义立场的青年团体当时抨击过他)。
克瑙斯高的死忠粉丝想必会很欣赏他对童年经历及年少轻狂的回忆,哪怕有些内容属于炒冷饭。《我的奋斗5:总有阴雨天》(Some Rain Must Fall: My Struggle Volume 5)有一种阴暗的魅力,克瑙斯高在其中着重回顾了一个有预言意味的梦,梦里预示了一个给予他甚大打击的事件:一桩恶意的虚假强奸指控。然而我们正好借此洞察到《在巨人国》的核心缺陷:克瑙斯高的自传体小说把我们锁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第一人称视角里,而且这还是头一次;有关文学、精神分裂症、但丁、第谷·布拉赫以及冰岛史诗的随想显得冗长、无度且了无生气,比较而言,梦及其预示的恐怖只算得上小插曲。“我恨我自己,”克瑙斯高在日记体的《宇宙底部》(At the Bottom of the Universe)一文里自顾自地宣称。我从来不恨他,但我个人确实希望他能明白我的用意,容我把他礼送出门,这样我就能在扶手椅上好好休息一阵了。
本文作者Rob Doyle是作家、小说家。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