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智力和文化力量,在个人崇拜以及大规模军事动员中找到了强有力的表达。

金字塔战役前夕,拿破仑·波拿巴对军队发表演说。安托万-让·格罗 绘,1798年。图片来源:Leemage/Corbis/Getty Images
1791年,在法国最有价值的加勒比殖民地圣多明各,成百上千名被奴役的人揭竿而起。战争紧随而来,在这场导致了1804年海地共和国独立的战争中,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从籍籍无名中崛起,领导了自我解放的起义军,对抗不断变化的英、法、西班牙联军。一名传记作家写道,杜桑使对手胆寒,“就像一棵高大威严的树,在它生长的时候,使所有杂草和灌木望风披靡。”
他是全球分裂时代英雄人物中的一员。1776年,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粉碎了欧洲政治和解。1804年,海地人的独立彻底否定了殖民地奴隶制,动摇了大西洋种植园经济的根基。1808年,拿破仑对波旁王朝西班牙的征服,激发了横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领土上的民族独立运动潮。
受好奇心、全球交往的扩张、启蒙运动中日益提高的识字率和大众教养等因素的驱动,历史的故事继续着,而这些革命成为了现代自由民主的起点。对君主制负有具体或习俗性义务的臣民,成为了具有抽象公民权利的公民,并参与到政府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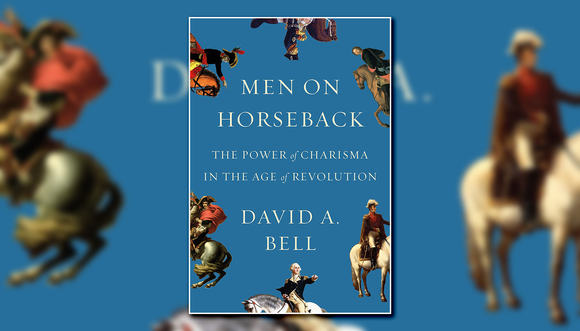
而现在,正如历史学家大卫·A·贝尔在《马背上的那些人》(Men on Horseback)中所写,如果我们严肃地看待这段“革命年代”,将其视作现代民主崛起的开幕,我们也必须审视作为革命原动力的那些魅力非凡(即“卡里斯玛”)的伟人。像杜桑这样的领导人因其武德而受到称赞,这让人联想起古罗马时代。自由民主的先驱常常像独裁者那样统治,唤起公众意志,为个人统治正名并美化。
让我们从巴斯夸·帕欧里开始,他是18世纪中叶先后反抗热那亚人以及法国人对其家乡科西嘉的控制的起义者,贝尔追踪了这些开明统帅之间的谱系。帕欧里红遍欧洲,他出现在书里、歌里以及画作里,作品主题从爱国主义到色情都有。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些民谣歌手为了满足公众对纪念这位高大英俊将军的纪念需求,就把帕欧里的名字换成了乔治·华盛顿。
1799年,华盛顿去世,法国年轻的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宣布举国哀悼。不久之后,杜桑成为拿破仑在安的列斯群岛的陪衬,法国的敌人称赞他在战斗和管理方面超人的毅力。最终,西蒙·玻利瓦尔——他在南美的早期战役中,仰赖海地军队的支持——在与西班牙帝国作战时,有意识地借用了过去50年中才诞生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话语。

贝尔是研究法国史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借其名义实施的暴力和镇压之间的紧张关系十分敏感。他认为,启蒙运动的智力和文化力量,在个人崇拜以及大规模军事动员中找到了强有力的表达。
当识字率在欧洲以及欧洲的殖民地上升时,印刷文化也随之生长。尽管有些人把“启蒙运动”当做科学、世俗主义以及和平的缩写,真正的启蒙运动却是难以控制的。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新艺术形式是小说,它使读者们渴望一窥权势人物的隐秘生活。詹姆士·包斯威尔是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因为一部关于帕欧里的充满谄媚的传记而初获声名,在欧洲以及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之间广泛传播与译介。贝尔认为,在第一批现代名人之中,大众媒体造就了“马背上的那些人”。
名人们既“与我们一样”,也与我们有着显著的不同。通过军事胜利赢得的个人魅力,有时又因公众过分的奉承而增强。在生活中,华盛顿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名声,这为他的死后传奇增添了色彩。1800年,曼森·洛克·威姆斯出版了《华盛顿的一生》(Life of Washington),这部充满空想的传记持续出版了好多年。对威姆斯来说,华盛顿既是一个有普通习惯的平凡人,又是一个“半神……他是议会中的阳光,或战争中的风暴”。像拿破仑和玻利瓦尔这样的领袖则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他们希望这不仅仅为自己带来忠诚,甚至能够引发崇拜。
在科西嘉起义后,帕欧里的名声破灭了;乔治·华盛顿在他的种植园里退休;杜桑和拿破仑则死在狱中。军功式的个人魅力可能是一剂慢性毒药。领袖与人民之间亲密的,甚至有时候有些情色意味的认同,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来维持。“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府,”拿破仑说道,“需要漂亮的行动,因此需要战争。”1822年,在一个新建立的共和国长达十年的胜利之后,玻利瓦尔攀登了基多城外的钦博拉索山。据说在那里,他遇到了时间的化身。当时间指责他虚荣时,他回应道:“我高高在上,我统治地球,”他的士兵变成了“吃苦耐劳的人,而人民变得敢于行动”。拿破仑需要军队来保卫国家;玻利瓦尔放言说,国家就是军队。
民族独立是有代价的,革命年代建立的许多国家至今还在还债。对奴隶主华盛顿来说,美国白人的独立,是建立在对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奴役基础上的。在自由海地,年轻的民主受到杜桑对军队和国家近乎绝对控制的流毒侵蚀,并被国家周围的蓄奴帝国不断地威胁着。玻利瓦尔为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树立了榜样,这却给拉美几代民主国家带来了创伤。启蒙运动中关于帝国、印刷文化、技术转变以及简化官僚主义的遗产,不仅没有鼓励共同的人性,反而将革命理想主义引向了独裁堕落。

《马背上的人》言辞风趣优雅,是一个灵巧互联的传记系列。尽管贝尔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并不把18世纪的史事硬套进21世纪,但这部书似乎是在特朗普治下的残酷和愚蠢终在全球疫情之中走向终点所带来的悲哀中才最终成型。除此之外,有人将“启蒙运动”视为世俗主义和技术官僚政治的一维同义词,对此,贝尔的回应是,在革命年代,右翼的蛊惑与普世自由主义一样,都留下了鲜活的遗产。
这本书也与糟糕的当下产生了共鸣,今天的政治家都是名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塑造是一种持续的、令人沮丧的、没有报酬的劳动。公众人物从偶像崇拜快速滑向抵制。随着全球和区域的病毒检测和病例排名、医疗设备被劫持以及“受感染”的外来者受到污蔑,新冠疫情已经使公共卫生陷入危险境地。而在大背景中,世界正在加速变暖,我们正向太平洋垃圾带中扔进数以十亿记的废弃医疗口罩。
我们正处在一场危机中,它似乎足以溶解将全球和各国政治维系在一起的纽带。通过一场新的政治和解,那或许预示着一个更好的、更公平的世界。但是,即将步入19世纪的理想主义者,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如今,贝尔警告说,在许多人看来,启蒙运动是一种“将战争视为潜在再生和崇高的愿景”。在《马背上的人》中的那场危机中,快速变化世界中的矛盾和张力,使独裁者大胆起来,他们不单要获得公众的服从,更要获得他们的爱。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