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物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后殖民主义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博物馆中海量的中国藏品呢?

2020年12月4日,北京,马首铜像在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陈列展出。图为展出的马首铜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12月1日,经历了百年流离的马首铜像终于回到圆明园,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而2020年恰好是圆明园罹难160周年。历史时点的巧合使这一新闻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纷纷对文物归国表示喜悦。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马首价格的一路炒高提出质疑:1985年前后,美国加州的布莱克警察以1500美元的单价卖掉了3只被当作浴巾架的兽首铜像(虎、牛、马)。此后兽首价格飙升。2007年,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拍下马首转赠给保利博物馆。到了2008年,两只兽首拍出了2800多万欧元的天价。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曾经表示,“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看,圆明园兽首只是一般性的历史文物,它在超过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它的血缘缺少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反映的是西方写实雕塑的传统,但将其放到西方雕塑史上来论,也只能说是一般性的雕塑。”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圆明园兽首的最大价值是见证了罪恶,其中承载着民族情感。

回想2000年在香港拍卖牛头和猴头的现场,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当北京保利艺术馆顾问易苏昊想要拍下此两件兽首时,发现这里已不再是单纯的拍卖现场。场外有人高喊“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伴随“讨伐”而来的是兽首身价与日俱增,它们已势不可挡地成为多数人心中记录着屈辱历史的珍贵国宝。
显然,马首已被赋予诸多意义,不再能简单以文物本身的价值衡量,马首回归的背后也凝结了中国人对于文物的复杂情愫。那么,文物对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物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国宝是如何成为国宝的?在后殖民主义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博物馆中海量的中国藏品呢?
中国人对文物的认知在近代以来一直在发生变化。传统中国社会认为“形而下者谓之器”,并普遍将文物视为皇室的秘藏珍宝。而在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人在现代意义上认知文物的历程,从一开始就与屈辱和任人摆布的历史相连。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大批西方学者、探险家进入中国腹地进行考察和掠夺,数量巨大的文物流向海外,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也在动荡中艰难生长。考古采集品及其归属常常被赋予民族主义的意涵,文物主权的观念也日渐从学者扩展到社会各界。
博物馆被视为现代中国启蒙和富强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紫禁城从皇室宫殿向故宫博物院的转化也带来了新的公共和平等观念,这一嬗变在此后更长时间里也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回响。千禧年之后,文物归国的路程仍旧曲折,有关文物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争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日益频繁且复杂的文物交易,也为文物的归属权问题带来了更大的变数。
传统中国区分器和道,《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物在历史上往往有着特定功能,或是作为仪式礼俗上的礼器或名器而存在,或是偏重玩赏性的“古董”或“古玩”。“文物”概念是近代化的产物,在与西方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中国人加深了对自身文明的体认,西方的中国热也使得我们得以从外部视角重新欣赏传统文化,文物逐渐被视为与国家文化、命运相连的国粹。
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掠夺和破坏,十二兽首从此走向了不同命运。然而这只是开始,中华文明瑰宝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屡遭浩劫。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尽管放弃了火烧紫禁城的原计划,无价的财富还是使得紫禁城成为了侵略者的众矢之的。他们对紫禁城、圆明园、北京皇城和官署衙门等地大肆劫掠,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承认,中国文物当时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据统计,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中国馆,仅出自圆明园的文物合计就超过5万件。

远在京城两千公里之外的中国西部,局势也不太平。世纪之交,斯坦因和伯希和以低价大批打包藏经洞的珍稀文献,随后来自各国的不速之客也纷纷进入藏经洞。仅英国和法国图书馆就藏有敦煌文书共1.7万余件(约占总数的2/5),且均为精品,西北竹简、甲骨等对探究中国历史有重大价值的珍贵文物也遭此厄运。20世纪初,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频繁的文物交易,尤以卢芹斋和山中商会为甚,后者曾砍下天龙山石窟佛像佛头运出国门。
可以说,中国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文物的感知,一开始就与西方侵略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物自此有了新的象征意涵,一方面与国家悠久的历史相勾连,另一方面也与屈辱的命运暗合。无力保护古物的场景被投射放大,似乎暗示着近代中国任人摆布和掠夺的悲剧。
几乎与20世纪初西方学者大规模进入中国进行考察同期,中国考古学发端。由于当时国内缺乏人才、设备和经验进行考古挖掘和研究,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几乎是一种必然。在经历了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中国进行考古挖掘和文物交易的无序之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1917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古生物化石采集,并向当时的中国调查所递交了一份有关采集品分配的协议。双方拟定由瑞典承担全部费用和对标本的检测分析,所收集到的标本由两国平分,并规定允许采集品送至瑞典做科学研究。中方在后续的补充协议提出,这些标本需在运离两年之内归还中国。尽管协议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且在后续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落实,但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在维护文物主权上的进步。

在此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古物保存法》等法律规定,尽管并没能阻止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古收集行动,却与同时期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朴素民族主义情感一道,促成了文物主权观念向普通民众的扩展。曾经三次到中国西北考察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1926年第四次考察中国时,虽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许可,但遭到了舆论和报刊的强烈谴责,民众掀起了一场遍及南京、北京及上海的抗议活动。这一行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学界为此专门成立了反对赫定考察计划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制定了六条原则,规定采集物“绝对不得运出国外”,并将外国人在中国的随意调查、采集以及将所获材料运至国外的行为,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尽管“六条原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仍成功阻止了斯文·赫定的西北考察之行。自那之后中瑞双方签订了长达十九条的合作协议,并建立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为中外学术合作的先行者。斯文·赫定事后回忆起这次曲折的经历说,“那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标志新时代开始的、从南方席卷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潮流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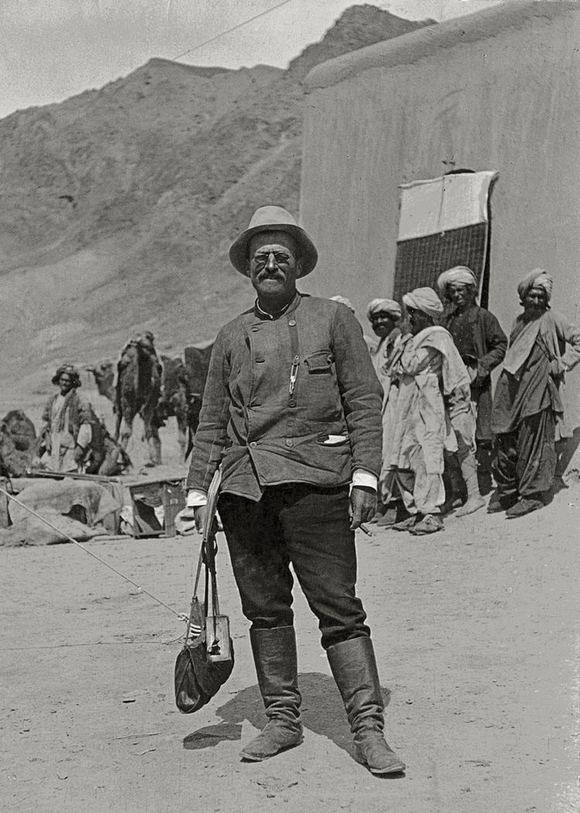
文物同国家主权的紧密关联使其成为了民族主义的载体,这也影响着人们对考古采集品的看法——希望通过文物的发掘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寻找证据,缓解几十年来抗击侵略战争中屡屡受挫的民族自信心。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西来说曾盛极一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最早提出中国文化发源于西方。晚清之时,这一说法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追捧,他们意图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同源,以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序列,为反清寻找证据。然而在1920年前后,一战打破了中国人心目中西方的良好形象,加之受五四运动影响,越来越多人开始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同时期,学术界发起古史辨运动,对古书记载的起源神话真实性提出质疑。在上述因素推动之下,学界也想要通过地下文物的发掘来证史,主动探寻中国文化的根源。
由此,中华民族起源问题已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现实际遇密切相关。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关于中国人起源的问题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在学术界,关于现代人到底是各地独立演化的多地起源还是来自非洲的单一起源的争议尚未有定论,但在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北京猿人的考古发现被放入到了早已构建好的华夏起源神话之中,成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这样的考古发现也被视为凝聚民族情感、建构国家历史和塑造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近代中国,博物馆概念的引入及相关的意义建构,为人们观看文物提供了新的视角。1860年左右,传教士将博物馆的概念传至上海,来华人士将它塑造为知识普及的象征和开启民智的手段,并极力宣扬西方优越性。出洋考察大臣曾向清帝谏言,“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张謇在参观伦敦和巴黎博览会归来之后,力倡中国开办博物馆事业,成为国人中最早提倡并实现博物馆计划者。他认为博物馆是极富时代特色、鼓吹工业文明的重要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尤其在进入民国之后,各地渐次设立博物馆,它们同图书馆、档案馆一起,被纳入到民众教育体系之中并得到行政力量的推动,成为了社会富强和文明的标志以及地方认同的纽带。
在近代博物馆的形成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故宫博物院的设立,它的出现带来了“文物为公”意识的普及。中国历代王朝有皇室收藏的传统,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但这些藏品只供皇帝一人玩赏,除少数亲近大臣之外,外人几乎不可见。王室收藏的双重性从未受到质疑——它们既是一家之私,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瑰宝。而到了共和时期,其中的张力便彰显出来。1912年清帝退位时与南京临时政府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包括有关王室的诸多临时性条款,包括“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但究竟什么是“原有之私产”?宫内艺术收藏究竟是国家宝藏还是个人私产?如何处置紫禁城内丰富的藏品,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

1924年冯玉祥以革命方式驱逐逊帝离开内廷,次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成立仪式在乾清宫正式开幕,由此,明清帝室宫苑正式成为公共博物馆,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具政治象征价值的时刻之一。学者季剑青认为,“昔日的紫禁城不再是皇帝一己之私产,而在思想和话语层面获得某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可以跨越地位和身份的差异,凝结在‘国家’这一新的观念和符号上。”类似例子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出现,由法国王宫转变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的卢浮宫便是典型。
尽管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关于如何为故宫定性、故宫与普通民众是何关系仍屡有争议,但皇室文物以及紫禁城本身的公有化进程还是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并奠定了之后一百年人们的认知。中国人逐渐形成一种观念,认为私人或外国人随意占有和买卖文物是不正当的,国宝更是不能拿来交易的。因此人们时常将曾经的文物商人如卢芹斋和山中商会等冠以“文物大盗”的恶名,也会在提起将无数文物带出宫外的溥仪时愤愤不平。
文物公有观念的背后是平等意识的勃兴。从帝制时代皇室的秘不可宣到共和时代的人人皆可进入,人们早已将博物馆视作为公共财产,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平等地共享文化遗产。近些年来与故宫相关的话题不断,《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的播出让普通人以第一人称视角,身临其境地感受故宫内部的场景,观众与故宫形成了更紧密的情感联结。这是马首归国给人们带来真实触动的原因,更是今年年初开车进故宫事件引发众怒的解释——人们害怕于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看到,在赶走了曾经的天子之后,又有新的特权阶级进入。这亦是百年前变局所留下的遗产。

正是在文物被赋予了与民族国家休戚相关的新意义的背景之下,人们才会如此渴望文物回家。然而,在后殖民主义与国家间壁垒逐渐升起的过程中,归国往往并不顺利,文物到底是民族的还是普世的,这一问题仍在争论当中。
2017年,陕西省昭陵博物馆发布《昭陵二骏中国等你回家》一文呼唤李世民陵墓六骏浮雕石刻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归国,引起广泛关注。这两块石雕曾在民国时期由卢芹斋运出国门,随后被置于宾夕凡尼亚大学博物馆。宾大博物馆馆藏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不同于其他博物馆,馆方并不讳言历史。馆长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他们从来没有进入到文物现场进行主动开掘,“所有的中国收藏都是买来的,从来没有任何宾大博物馆的人到中国取走任何文物。如果是非法买的,我们必须归还。”而当年的卢芹斋在面对盗窃、抢夺的指责之时,坚持“二骏”来自“中国高层”的首肯甚至亲自出让,买卖手续完全合法。

昭陵六骏所面临的困境也许是万千海外中国文物的缩影,通过法律手段追索文物之路漫长而艰难。国际上有关跨国文物收藏和交换的协议主要有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法律界学者认为,运用这三条法律争取权益困难重重。
首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三部国际法的效力,英、美、日、德等西方文化市场国,同时也是主要的流失文物所在国,分别对三个公约表示抵制并拒绝加入。这就意味着国际法的普世性大打折扣,对比起庞大的流失数量,个别追索的方式会耗费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成本。其次,它们的法律效力仅在该法颁布以及相关国家加入之后才产生,对于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出的二十世纪初期,国际法几乎无所作为。比如《1970年公约》主要是通过对文物来源实行控制以及限制文物的国际流转而起到预防文物流失的作用,但无法解决那些已经流失至海外并被私人占有或已成“既成事实”的文物返还问题,“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原则让文物归还难上加难,其法律效力也相当有限。根据国际习惯,归还文物仅为国际道德准则而非法律义务。
从理论层面上,人们对文物的归属问题也争议颇多。文物国家主义者认为,每一个国家、民族和群体都对其创造出的文化成果享有合法的所有权。他们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作为一种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具有文化上的含义,并将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纳入了人权范畴,认为强占其他群体文物的行为就是对该群体人权的永久侵犯。
文物的国际主义者则强调文明的普世性,认为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而不认为文物占有国有返还的义务。早在18世纪,在涉及法国是否应返还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所掠夺的文物时,法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与考古学家Quatremere de Quincy就指出:“这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整个欧洲,而不是哪一国的独有财产。”美国斯坦福大学J H Merryman曾列出利于文物的保存、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和文物的分布应均衡三原则,认为对于已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的被占文物,不应不加分析地将其一律返还来源国。

在涉及中国文物时,外国的古董商、学者和博物馆馆长分别提出过不同的理由,为在境外的中国文物进行辩护。古董商强调自己是合法购买的;学者认为将文物运到西方发达国家利于学术研究的进展,并指责过去中国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本国遗址,而这些在国外的文物在战时受到安全保护;一些博物馆馆长则提出,此举可以提升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
希腊、埃及等文明古国都曾面对过这些争议,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而其背后是某种国际秩序霸权。例如Merryman主张文物在世界各地应得到适当的分布,从而增加各国人民对本国和他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而在现实中,文物的分布极度不均衡,世界几大博物馆都设有数量众多的各国和各区域分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的遗留,众多来自世界各文明的珍宝都需要到这些西方国家才可以看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曾写作《名山》一书,追溯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背后的思想史脉络,该书扉页上写着“本书封面山西稷山县兴化寺壁画由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授权使用”,极具讽刺意味。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弥漫着富强焦虑和文明焦虑——前者是希望在物质文明上赶超西方,揖美追欧,实现现代化和强国梦;后者是希望扶起跌入谷底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尊严,追求文明复兴。
在文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两者的结合。文物在彰显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时刻想到西方侵略史的血泪与悲剧。在当下语境中,人们对归属权的讨论也时常和国家富强相联系,希望以强大的国家为后盾找回失去的文物,重拾文化自信,出现了类似“我们国家富强了,有实力争取我们曾经丢失的文物”这类论述。
而当我们过于重视文物作为国宝的意义,也可能带来一个危险的倾向——将其简化为一个符号,不再关注文物本身的价值和历史渊源。同时,文物商人也可能利用这一点过分炒高价格,反过来人为加高了文物回归的门槛。如何在关注文化瑰宝和争取文物权益的同时,不过分神化文物的意义,让文物价值回归其本身,更加理性地看待文物,是今天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矛盾的难题。
【参考文献】
张自成.《百年中国文物流失备忘录》.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
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没有一件藏品是从中国掠夺的”》,腾讯文化https://new.qq.com/omn/20181108/20181108A1071A.html
《这些年,归来的流失文物》,界面新闻
https://mp.weixin.qq.com/s/5goTZ-A_MTl79QQpWcuhYw
《老马回家,大家保持队形》,南风窗
https://mp.weixin.qq.com/s/2-u0WzDcp93ZM_QiIj8V_w
《被贩卖的中国古董:追踪近代文物流失的两大推手》,国家人文历史
https://mp.weixin.qq.com/s/7NJWPUFBuJKBTGVjfWfHRw
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近代史研究》,2013(06):62-81+160.
李建:《近代中国文物主权意识的兴起》[J].《东岳论丛》,2015,36(04):26-31;
《从清帝之禁宫到故宫博物院的转变——兼论民初国人文物公有意识的增强》,《理论学刊》,2015(05):122-128.
《民族觉醒下近代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嬗变》,《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03):60-64.
徐玲:《关乎主权:民国时期的中西文物权属之争》,《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03):3-9.
沈庆林:《对文物和文物意识的哲学思考》,《中国博物馆》,2000(01):20-24.
李飞:《旧物维新:古物观念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东南文化》,2016(03):103-109.
罗国强:《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国际法困境与出路——以“鼠首兔首拍卖案”为例》[J].法商研究,2009,26(03):19-27.
杨树明,郭东:《“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文物返还问题探析》,《现代法学》,2005(01):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