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究竟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套纸面制度?数十年来,不同的政治理论家一直在给出不同的解答。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王子琛
民主制度,正如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一般,多少被寄予了非凡的希望。尤其是当OECD国家都是发达的民主国,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对频繁的政变、军政府、衰退和失败政策时,民主被视为能够同时带来繁荣、增长、尊严和富足。
然而,人们从未对民主这一概念产生过基本的共识。民主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决定政府政策?只要每个人都有选票,是否就满足了民主的条件?如果民主不能带来良好的治理,是因为民主本身具有问题,还是因为没有实施“真正的民主”?民主制度究竟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套纸面制度?数十年来,不同的政治理论家一直在给出不同的解答。而通过对康涅狄格州一个城市的民主机制精加研究,从而提出多元民主理论的罗伯特·达尔,试图通过一本浅显易懂的小册子,来对多元民主的概念、限制和正当性给出自己的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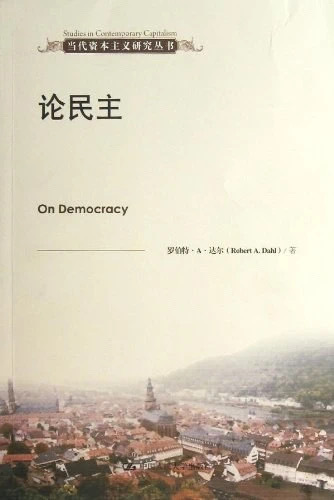
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民主也远非只有“多元民主”一种定义。不过,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多元民主的实践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并被视为唯一可行的政治制度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达尔的分析和论证,仍然不失为让我们了解民主制度的一面镜子。
相比达尔在《多元民主》中的论证,在《论民主》中,达尔将对民主的成立标准定义更进了一步,这就使得民主的所谓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之分又一次在达尔的书中得到了体现。由于达尔希望建立一个关于多元民主的规范理论,采用更多的实质标准来定义民主概念理所应当。然而,达尔的实质标准仍然缺乏一个可操作的定义。
达尔认为,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民主的体系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条件:有效的参与、选票的平等、充分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全体成年人的公民权。除了选票的平等与全体成年人的公民权外,其他所有的条件其实都需要更详细的细则加以补充,而每一条细则又都会存在大量的争议。譬如以“有效的参与”而言,达尔给出了一个机会平等式的概念,认为应保证每一个人拥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可能在客观上影响每一个人的政治参与。以美国选举中所谓的“投票压制”问题为例,许多美国南方保守州通过降低大城市的投票站数量来打击黑人等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投票率:富裕的白人可以有闲暇时间投票,但是常常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可能要通过打多份工渡日的黑人则无法承受在投票站排队数个小时的时间成本。黑人和白人确实同样有着在投票站投票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不平等。可是,如果要让这种实质性限制更加严格,是否又会过度缩小多元民主的定义范围?
类似的争议还可以在“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中出现。只要政治存在“可问责性”,那么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选民无法最终控制议程?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权力极大的时候,确实存在委员会主席可以操控政治议程的情况。而由于委员会主席是某州参议员,只需要对某州负责,因而某领域的议程便不在全体选民的控制之中。但是,委员会主席最终仍然是由多数党决定,理论上,选民可以通过迫使多数党参议员承诺置换某委员会主席的方式来控制议会议程。现实中,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因为这种选举动机可能并不强烈。那么,这究竟是议程受到了操控,还是选民其实并不注重议程的设置?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定义本身可能是不完善的。比如“充分知情”这一概念,达尔定义为每个选民都应有“平等而有效的机会了解政策及其可能的后果”。同时,达尔也承认时间因素会造成一个“合理限制”。但问题是,时间因素本身就是最大的、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卡普兰提出的“理性的无知”正是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选民会选择的一种理性行为方式,政党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捷径的方式更是应运而生。对于不同的选民来说,如何以及知道应当如何获取可靠的信息本来就具有门槛,在如今的“信息茧房”影响愈大的时候,获取信息已经不只是政治制度或公共部门的事情,甚至涉及到新媒体巨头、互联网公司等社会-经济领域。

事实上,给多元民主制定实质标准困难重重,应该承认的是,达尔的标准已经最大限度降低了实质性要求。许多民主理论家主张更能动性的、更积极的民主标准,都并未被达尔所采纳。达尔的标准实际上非常类似于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民主定义。形式理论即用规范化的数学语言表述人的效用和动机(incentive),从而分析人的行为。知名的政治学、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正是用形式理论简洁的证明了理想意义下的民主是不存在的,而达尔给出的标准,如果用相对形式化的语言表述,就是信息对称、议程设置与平等的全体参与,至少前二者是时常在博弈、信息与民主的理论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也实际上很可能是基本的多元民主所应当达到的标准。而对于后者,达尔专门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讨论,其内容容后再论。
但是,对于一本论述民主理论的规范性著作而言,使用形式上的标准来作为民主的标准可能有更多麻烦。比如经典的、普热沃尔斯基所规定的民主国家的可操作性标准会使得1990年之前的日本政权被视为威权政体。最早主张应该在经验研究中采取一种形式化的标准来判断民主政体与否的亨廷顿本身也承认,这种判断标准只是为了经验研究能够给出一个清晰可行的划分标准,从而避免争议和模糊空间。形式标准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民主政体虽然有平等公开的选举和轮替的政党制度,但却并不真正存在达尔所说的“有效参与”。政党和选民的关系往往类似于一种荫庇主义关系,亦即诺斯等学者所称的“有限准入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政党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利用族裔、阶层、文化、地域等纽带控制和组织选民,从而产生政治稳定。选民只是成为了某个政党或有限准入的团体的成员,而不是真正参与了政治决策。许多充斥着腐败、低效和暴力的民主政体,都属于此类。
论及民主政治的作用,不能不先提及对民主政治最大的批评。上承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许多论者认为民主政治与所谓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相悖,而政治家应当是“选贤举能”,以治理绩效为优先。由于人和人的能力确实是不相同的,那么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就很可能反而损害而不是增进政治绩效。
更具体的阐述,这种观点还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民主选举有可能只产生没有能力的政客,而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政治精英;其二,则是由于每一个人的政治素养和知识性经验不同,那么每一个人拥有同样的投票权或政治参与权是否可能反而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前一种观点而言,我们将留到第三部分再做探讨。而第二点,则是达尔专门花费两个章节加以探讨的问题:平等参与是否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内在的平等是达尔论述出来的第一个理由。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认可这样一个观点:人与人,无论其有哪些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从根源上而言,他们应当是平等的。但达尔自己也承认,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人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毕竟,既然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领域都需要由专业人士来主持,为什么偏偏政治就没有任何门槛?
达尔对这种观点给出了进一步的实质性反驳:首先,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专业领域,我们将许多重要决定委托给专家,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最终控制权。无论专家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最终的决策者往往还是每个人自己。同理,在政治中,选民当然可以授权有才能的人制定政策,但选民同样应当通过普遍的民主参与拥有自己的最终控制权;其次,国家政策不只是知识性的客观决策。国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调和,也许做大蛋糕只需要通过知识和才能就能实现,但是如何切分蛋糕,却涉及到不同团体之间的博弈和力量,这同样意味着,如果要公平的进行分配,就必须让每一个人拥有相同的政治话语权。此外,即便我们能够证明贤能政治是非常美好的,理想的贤能政治却未必能够用有效地制度设计出来。当我们发现,贤能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幻梦的时候,人人平等的政治参与就成为民主最重要的内在价值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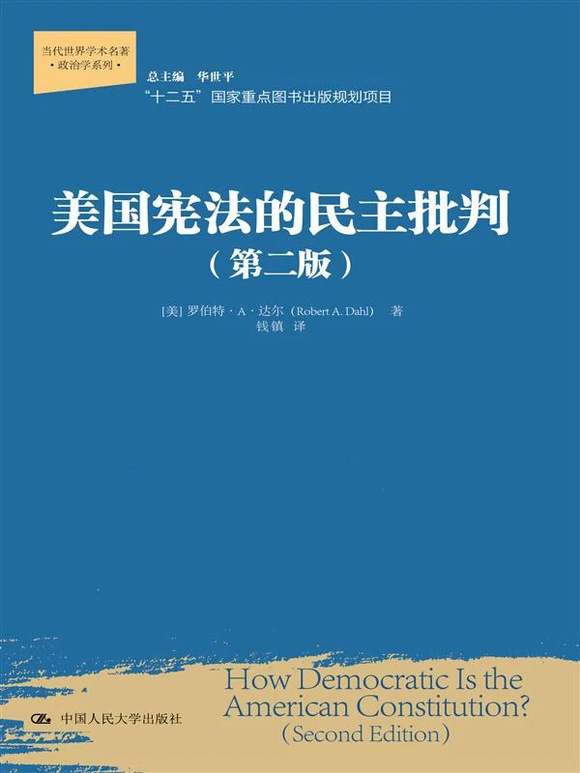
然而,最后一种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同样可能应用到达尔所言的民主政治之上。如果说现实中并不理想的“贤能政治”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成功的贤能政治,那么民主政治呢?达尔列出了八条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利处:避免暴政、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普遍自由、保证人的根本利益、使人们能够自主决定政策、为人们提供履行道德责任的机会、促进人类的发展、以及促进政治平等。除此之外,达尔相信民主还有利于谋求和平与繁荣。这其中的部分内容与达尔所归纳的民主定义相同,但还有部分则很可能受到经验证据的质疑。人们可能会指出,魏玛德国宪法和自由主义意大利王国具有相当意义的民主制度,却仍然未能避免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兴起;经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土耳其1950至1960年的“民主党”政权,最终其行政风格却日益威权化,并通过其宗教保守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世俗主义者的基本权利;甚至,在所谓的“国家性问题”(stateness)相当严重的国家内,亦即民族和族群矛盾尖锐的国家中,即便是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也无法确保政治平等,甚至无法保证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1970年代,不会被任何主流政治家认为非属民主政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展开了严酷的、镇压爱尔兰共和军的运动,其人权污点不可胜数。
繁荣与和平则更是一种猜测论点。第二波民主化潮流之后,大量亚非拉的新兴民主国家甚至没能实现政治稳定,频发的族群冲突和政治暴力最终往往导致民主制度的崩溃。更不必说“繁荣”了。这甚至导致许多新一批政治学家不再将民主与发达国家挂钩,而更关注发达国家的政治治理结构、社会制度、经济团体与权力关系等。诸如道格拉斯·诺斯就提出了所谓“准入秩序”概念,认为即便同样有着民主制的外衣,有限准入秩序的非发达民主国家和开放准入秩序的发达民主国家天壤之别。诸如梅斯奎塔之类的政治学家更进一步,直接不再强调民主的定义,而是关注“有资格选举国家执政者”和“能够决定执政者的联盟”的人数。
惨淡的现实和达尔的许诺之间自然有着巨大的鸿沟。但是,只是简单地声称这些鸿沟都来源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便很容易将有益的讨论变为无益的定义游戏。如果认为民主制度的所有缺陷都只是因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不够完美,那么至少应当讨论如何能够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完善民主体制。这,正是达尔颇费笔墨探讨的最后一部分,也正是当代民主理论中仍然保持着争议和活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前的多元民主制度远称不上完美,随着近年来的民主退潮,关于民主稳定性与民主政体下具体制度的探讨再次见诸学界。即便是与达尔的最低要求相比,许多老牌的、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也仍然存在巨大的制度改良空间。
以美国当前的民主体制为例,达尔所提的多项基本要求能否达成,仍然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话题。自从1980年代的公平报道法案被取消之后,美国媒体便不再受制于法律要求公平的报道重要政治议题,导致自由派与保守派选民只乐意观看符合自己胃口的电视节目,从中获得的信息自然大不相同,甚至不乏极端的、播放假新闻的信息来源。自从联合公民案之后,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显然恶化了这种信息扭曲的程度。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和这种信息茧房的出现极有关系。事实上,可以用具体制度来规范这种不利情况,譬如法国便规定主要电视台必须给总统候选人提供大致均等的曝光时间。除此之外,有多个欧洲国家正在计划立法对假新闻的散播进行制约。这自然引发了对于言论自由的质疑,从而也体现出达尔所提出的基本标准,事实上很可能需要更加精心的制度设计。
对议程的控制同样可能在具体制度上与平等参与相矛盾。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议会选举究竟是采用比例代表制还是采用单一选区多数制,就很可能是在上述两个原则中的两难权衡。使用单一选区多数制选举议会的国家,容易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因为这种制度会放大优势政党想席位比例。一个政党在一个选区只用获得51%的选票,就可以获得席位。极端情况下,如果选民分布非常均匀,一个政党可以获得49%的选票而在议会中没有席位。1997年英国大选中,布莱尔率领的工党便以不到45%的普选票,获得了超过60%的议会席位。这样,一个政党非常容易组建稳定的政府。但如此一来,对于受损的一方选民而言,他们的政治参与真的是足够平等的么?一个选区中的少数群体,无法获得相应比例的代表权,这显然在平等参与的原则上可以受到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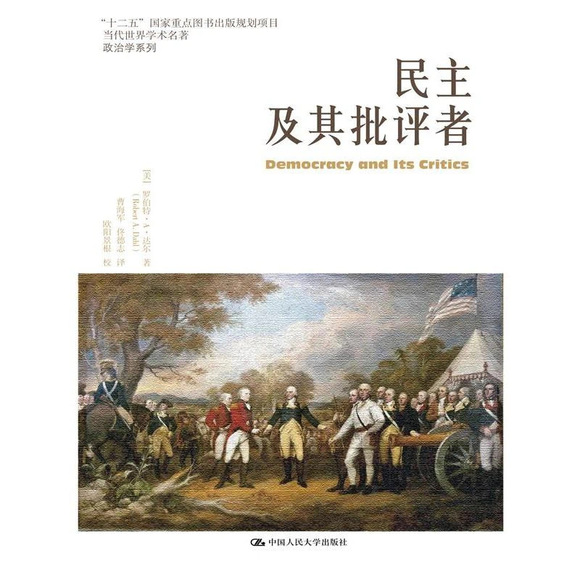
比例代表制看起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比例代表制最极端的荷兰,只需要赢得0.67%的普选票就可以在议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如此一来,即便是最小众的群体,也可以表达他们的诉求,诸如现在荷兰议会中拥有席位的主张动物保护的政党。然而,这样的制度会导致极端的多党制。荷兰议会经常有超过十个以上的政党,他们为了组阁进行博弈,则必须组建政治联盟,亦即联合组阁。联合内阁势必导致政治上的妥协和议程的重新设置,而因为这一过程在选举之后,选民无法控制,甚至无法惩罚相应的妥协行为。因为为了政治的稳定性,总是要组建一个能够运转的内阁。如此一来,事实上选民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充分知情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充分知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能够惩罚选民不满意的政党,但对于大量存在的联合政府来说,选民又如何知道一个政策为哪个党所提倡,其选票应当惩罚哪一个党呢?
最大的制度设计问题往往来自于存在严重国家性问题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存在多个族群,每一个族群彼此不认可对方主导统治的权力,甚至可能谋求民族自决。这种情况下,达尔的民主最低标准其实很可能存在问题。虽然达尔推理称每一个公民都不应当反对其他人的平等参与权力,但是对任何一个民主政体来说,政治参与的边界都是首要的问题。什么人有资格决定什么范围的事务,是一个先于平等参与的“元问题”。只要国家的边界存在,这种一部分人认为另一部分人无权决定相关领域事务的纠纷就很容易导致民主体制遇到的困境。这种国家性问题往往可以摧毁民主国家。
南斯拉夫可以被视为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知名政治学者迪蒙西·加顿·艾什曾经评价过,米洛舍维奇在2001年的倒台,更像是一个民主国家中长期执政的领袖遭到民众的厌弃,而不是一场“民主化革命”。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在塞尔维亚地区实施的是一种软性威权政治,通过骚扰反对党和媒体控制来获得不正当的优势,却并非全然的独裁。然而,在科索沃等地区,暴力升级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半民主政体国家可能出现的。事实上,从杰克·斯奈德到迈克尔·曼,都察觉到民主体制——至少是某种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的民主体制,可能成为族群冲突乃至种族清洗的温床。达尔所推崇的“多元民主”,可能无助于解决族群冲突问题。
一种被视为可能的替代方案是利普哈特提出的“共识民主”框架,而这种民主显然与达尔的定义不相符。共识民主意味着代表各个族群/社会团体的政党采用一种合作寡头式的模式执政,并采取共同一致的决策方法。荷兰、比利时,某种程度上的奥地利和瑞士都符合利普哈特所说的模型。单一的、具有组织性的大型社会团体控制了相应的选民,政党的领导人拥有远超民主体制所允许的权力,政治议程通过密室政治完成。但另一方面,协和民主似乎确实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族群冲突。曾经在战间期撕裂奥地利社会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战后和谐相处,比利时与荷兰的“支柱主义”(Pillarism)促成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和谐。
如果这种替代方案显得与民主的真谛格格不入,那么人们也还有别的制度选项,可惜同样并不完美。联邦制被视为是能够缓和族群冲突的重要制度,但联邦制仅适合那些少数族群集中分布的国家。少数族群平均分布的国家中,联邦制可能没有太大意义。除此之外,定量研究的证据并不能支持联邦制缓和族群冲突的作用。霍洛维茨提出了一种能够激励跨族裔合作的选举制度,然而这种制度的前提是族群之间本就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事实上,正如美国一些原本为了让黑人聚居区能够选出黑人议员而设置的“杰利蝾螈”选区最后成为了让政党获得不公正优势的选区一样,几乎所有的相应制度都必须做这样的取舍。
相对于尚不完美的、具体的多元民主制度,政治理论家们对民主本身有着更多的讨论,并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慎议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就是其中的代表。慎议民主的倡导者主张民主不应该通过多数决的方式实施,而应当通过民主政治的全部参与者之间的审慎讨论,来取得更具有一致性的政策。对多数民主的一大批评正是对多数人暴政的怀疑,而慎议民主可以更好地避免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慎议民主可以让人们更加热心公共事务,而不只是通过投票的方式完成政治参与。但慎议民主的反对者认为,慎议民主事实上并不能和现有的民主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区别。在现有的民主模式下,市政会议(town hall)、公民组织、游说等多种方式都可以达成一部分慎议民主的主张者所设想的效果。
对民主制度的另一种批评源于形式平等的政治参与之下所存在的实质不平等。对这一点,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伊恩·夏皮罗曾经在《民主理论的现状》中给出过自己的看法。夏皮罗认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虽然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的议题上,确实应当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话语权。具体的标准是:政策对谁的影响最大,谁的意见在该政策中最应被优先考虑。这一影响不是简单地只考虑政策的直接影响,而要考虑每一个人的“退出成本”。如果政策对一个人影响巨大,但这个人退出成本很低,那么更值得被考虑的则是受到中等程度影响,但具有很高退出成本的人。其实,这与赫希曼的观点不约而同。赫希曼曾指出“声音(voice)”与“退出(exit)”是人们表达不满的两种方式。当退出的成本高昂时,一个人的声音理当得到更多的重视。但是,这一设想同样面对着类似的诘难:这种原则无法通过客观的标准得以确立。
乃至于在民主的目的上,政治理论家们仍然有着严重的分歧。在这里我仅简述威廉·赖克的一个观点。威廉·赖克认为,民主的目的有自古以来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解读方式,其中民粹主义的解读方式认为民主就应该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达尔的定义,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温和版的这一定义)。然而,考虑到议题循环、考虑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证明,事实上加总每一个人的议题偏好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民粹主义民主理论的许诺多么美好,在逻辑上,这一理念无法实现。相反,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认为民主是监督和制衡,是能够惩罚那些为选民所厌倦和不喜的民选官员。在这一层意义上,代议制民主体系便能够满足其目的。赖克绕开对普遍民意的实现是否可欲的规范性论证,而直接以形式理论的手段在数学上否定了普遍民意的存在。作为极端的理性选择主义者,赖克的论述自然存在巨大的争议,但是这不得不给包括达尔的本作在内的大量民主理论著作,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离开具体的民主制度实践,对于民主本身,民主理论家们的争议仍然层出不穷。
在如此多的矛盾、缺陷和各有漏洞的理论之前,民主究竟是什么?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标准,还是一个值得追求但永远无法完美实现的目标?民主的定义是否只有一种?这不是达尔的著作能够回答的问题,这也不是一本关于民主的辞典,抑或标准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民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是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价值。如果要有一个切入点开始了解民主、民主理论,以及与民主制度相关的讨论,那么达尔的这本书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