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急于给女权讨论扣上“田园女权”帽子的男性正急于守住等级制中他们的特权、向上攀爬以获得更多的(性)资源,那么,恩格斯的例子则呈现出了一个人的思考是如何超越自身局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今天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上一次他的名字在社交媒体上被热议,是一位博主在微博上贴出了恩格斯关于女性大量参与公共事务才能实现男女平等的观点,随后,恩格斯的这番言论被一位男性博主讥讽为“田园女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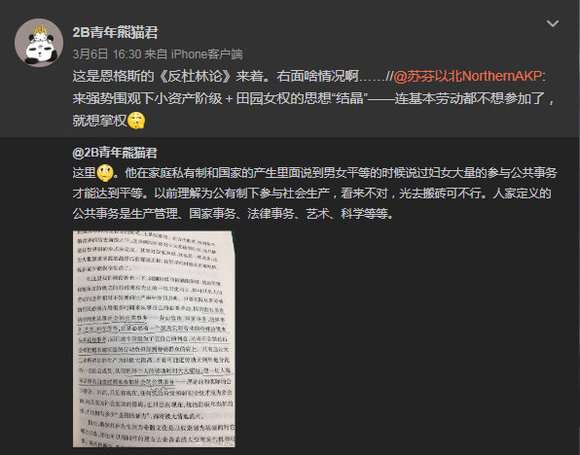
作为一名男性,恩格斯和女权有关吗?有关。他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是女权主义者常常引用的著作,他认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财产关系,女性解放才会实现。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批判和补充。随着相关理论不断完善,今天的人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实际上,女性处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桎梏之中。
那么,为什么写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典作品的恩格斯,会被今人与“田园女权”这一名词联系起来?《微博女权的前世今生:从“政治正确”到“商业正确”》一文作者李思磐看到,“田园女权”一词意味着“只要权利/权力不要义务”,这个词已成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它既承认女权运动在抽象层面的正当性,又可以被用来指责具体的女权讨论。从恩格斯的言论被斥为“田园女权”来看,很多男性并不理解或者关心真正的女权诉求意味着什么,而仅仅对女权运动之下自身优越地位的可能丧失感到担忧。在这一点上,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身为男性却在思考女性解放的恩格斯,应当成为他们的榜样。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根据巴霍芬《母权论》、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主张历史上曾经有过母权制的时期,而母权制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过程中,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私有制的产生,按照性别分工,谋取生活资料和制造生产工具是男性的工作,财产也归他们所有。而一旦财产归男子所有,就决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阶级,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恩格斯还揭示了所谓“专偶制”的虚伪。他认为,因为专偶制起源于财产关系,所以会带来男子的统治。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生育带来的是他自己的、确定继承其财产的子女。专偶制的产生是因为大量财富聚集在男子之手,所以,专偶制只是妻子方面的专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会妨碍丈夫秘密或者公开的多偶制,卖淫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成为了专偶制的补充。不仅如此,在古代公有制家庭里,男性狩猎,女性照料家庭,这时候家庭事务管理其实是公共事务;而在专偶制家庭建立以后,家务劳动就变成了私人服务,妻子变成了家庭的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恩格斯基于此提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共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
恩格斯的观点曾遭遇一些反驳,比如母权制究竟是否存在过就饱受质疑,但他对专偶制的分析依然具有现实意义。1878年出版《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认为,除了家务劳动、抚养孩子,生育也会导致女性丧失权力。激进女权主义者也对恩格斯的看法有所批判。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财产关系,婚姻自由和女性解放才会实现。这意味着性别压迫是附属于阶级压迫的,妇女被奴役就是一种阶级统治。这种看法遭到了一些反对。例如,激进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就看到,妇女遭到奴役并不能只归结于阶级统治,“这一形式是和阶级互动的,但绝非来源于阶级构成或者是其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在其他的社会形态、经济制度里,也有女性遭到奴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压迫又来自何处呢?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的政治》里首次论述了父权制的理论,“男性统治女性”正是父权制的内容之一(另一为“男性长辈统治晚辈”)。
上个世纪70年代,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一文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父权制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其中忽略了性别;激进女性主义则忽略了阶级,认为父权制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中。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彼此依赖、相互强化的。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到了她与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川副诏三的辩论,她看到,直到今天,一些男性马克思主义者还倾向于把女权主义者的斗争还原为阶级斗争。但女性的斗争,不仅仅是针对资本和国家的斗争,也是针对父权男性的斗争。上野千鹤子写道,“第一,性压迫是存在物质基础的;第二,男性劳动者从中获利;第三,他们无意放弃既得权力;第四,在历史上,男性劳动者为了守住既得权力,与资本和国家狼狈为奸并积极地排挤女性。”也正因如此,像恩格斯一样和女性并肩、共同争取人人平等的男性十分稀少。
如果说恩格斯的作品虽有一定局限、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的话,为什么在今天的中文网络上,会有人把恩格斯的观点和“田园女权”联系起来呢?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谈到:“女权意识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受害者意识,即意识到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公平,意识到自己是这种不公平的受害者。”那么,“田园女权”这一概念又是什么意思?按照“田园女权”百度条目的定义,它指的是要求男女平等却要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女权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体。李思磐看到,“中华田园女权”一词继承了之前“伪女权”和“国产女权主义”等诸多批评中的面向,意味着“只要权利/权力不要义务”。具体而言,或许我们可以参考知乎“田园女权是什么定义”的最高票回答,该回答称:“我一直鄙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还满身封建气的所谓现代女性,一边要自由恋爱,一边要婚房彩礼;一边高喊男女平等,一边又坚称男人就该养家。”并敦促女性注意,“没有承担对等的义务,何来平等的权利?”

这句话乍听似乎有理,细究起来却有很大的问题。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共谋中,究竟女性应该承担起怎样“对等的义务”呢?“一边要自由恋爱,一边要婚房彩礼”,在这样的表述中,似乎“自由恋爱”成为了一种权利,女性享受这样的权利,就应该承担起分担婚房不收彩礼的义务。婚房彩礼的存在有其经济背景,这一背景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男女之间的财富悬殊巨大。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财产归男子所有,就决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以购房为例,《剩女时代》一书作者洪理达发现,父母愿意在儿子购房时提供较大的经济资助,但是往往拒绝给女儿助一臂之力。他还引用人类学家王丹宁的研究称,由于兄弟被看作是“整个家族的后代,大家理应为其分担责任”,所以向兄弟提供经济资助的城市女性数量越来越多。“总体而言,男性经过一番周折,最终还是能拥有价值不菲的住房(只要他们有父母、女友、妻子和其他亲戚的资助),而背着买房压力的女性,拿出了不菲的钱财,到头来还没有权利在房产证写上自己的名字。”在父权制的大环境中,在经济上作为显著弱势群体的女性要求婚房彩礼,不仅常常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而且还可能导致她们最终不得不接受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
“一边高喊男女平等,一边又坚称男人就该养家”看来是双重标准,但在结构性不平等之下,又似乎没有那么匪夷所思。在市场经济中,工作赚钱“养家”占有道德高位,看似和市场无关的家务、育儿、照料等却遭到无视和贬低——正像恩格斯说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共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市场化转型之后,和再生产(包括家务、育儿、照料)有关的职能要退回社会,实际上也就是退回个人和家庭。绝大多数家庭里,再生产的责任被完全推给母亲,家庭中的女性被套上层层枷锁。《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2017No.11):女性生活蓝皮书》指出,2017年,中国家务活承担比例为妻子65%、丈夫7%、老人23%(其中很多老人也是女性),但这些劳动都被视为无偿劳动,是“二流劳动”。
而且,女性不光承担起家务、育儿等再生产活动,她们在职场上也要付出努力——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70%,居世界第一。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及对女性劳动的贬损虽然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又在相互补充。劳动力市场中,需要承担照料责任和养育子女的女性受到父权制的拖累,市场榨取了“性”这一变量,女性被看作“二流生产者”,同工不同酬从此而来。真正的双重标准是,女性被鼓励既要像女人一样在家庭中承担起无偿的再生产责任、在“爱”的关系中进行单方面的付出,又要像男人一样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这种环境下取得成就,相较于男性无疑是困难加倍。所以,上野千鹤子指出,“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女性看起来是获利了,实际上却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
虽然所谓“田园女权”并不在女权主义的主张当中,究竟有多少女性真的“受过高等教育还满身封建气”地持有类似观点也值得打上一个大问号,在恩格斯被指认为“田园女权”的事件中,我们看到它甚至可能只是男性群体的一个假想敌。但是,其看似双重标准的“诉求”,产生的土壤却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实际的社会环境。书评人维舟也在文章中提到,“田园女权”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现象,是“主流社会既要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却又不肯松手给女性赋权所造成的”。
回到被贬损为“田园女权”的恩格斯,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以及“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恩格斯想要看到的是女性大量进入生产,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这样才能够实现男女平等。而这个愿景的局限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本身,也没有看到社会对女性工作和家庭兼顾的期待,在现实中成为了所谓女性解放的桎梏。

令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感慨的是,恩格斯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却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仅如此,他是一位男性,却致力于思考女性的解放。关心女性解放的男性不只有他一位。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妇女的屈从地位》的作者,他的作品影响了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他提出,“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穆勒主张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提高妇女素质,接纳妇女进入被男子独占的所有职务和职业。他的这部著作写于1869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于1884年,同样提出女性要参加公共劳动和社会公共事务,包括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这些思想早已不是新鲜事,在今天却被部分中国男性一棒子打成“田园女权”。这又是为什么?

如界面文化作者罗广彦在《当声讨田园女权成为潮流:反女权话语背后的男性焦虑》一文中所言,反女权话语背后是对男性的优越与团结被侵蚀的忧虑。他看到,在男性对女性“没有承担对等的义务,何来平等的权利”的话语中,“义务”其实指的是女性应该扮演好女性应该扮演的角色,也就是纯真、温柔又体贴的男性附庸,所谓的“权利”就是父权给予女性的奖赏。这类男性认为,自己只要好好奋斗,按照男性群体的等级秩序,就可以获得应有的资源,其中就包括性资源。但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被视为性客体的女性实际上可能无法被他们“拥有”和“摆平”,这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够男人”。
这种焦虑情绪泛滥之下,“女权主义”一词遭到污名,而任何关于女权的讨论都有可能被扣上“田园女权”的帽子,恩格斯的言论被批“田园女权”正是其中一例。如李思磐所言,“田园女权”一词的广泛使用,在承认抽象“女权”的正当性的同时,否定具体的女权讨论和行动的“正宗性”。可实际上,女权的议题对于男性来说也是重要的。恩格斯写道:“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父权制意味着等级思维,把男女对立,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等级,就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等级对立一样。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看到,今天,人类生活的内在差异都按照等级制形式编码和符号化了——年轻人和老人、女人和男人、穷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外国人和本国人、城里人和乡下人——这个结构秩序决定了人们的地位以及这些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二元式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正是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同在的。任何人只要在这其中的一端处于弱势,就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穆勒及恩格斯能够理解,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自由和特权是建立在压迫其他人的前提之上的。如果说急于给女权讨论扣上“田园女权”帽子的男性正急于守住等级制中他们的特权、向上攀爬以获得更多的(性)资源,那么,恩格斯的例子则呈现出了一个人的思考是如何超越自身局限的。在界面文化的采访中,社会学家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说自己会把小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贴在书桌上,时刻反思自己的特权和偏见,这句话是:“只有当所有人自由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
参考资料:
你不可能只要“田园男权”,却想消灭“田园女权”https://www.sohu.com/a/416918753_481285
当声讨田园女权成为潮流:反女权话语背后的男性焦虑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219393.html
李思磐:微博女权的前世今生:从“政治正确”到“商业正确”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54160
刘莉、王宏维:重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回应麦金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批评”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NYJ200301001.htm
秦美珠: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幸福吗 ? ——关于西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反思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SJL200904005.htm
【专访】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应是集体责任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218865.html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2018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 上野千鹤子 著邹韵 薛梅 译 绿林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3
《剩女时代》[美]理达·洪·芬奇 著 李雪顺 译 鹭江出版社 2016
《何为真正生活》[法] 阿兰·巴迪欧 著 蓝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