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强制推行药品电子监管码属于行政违法,要求立即停止这一违法行为,并重新审查相关条款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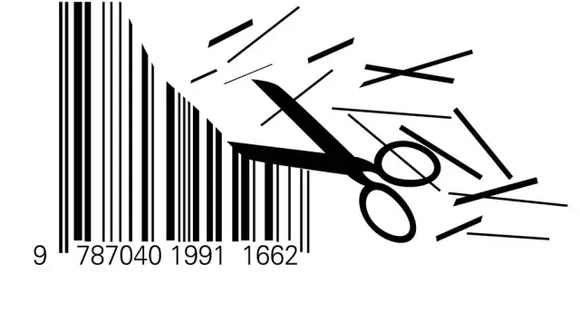
1月26日早上,一纸诉状震惊行业!
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养天和)起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强制推行药品电子监管码属于行政违法,要求立即停止这一违法行为,并重新审查相关条款的合法性。
这是极少见的“民告官”,同时也是药品电子监管码第一案。而在此之前,电子监管码一事早已引起行业及媒体关注,新康界梳理了一下此前的报道,将行业及媒体对此的观点,以及此事的发展脉落呈现。
电子监管码并不是新鲜事物。
自2006年开始实施,在2006年至2012年的6年间,国家局已分三期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疫苗、基本药物全品种纳入电子监管。不过在这之前,电子监管码仅覆盖到批发企业,未推行到零售药店和医院等药品终端。
这6年,电子监管码在生产及批发环节的推行虽并无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其合法性则从一开始就遭受质疑,2010年,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就发文追问:电子监管码合法吗?合理吗?可行吗?该谁付费呢?
在之前的6年间,电子监管码后台体系由原中信21世纪中标筹建,随着中信21世纪被阿里健康在2014年以10亿元收购后,关于电子监管码管理后台的归属问题突然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监管码推行遭遇质疑始末
2014年1月,阿里巴巴层宣布联手云锋基金,对中信集团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进行总额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37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收购后者54.3%的股份,同年10月份,中信21世纪正式发布公告称,正式更名为“阿里健康”,并更改了股票简称及公司网址。
众所周知,中信21世纪既拥有国内第一张第三方互联网售药平台资质,又掌握着中国仅有的药品监管码体系,此番转让更名,意味着阿里正式接手这两大稀缺资源。2015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宣布将转让天猫在线医药业务的运营权给予阿里健康,包括可转债完全兑换等交易完成后,阿里巴阿持有阿里健康的股份上升至约54%左右。
而阿里健康财务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收取电子监管码数据库的费用:阿里健康发布的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上半年财报显示,集团主要业务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收入同比增长14.61%至2137.1万港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6.3%上升至22.4%;
因此,媒体上对阿里健康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双重身份的质疑不断升级,并集中将矛头指向了阿里健康托管的电子监管码体系。
尤其是当国家食药监总局2015年1号文发出后,医药企业的反对声音就一浪高过一浪。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将矛头直接指向阿里健康。他公开向国家食药监总局建言,立即停止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由企业运营的做法,将系统交由国家食药监总局运营管理,在没有解决信息安全问题之前,停止强制企业向电子监管平台上传数据的做法。
2015年4月,一心堂总裁赵飚在其个人新浪博客上连发三篇文章,最后指出“药品电子监管码由阿里健康运维是个国际笑话”。他列举七大理由——“一,药品电子监管码是一个重复建设工程;二,系统运维管理的商业机制存在重大问题;三,药品电子监管码无法解决假药流通问题;四,目前的电子监管码系统存在一系列重大的漏洞与缺陷;五,没有任何有效的项目实施规划管理,项目风险极大;六,对药监部门而言这是一个玩具而非有用的工具;七,与国家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未来前景堪忧”,并直至阿里健康的裁判员与球员的双重身份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和数据安全问题,以此证明药品电子监管码从增加的社会成本,到项目的必要性,再到项目运维者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停止药品电子监管码的推行,重新思考,以找到更好的药品监管的方法。
虽然阿里健康通过其官方微博说明,自身只是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者和运营者。而数据会由食药监总局开放给医药企业,提升企业的效率,但很快又出现新的质疑声。
有业内人士就透露,电子监管码数据库已经衍生出了新的利益链条,有企业在药交会等公共场合直接表示与阿里健康大数据合作,共同开发产品服务于医药生产经营企业,而其指的大数据背后,实质指向的正是电子监管码。
而事实上,关于电子监管码数据安全的问题,在2015年初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当时有报道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2015年春节前,一个营销人员拜访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红,希望利用数据为这家上市药企设计一个市场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公司的数据啊?”看到方案,陈永红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方案所用的数据,包括各类药品的批次、流向和数量都来自众生,但陈永红却从未看过。陈永红称数据来自掌握全国药品监管信息的阿里健康,这让他担心企业的信息安全。
随后,在2015年的两场药交会上,尤其是冬天在厦门的药交会上,多个机构自称是阿里数来宝的供应商,可以利用电子监管码的数据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其中如药品流向的数据服务,可以提供细致的各种数据,包括含有各级商业名称及调拨数量的商业调拨明细。而《法制周末》的一篇相关报道中,北京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和律师表示,在医药流通企业内部,药品流向、客户名单、单位价格、销售政策往往都是作为具有竞争性的商业秘密而被采取保密措施,以显示其商业价值,药企负责销售的高管和掌握上述资料和文件的员工离职时,都要受到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的限制和约束。他还强调,药企的药品流向、销售状况等很多信息还涉及商业机密,不全是公共信息。
因此,到了2015年底,关于电子监管码推行的问题有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2016年元旦后,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健康网络媒体分会会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客座教授沈阳的《阿里和百度还玩不转大健康的十个理由》一文在朋友圈迅速传开,他在文中直指阿里健康的电子监管码系统存在漏洞与隐患。
沈阳在文中表示,首先电子监管码自CFDA成立后放成为国家标准,但目前医药企业使用的都是国际标准的商品条形码。其次,药品电子监管码数据库只是在商业流通环节、即不足35%的药品销售中启用此监管,而另外65%(医院、部队等)根本就不用药品电子监管码数据库。所以,阿里健康借此数据库向本来利润就剩下6-8%的商业流通环节收取费用,明显是不讲究社会成本、不专业地见数分帐。再次,根究调查,阿里健康母公司阿里巴巴所经营的平台网店假冒医疗器械经营事件不断曝出,却要借药品电子监控码达到中国市面流通药品的百分百正品,信服力太低。
他还指出,不少连锁药店甚至提供了怀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下属机构中有寻租问题的一些证据,并指控阿里健康因涉足大健康失败,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转型寻租。文章描述到:“近期有些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改用口头通知交费方式,向药店负责人威胁说:若不交费给阿里健康指定帐户,不是他们要下岗,就是该药店2016年的年审将通不过。这中间存在什么关系,本文暂不公布。但是,疑问很多,值得考问。而此举,显然是阿里健康找不到收费‘国际惯例’、一定会受到行业抵制。”
而针对1月26日的医药企业诉讼食药监总局一案,有业内人士直言,企业这次是真的被逼急了。
电子监管码推行过程
2006年开始实施的电子监管码到2012年还只仅限于部分药品,且未覆盖到终端。
2012年,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印发2011-2015年药品电子监管工作规划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12]64号),提出总目标:2015年年底前实现药品全品种全过程电子监管,保障药品在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的安全,最有力地打击假劣药品行为、最快捷地实现问题药品的追溯和召回、最大化地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并提出三点具体目标,包括:
(一)在当前已实施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血液制品、中药注射剂、疫苗、基本药物全品种电子监管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到其他药品制剂,实现药品电子监管的全品种覆盖;适时启动高风险医疗器械电子监管试点工作,并探索原料药实施电子监管。
(二)在当前已实现的药品生产、批发环节电子监管基础上,推广到药品零售和使用环节,从而实现覆盖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的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全过程可追溯。按照卫生部的总体部署,开展医疗机构药品电子监管工作。
(三)拓展药品电子监管系统的深度应用,充分利用药品电子监管数据,为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服务,为广大社会公众提供药品信息检索、监管码查询、真伪鉴别等服务,探索电子监管系统与医保卡系统互联互通的可行性。
2015年1月,食药监总局1号文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实施药品电子监管有关事宜的公告》发出,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对于生产企业,2015年12月31日前,境内药品制剂生产企业、进口药品制药厂商须全部纳入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以下简称入网),按照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12〕283号)的要求,完成生产线改造,在药品各级销售包装上加印(贴)统一标识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码(以下称赋码),并进行数据采集上传,通过中国药品电子监管平台核注核销。2016年1月1日后生产的药品制剂应做到全部赋码。
批发及零售等经营企业,则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前,所有企业须全部入网,严格按照新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对所经营的已赋码药品“见码必扫”,及时核注核销、上传信息,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并认真处理药品电子监管系统内预警信息。
本文来自新康界(XKJ0101)微信公众号,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