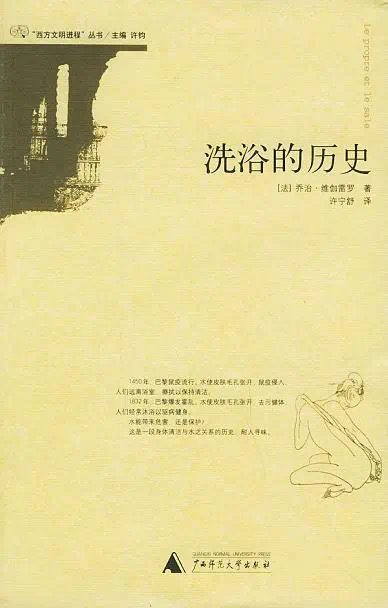我们是否可以按今天的标准,将十六、十七世纪视为一个不讲卫生、肮脏不堪的时代?

按:据说贵为君王,而且是作为十七世纪时尚风向标的君王,路易十四闻起来却臭气熏天。“路易十四一生到底洗过几次澡?”考察欧洲洗浴的历史,原来希腊、罗马人热衷洗澡,基督教传播后,洗浴就被视为一种腐化灵魂的享乐行为。十五至十七世纪,公共澡堂男女混浴带来道德堕落,瘟疫借助洗浴蔓延,澡堂因此遭到谴责并关闭,私人洗浴也因对疾病的恐惧被排斥,时人洁净的准则发生变化。有关洗浴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看起来琐细,其实正得以窥见身体的社会属性和时代、文化观念的演变。
文 | 熊芳芳(《读书》2020年10期新刊)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使得诸如吃饭、穿衣、洗浴、如厕之类的历史成为职业史家和大众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作为十七世纪欧洲最显赫的君主,路易十四是否喜欢洗澡,一生到底洗过几次澡?就曾让职业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反复纠缠、争论不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琐碎隐微,探照到日复一日、衣食住行的每个细枝末节,看似波澜不惊,但同样映射着时代的特性和文化观念的演变。

从时人记述和已有研究来看,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盛行的健康观念对洗浴确实抱有一种敌意,凡尔赛宫里专为路易十四修建的浴缸使用次数也的确有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按今天的标准,将十六、十七世纪视为一个不讲卫生、肮脏不堪的时代?这样的看法显然有些武断。现代卫生观念中所谓“洁净”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概念,不仅外表要整洁,身体本身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但这一概念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洁净观相去甚远。恰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中所言:“我们关于污垢的观念由两个方面构成:讲究卫生和尊重传统。当然,随着我们知识状态的变化,讲卫生的规则也会变化。”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这里所说的洁净和卫生都关乎身体本身。在后现代史学的阐释框架中,身体常常与政治和权力捆绑在一起。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关注的是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以此来揭示十八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化框架,他将身体更多地视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以身体史研究闻名的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则试图揭示身体的社会属性,在他看来,身体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身体的洁净,无论关注的是身体本身,还是身体外在的穿戴,即外在的物质性,首先是由社会领域来界定的,“所有外在表征施于身体的限制,勾画着身体的表象和轮廓,也揭示着它的内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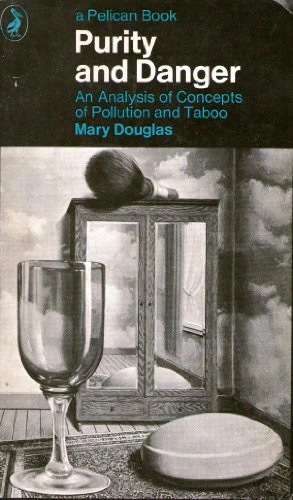
提到洁净,人们自然会想到提供洁净的水和洗浴。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洗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罗马人而言,洗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日常的娱乐和消遣,公共浴场更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场所。驻足仰望罗马城郊外卡拉卡拉浴场的断壁残垣,便足以让旅者惊叹于罗马人对洗浴的热情和执着。
洗浴也是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与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对身体的洁净本身并不是特别关心。《马可福音》(7:1—7:7)中的一段记载常被用来作为例证: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几个律法师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中有人饭前没有洗手。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若不先行洗手礼就不进食;从市上来,若不先清洁,也不进食;他们还拘守好些别的规矩:就是洗杯、水壶、烧水锅、餐桌等物。)
法利赛人和律法师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却用未清洁过的手吃饭呢?”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伪君子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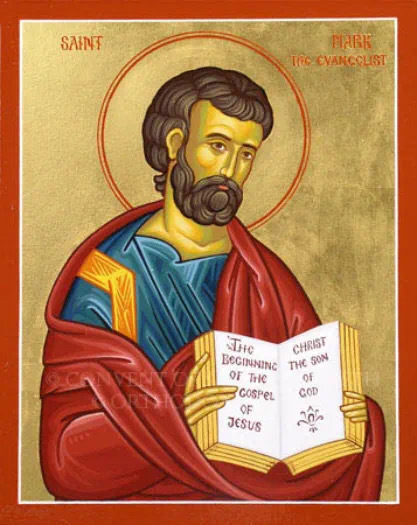
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看来,道德上有罪的人,并不能通过肉体的洗浴得到净化,忏悔才是赎罪之道。
人类学家早就指出,宗教中对圣洁和污秽的界定与世俗的洁净和肮脏并不必然对应,仪式中的洁净是一种象征性表达。世俗观念看来污秽的东西,在宗教仪式中往往被奉为圣洁,仪式性的净化与身体的洁净本身并非一回事。尽管信仰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不过基督教对灵魂的强调、对肉体的漠视很可能影响了对身体洁净的关注。从第三世纪起,基督教思想中出现了对洗浴的明确反对。洗浴被视为一种享乐行为,会激起人的欲望,是对灵魂有害的行为。四到五世纪,肮脏甚至被赋予基督教的神圣性。著名的圣徒保拉(Saint Paula,约三四七至四〇四年)是伯利恒修道院附近一所女修院的院长,她曾警告她的修女说:“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意味着一个不干净的灵魂!”一些修道院允许修士每周六洗一次以苦修为目的的冷水浴,只有生病或年纪大的人才被允许洗热水澡。
城市供水系统的中断,使得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公共浴室大都被废弃。不过在摩尔人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洗浴传统自八世纪再度复兴。这可以追溯至公元十世纪甚至更早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中,洗澡沐浴的场景多不胜数,和澡堂直接相关的故事就有好几个,如《洗染匠与剃头匠的故事》。清洁身体无疑是穆斯林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一二三六年基督徒夺取科尔多瓦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公共和私人浴室多达三百多间。也因此在中世纪很长的时间里,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都把洗浴与摩尔人的异端信仰相联系,视身体肮脏为基督徒的标志。

真正让中世纪的欧洲人再度回归浴室,享受洗浴带来的乐趣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被称为“哈马姆”(hammām)的土耳其浴室被引入欧洲。哈马姆实则受到延续自罗马的拜占庭早期洗浴文化的影响。罗马时代被废弃的浴室或温泉浴场得到重新修缮,有些改成带蒸汽浴室的哈马姆。到十三、十四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城市都建有公共浴室。一二九二年巴黎城的税册上登记有二十六个开澡堂的纳税人,店主们还组建起澡堂同业公会,与巴黎市政官员一同监管公共澡堂的经营、定价和安全性问题。图卢兹的公共浴室集中在今天加龙河边的图尼桥路上,十三世纪时这条路被称为“达尔巴德澡堂路”。十四世纪的伦敦至少有十八个公共澡堂。公共浴室在德国更是特别受欢迎,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蒸汽浴室便经由北方传入到德国。此外,私人浴室在中世纪也比较常见。考古发现证实,中世纪的主教、贵族,甚至富有的商人都会在自己的府邸中修建华丽的浴室。十三世纪意大利的医生锡耶纳的阿尔代布朗丁(Aldébrandinde Sienne)在他的医学论著中指出,无论温水洗浴还是冷水洗浴都是对健康有益的,尤其是热水浴“有助于排出大自然潜藏在人体内的污秽”。
然而,从十六世纪开始,城市中的公共澡堂逐渐消失,家庭内的私人洗浴行为也日益减少。弗朗索瓦在一五三八年下令关闭法国的澡堂;一五六六年奥尔良三级会议要求关闭法国所有的声色场所,其中也包括澡堂。第戎、博韦、安茹和桑斯的澡堂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基本都关闭了。巴黎到一六九二年还保留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公共澡堂,大多用于疾病疗养。
公共澡堂消失的原因之一在于澡堂在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中充当着破坏者的角色。中世纪的澡堂中男女混浴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上卖淫和偷情,澡堂往往被道德学家视为腐化堕落、犯罪丛生之所。在十五世纪的布道书中,澡堂和妓院、酒馆相并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鉴于此,有些城市明令公共澡堂不允许男女混浴,错开两者的开放时间。此外,澡堂是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很容易发生冲突或骚乱,使得澡堂也成为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治安的地方。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第戎城的女老板塞妮昂(Jehannotte Saignant)因经营的澡堂涉嫌投毒、组织卖淫、扰乱城市的公共秩序,于一四六六年被判处溺刑。对道德观念和城市公共秩序的强调,加上对犯罪和性病的恐惧,尤其是十六世纪梅毒在欧洲的传播,公共浴室日益受到王室和市政管理者的约束甚至禁止。
公共澡堂消失更重要的原因与瘟疫时期对“接触”可能传播疾病的恐惧有关。十四世纪黑死病的大规模肆虐过去之后,欧洲的地方性瘟疫几乎从未间断过。根据法国历史学家科斯特(Joël Coste)的统计,从中世纪晚期直到一五三六年,地方间歇性爆发的瘟疫平均每十一年出现一次,一般持续一到五年;一五三六年之后,平均每十五年出现一次。特别是巴黎和里昂这样的大城市,从十五到十七世纪瘟疫几乎接连不断。一五六二年的巴黎瘟疫死亡人数多达二万五千人。里昂作为法国南北的交通要道,在一五四四至一六四三年的一百年间至少爆发过十三次瘟疫。根据一六三一年《法兰西信使报》的报道,一六二八年里昂瘟疫仅八月到十二月间死亡人数便高达六万。
瘟疫爆发时,接触往往被视为首要威胁。为了切断瘟疫扩散的链条,禁止疫区的人与外界接触自然成为主要的防控手段。与此同时,受瘟疫之苦的城市内部也会颁布各种社会卫生限令,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还会出台有关个人卫生的“建议”,譬如取消所有的社交接触,减少可能将身体暴露于空气中的行为。出于相同的顾虑,学校、教堂、澡堂和浴室也会被关闭。早在一三四八年黑死病传到法国北部之时,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便责令巴黎大学医学院调查瘟疫散播的源头。医学院提交的策论认为受星象运行的影响,来自地表和水中带有臭味的有毒蒸汽会污染空气,通过呼吸进入人体,使人生病;其中也提到热水浴会让人身体松弛,有毒气体更容易内侵。这些看法在整个欧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瘟疫和疾病的解释还涉及当时的医学常识。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医学理论在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中被奉为经典,是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根据盖伦提倡的“体液说”,人体中包含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身体的健康与否取决于这四种体液是否平衡。在盖伦看来,瘟疫源自自然界的空气和人的身体同时失序,如果空气被恶臭所污染,那些生活不知节制致使体液失衡的人更容易受有害空气的感染而生病。一般的洗浴被认为会破坏身体的体液平衡,使人生病。
自十五世纪起,每当瘟疫爆发时,医生们便会谴责澡堂和浴室,官方则强令其关闭。这是从隔离和阻断接触的逻辑出发,不过这样的观念可能直接触及并反过来影响着人们有关身体运行机能的想象。十六、十七世纪,洗浴日渐被视为一种可能让身体虚弱、疾病内侵的不良行为。著名的王家外科医师昂布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便警告说:“应该避免去澡堂或浴室,因为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肌肉和身体是松软的,毛孔是张开的,受鼠疫污染的蒸汽会迅速侵入人的身体,甚至会使人暴毙。”各地此起彼伏的瘟疫和流行病,使得类似的观念和禁忌得以推广。十七世纪一本《瘟疫预防与治疗简论》(Bref discours de la préservation et cure de la peste)的书中写道,让身体发热,“就如同敞开门让有毒的空气一下子侵入人体内”。

随着人们对瘟疫和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水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导致家宅内的私人洗浴行为也受到排斥。甚至有人认为,抵御瘟疫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洗澡,让脏东西把毛孔覆盖起来,以免有害气体侵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身体更深层次的生物学想象,类似的观念中潜藏的不再是对人与人近距离接触的质疑,而是毛孔舒张原理背后人体与有害物质之间的接触和渗透可能带来的危害,甚至致命的危险。
鉴于洗浴有很大的风险,一种新的保持洁净的方式——“干洗”(Toilette sèche)自十六世纪逐渐成为风潮。所谓干洗就是不直接接触水,用毛巾擦拭脸部和手部。清洁身体的方式以“擦拭”为主,只要身体外露的部分显得干净即可。这样看来,说路易十四时代的人不洗澡、不爱干净似乎也没错。不过,正如维伽雷罗着意强调的,洗浴行为的消失并不等于卫生观念的退化,这种变化并非说明人们不爱干净,而是洁净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瘟疫以曲折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于身体机能的想象以及对水的恐惧,并衍生出一种新的洁净观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卫生习惯之中。到十六、十七世纪,所谓“洁净”指的是“看起来还算干净,闻起来不那么臭”,意即外表的干净。因此,洁净最直接的体现不是身体发肤本身干净与否,而是身上穿的衣物是否整洁干净。介于人体和外衣之间、紧贴皮肤的内衣由此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内衣主要指白色的衬衣。在当时人看来,“洁白的衬衣可以净化身体,去除其表面污垢,便于体内分泌物和油脂排出,附着到白衬衣上”。因此更换内衣即意味着清洁身体,内衣可以反映一个人是否注重身体卫生,换洗内衣的频率于是成为洁净与否的新标准。十六、十七世纪的死后财产清册中有关衣物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十六世纪初,贵族家庭购置衬衣的开销并不多。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和十七世纪,除王室和贵族外,富有的城市资产阶级,如高等法院的法官、医生,或是莫里哀和拉辛等享受年金的学者文人一般都会有三十来件衬衣。衬衣成了从“清洁服装”过渡到“清洁身体”有形的物化体现,这一做法实则扩大了清洁行为的实施范围,丰富了清洁卫生准则。
既然清洁行为主要通过内衣来体现,在宫廷礼仪的引导下,人们对外观的要求和标准日益提高,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内衣逐渐外露,成为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维伽雷罗在这里提到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新的洁净观念衍生出新的着装准则,在很大程度上突显出作为内衣的衬衣的重要性,从而加深了服饰的内里与外表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使得衬衣不再隐藏于长袍或外套之下,而是开始从里面显露出来,改变了十七世纪宫廷和上流社会引领的时尚潮流和服饰搭配方式。“洁净”一词的含义也因此发生变化,它与高雅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礼仪,在社会层面确立起通过身体外在的物质性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洁净和高雅、是否有教养和礼仪的新标准。

对比文艺复兴时期和十七世纪西欧的画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服饰穿搭的演变。十六世纪上半叶法国宫廷画师让·布尔迪雄(Jean Bourdichon)笔下的《大富之家》(L’homme riche ou la Noblesse)中,夫妻和一对小儿女均是长袍着身,只有丈夫的领子和袖口露出些许衬衣的影子。再看一六三三年亚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的《城市婚礼》系列,尤其是《舞会》(Le bal)一画中,衬衣的白色衣领和衣袖的蕾丝花边从男士的紧身上衣和女士的裙服中大大方方地显露出来。披肩式大翻领逐渐取代文艺复兴以来流行的波浪形轮状拉夫领或立式领,配以盖在外衣袖上的白色蕾丝袖或花边宽袍袖,成为十七世纪的流行穿戴。新的洁净标准影响的不仅仅是服饰本身,还包括身体其他部位的装扮。如头上和脸上扑香粉、佩戴香囊、熏香衣物、搽香水,这些我们曾以为主要用来遮蔽体味、愉悦自我和他人的行为,在当时实则有着更重要的清洁和防疫功能。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关注到气味在人类历史或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历史人类学家阿妮柯·勒格雷(Annick Le Guérer)在论及气味与瘟疫之间持久交织的关系时,提到法语中的“empester”一词。从词根peste(瘟疫)而言,其原意是“传播瘟疫”。不过到十六世纪,它的另一重含义更加突显出来,即“发出臭味”“使染上臭味”,后来该词的原意反而很少再用。正因为腐烂物和恶臭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疾病和瘟疫之源,在瘟疫肆虐的年代,对其源头的追溯使得气味所具有的力量在集体想象中被无限放大。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微生物学的发展和路易·巴斯德大力倡导疾病细菌说之后,我们才真正了解瘟疫的罪魁祸首原来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病菌在作祟。人类很早就认识到香料具有防腐作用,是腐烂物的克星。既然是腐烂物的臭味污染了空气,使人体生病,那么使用香料可以驱散臭味,净化污浊危险的空气,防止瘟疫传播,保护人体的健康。香料的防疫和洁净功能在十六、十七世纪被进一步强化,扑香粉、搽香水因此构成新的清洁卫生准则的一部分。
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路易十四一生只洗过一次澡的传闻其实是十九世纪君主制批评者的杜撰,为突显凡尔赛宫奢华背后的肮脏所编排的不实之词。虽然不常在凡尔赛宫的浴缸洗澡,但路易十四始终遵循十七世纪的清洁卫生准则。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以干洗的方式,用酒精或白兰地浸泡过的毛巾擦拭脸和手,一般在小起床礼时进行。打猎或者打完球回来,国王会简单洗漱一下,然后换上干净的白衬衣。他每天至少要换五次衬衣。路易十四年轻的时候常去巴黎的澡堂,一六六一年亲政后也会偶尔光临。此外,路易十四和他的祖父亨利四世一样喜欢游泳。从年轻的时候起,每到夏天他会去塞纳河游泳。侍从们会“选一处河水干净可以洗浴的地方”,在水边支上一顶帐篷,“国王可以在里面更衣”。按今天的卫生观念来看,路易十四可能确实不那么干净,但如果按近代早期的洁净标准,他无疑是那个时代讲卫生的楷模!正是路易十四的宫廷引领着当时的清洁卫生准则和服饰装扮的潮流。
在维伽雷罗看来,尽管受瘟疫的影响,十六、十七世纪用水洗浴的行为不多,但有关清洁和装扮的标准却在提高。清洁卫生观念被前所未有地社会化,通过内衣外露、服装和外表的整洁和装饰体现出来,同时也通过这一新的洁净准则确立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大规模的瘟疫在法国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加上医学知识和健康观念的发展,洗浴才以新的方式重新回归日常,不过这个过程是缓慢且渐进的。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人们才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热水浴的清洁功效,认为毛孔堵塞会影响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对身体健康有害。从清洁卫生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洁净是文明进程形塑身体感知的一种反映。这一演变过程也是对人的行为举止加以打磨,私人空间日益扩大,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的历史,同时也体现出对身体本身日益精细的关照。
洁净准则的变化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时代的观念和文化差异。十六、十七世纪与今天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在观念和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同样,中国和东亚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掩卷之余,不由得想到在这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疫情中,对于是否应佩戴口罩、是否维持原有的行为礼仪、如何实行封锁和隔离之类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即便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仍是客观且真实存在的。作为研究者也好,作为有着基本科学素养的观察者或介入者也好,或许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如何回到历史语境或进入他者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去理解这种不同于我们自身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及其缘由。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会以“了解之同情”、包容的态度看待他者,或许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最基本的素养。历史研究如此,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