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伯·福克在新作《光明的时代》中描述了14世纪奇异而又复杂的世界,我们将通过一个先锋天文学家的眼睛重温这一切。

一颗彗星划过泰恩茅斯修道院上空 图片来源:Owen Humphreys/PA
在昆汀·塔伦蒂诺1994年的电影《低俗小说》中,马瑟鲁斯·华莱士对泽德说,他要“让泽德的屁股重返中世纪”。影片并未向观众直接透露这个惩罚的具体内容。任何一位观看《低俗小说》的中世纪史学家大概都会认为,这表示泽德的屁股将获得一系列优秀的艺术作品、丰富而奇异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的发明创造、科学探索和西方哲学的奠基思想。但在广大普通观众眼里,这句话代表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是凶残野蛮、不可描述的——它指的是来自“黑暗时代”的某种惩罚手段。
在《光明的时代》(The Light Ages)一书中,作者塞伯·福克(Seb Falk)打破了很多人们对中世纪的普遍想象。他指出,一些关于科学史的记载大约始于1600年,仿佛科研就像蘑菇一样直接从地底冒了出来。但地表的蘑菇底下隐藏着更大的有机体。中世纪的科学思想也是如此,这些思想错综复杂、相互联系且涉猎广泛。中世纪的思想家总对外来思想欣然接受,他们系统地翻译了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作品,其原作者来自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波斯的多个地区。福克在书中谈到“中世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驱动力,让人去修补,去重新设计,去不断改进和升级工艺”,这句话用来描述当时的科学思想也完全成立。
这不是一个拒绝创新和盲目从众的时代,相反,新思潮会激起人们热火朝天的讨论。中世纪的思想者力图在学习更早时代的思想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东西,尽管他们对基督教创立以前时期的作者还是抱有一丝怀疑。基督教早期教父把异教徒的哲学思想比作圣经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带走的金银财物——虽然被异教玷污了,但仍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副眼镜、第一批机械钟表和第一批大学在欧洲诞生。中世纪其实根本不“黑暗”。
《光明的时代》带着读者跟随14世纪一名英格兰修道士兼先锋天文学家的脚步踏上了旅程。这位名叫约翰·韦斯特维克(John Westwyck)的修道士只留下了零星存在过的证据——几份手稿、一些释文,以及一份文件里的几笔注释引文,仅此而已。但福克选择通过他的视角想象中世纪的世界,追溯他早年间在英格兰威斯维克的赫特福德村的故事,当时这个村庄归圣奥尔本斯修道院(St Albans Abbey)所有。我们由此再度经历了他在修道院学校上学的时光和可能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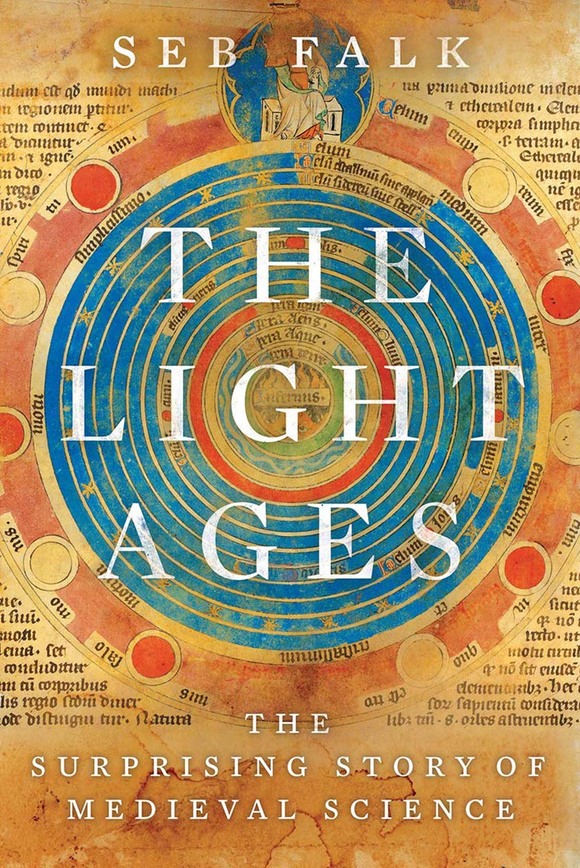
这本书有许多会让当代读者感到奇怪的内容:包括让病人用新鲜山羊肾脂肪灌肠的医学论著,以及福克对天体观测仪——一种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错综复杂的解释等等。但书中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内容。在韦斯特维克进入牛津大学之前的几年,一名天主教方济会修士抱怨,有两个修道士学生总爱饮酒作乐,一直喝到说不出话,站不起身为止。他还批评了他们对宴饮、狩猎、阅读禁书和与他人分开布道的偏好。
离开牛津大学后,韦斯特维克回到了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我们找到了他于1379年在此地誊抄的两份手稿。这两份稿子皆为前修道院院长沃林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Wallingford)撰写的关于天文仪器用途的论文。沃林福德于14世纪初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钟”,它被置于修道院教堂上方一个高高的平台上。这座钟无比精密,当它的设计者于1336年去世时,它仍处于未完工的状态。沃林福德显然是一名天赋异禀的思想家,且正好在这个权威机构中身居高位。这便触及了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在今天的我们眼中,宗教和科学二者是对立关系,但中世纪的思想家并不这么认为。福克在书中写道,对于中世纪人来说,“对世界的研究——也就是对整个宇宙的探索——是一条通往高尚情操和精神智慧的路径。”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修道士和科学家两个身份,这并不矛盾。
当韦斯特维克被派至泰恩茅斯修道院(Tynemouth Priory)时,我们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这个修道院是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位于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的一个附属修道院,它坐落在高高的岩层之上,俯瞰着北海。通过另一位修道士的记述我们得知,这个地方“汹涌的波涛日以继夜地拍打”,而且“阴沉的浓雾让人无景可观,声音嘶哑,喉咙发紧”。他还补充道:“在这里,春日的花朵被严肃取缔,夏日的温暖也被明令禁止。”乐于探索求知的韦斯特维克在此地一定特别煎熬,因为这个修道院只有“十来本书”。
后来,韦斯特维克与来自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及其附属修道院的另外六名修道士一同参加了诺维奇主教(Bishop of Norwich)的十字军征战运动。这场运动由当时的诺维奇主教亨利·德斯彭泽(Henry Dispenser)发起,此人在公关活动方面极具天赋。传教士游历全境,对资助或是加入征战的人许以天花乱坠的神灵上的好处,这吸引了各界人士报名参加。而且,经历了在泰恩茅斯的生活后,对韦斯特维克而言,杀几个人比没有夏天的日子好过多了。他于1383年5月出发。征战一开始大获成功,他们赢得了重要的战役,占领了关键的城镇,但随后军队开始遭受败绩,许多战士患上了痢疾——福克在此处向读者介绍了一系列可怕的疗法和有趣的小插曲。到了9月底,时运不济的军队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了英格兰。
经历了多灾多难的1383年,接下来十年间,任何文字记录都没有韦斯特维克的痕迹。一直到1392年,他才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所有的一家伦敦“旅店”再次出现。在牲畜横行的街道旁,他写下了自己的伟大发明“行星定位仪”(equatorium)的操作指南,这是一个用来计算行星位置的仪器。他的精确度可谓令人震惊。韦斯特维克用清晰明了、通俗易懂的英文写就了这份论述,这在当时很新鲜,因为那个时代的科学论著一般使用拉丁文写作。在论述中,他引用了杰弗雷·乔叟关于天体观测仪的论著的语句,当然,用的也是英语。他写作的同时也进行着修改:划掉了多余的词句,并附上必要的注释。这份手稿是我们了解他思想的一个窗口——他显然拥有一个乐于求知、才华横溢的头脑。此后,韦斯特维克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去世于1397年之后,具体日期无从知晓。
福克并没有仅仅把中世纪描绘成一个智慧博识的年代,他的书里还写到了当时的许多“奇思妙想”——有的作家痴迷于研究大蒜和洋葱对天然磁石的作用力;还有一位名叫埃尔默的修士从希腊神话人物代达罗斯(Daedalus)身上找到灵感,他把翅膀固定在自己的手和脚上,从马姆斯伯里修道院(Malmesbury Abbey)的一座高塔上飞跃而起。根据修道院的记录,他飞了两百英尺,然后被一阵风吹落了。他摔断了腿,成了终身残疾,但后来很长寿。正如福克在书中写道:“研究中世纪学者的谬误与他们辉煌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欣赏人类奋斗的伟大和复杂性。”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