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罗东是不断被外来政权剥削的地方,当地的人民要填饱肚子要繁荣、要现代化建设、要经济起飞,这个城市不可能像欧洲城市那样优雅地成长。”

张贵兴 图片来源:后浪
记者 |
编辑 | 黄月
张贵兴来自南洋婆罗洲,自1976年赴台湾地区读书,就定居在了台湾。但他经常会回到故乡,今年赶上了疫情,他就用谷歌街景在故乡街头散步,看看房屋有没有什么改变。“谷歌的摄影是360°的,前后左右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好像在马路上散步一样。”
今年引入简体中文版的《猴杯》是张贵兴写于二十年前的作品,讲述的故事是被开除教职的雉从台湾回到故乡马来西亚砂拉越,追踪抱着刚生下婴儿、不知去向的妹妹丽妹进入雨林,受到了当地土著达雅克人的热情款待,并与达雅克女孩亚妮妮之间产生了情感纠葛。二十年过去了,他的故乡罗东(Lutong)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新版序言里写:故乡从前鸟不生蛋,而鸟不生蛋有鸟不生蛋的好处,而现在鸟生蛋了,却也有鸟生蛋的坏处。
今年6月,《猴杯》获得了第七届联合报文学大奖,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文学评论家黄锦树将张贵兴与同为马华作家的李永平比较称,“他(张贵兴)与同样出身于婆罗洲的李永平对出生地之戒慎恐惧不同,却和出身高密东北的莫言类似,持续地淬炼一己的故乡梦土,全心全意扑向婆罗洲热带雨林。”7月,他又凭借新作《野猪渡河》摘得第八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评委之一的黄子平评价其文字“冷静、瑰丽,寓繁复于精练,不动声色地描绘血腥的杀戮场面,以暴易暴,极度挑战读者的阅读底线,建构了他在生与死、人与兽、善与恶之间,曲折迂回的历史哲学和暴力美学”。
借新书出版之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连线采访了张贵兴,从二十年前创作《猴杯》聊到晚近的《野猪渡河》。他在采访中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婆罗洲的“蛮荒”中走出,在前辈作家的激励下走向台湾文坛,却并没有一刻将家乡置于脑后。

界面文化:从20年前《猴杯》到今年的《野猪渡河》,在这之间你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吗?
张贵兴:对,已经隔了二十年了,《猴杯》里有那种雨林的、浓稠的、神秘的、意象繁复的感觉和非常华丽的书写,我知道很多人会受不了这种窒息的排山倒海的文字,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任性、一种自由驾驭文字的快感。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莎士比亚,受他老人家很大的影响,到《野猪渡河》的时候,我希望用一种精致的快节奏的语言,讲述一个以战争为背景的故事,所以叙事风格就明快很多了。
从《猴杯》到《野猪》,我认为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野猪》有非常复杂的庞大的情节去支撑小说的发展轨迹,相对而言《猴杯》的背景就简略多了,更多的是用意象和旁枝末节去烘托故事。
界面文化:《猴杯》的核心意象是猴杯,也就是猪笼草,小说里充满着热带雨林的奇花异草,这在没有去过当地的读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不光是《猴杯》,你的另一部作品《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洋公主》也是如此。对奇花异草的书写与你在婆罗洲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张贵兴:猴杯是一种肉食性的植物,固然是小说里的重要意象,其实真正的动物主角是一只婆罗洲即将绝种的犀牛,至于猪笼草和犀牛有什么指涉,就留给读者诠释了。
奇花异草当然是我非常深层的记忆,我的故乡在婆罗洲东北部,二战以前是个非常蛮荒的地方,老家的土地是英国政府殖民地赠送给我父亲的——唯一条件是开垦那块土地;当时我父母那一代,有很多人都获得了英国统治者赠送的土地。你可以想象,在那种热带的蛮荒地,植物茂盛,野兽横行,基本上是动植物的天堂,一点也不适合人类居住,华人为了生存只能努力开垦建设自己的家园。我那个地方叫罗东,这在当地土著的语言里是一种长尾猴的名字,本来就是猴子的老窝。对我来说,回忆这些动植物是非常正常、平凡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没有热带雨林的生活经验,听起来就非常陌生隔阂。
界面文化:事实上不光草木是“奇异”的,书中也有奇异的兽,有人转为兽、人兽不分的奇幻场景,尤其是妹妹带着孩子逃跑那一段,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张贵兴:你说的奇异的兽其实一点也不奇异,像是大犀牛、野猪、猴子、鳄鱼,这些都是婆罗洲土生土长的动物,进入雨林的时候随时可以目测到,当然有的动物比如犀牛被大量地屠杀,现在比较少能见到了。妹妹带着孩子逃跑这一段,是人兽不分最佳的例子,我看过一些动物,像猴子、狒狒、甚至鲸鱼,在孩子夭折后,还是会把已经死去的孩子带在身边,好像它们还是活的,直到孩子恶臭了腐烂了,才会把孩子抛弃。——动物强烈的母性有时候会超过人类,把死去的孩子带在身边,仿佛它们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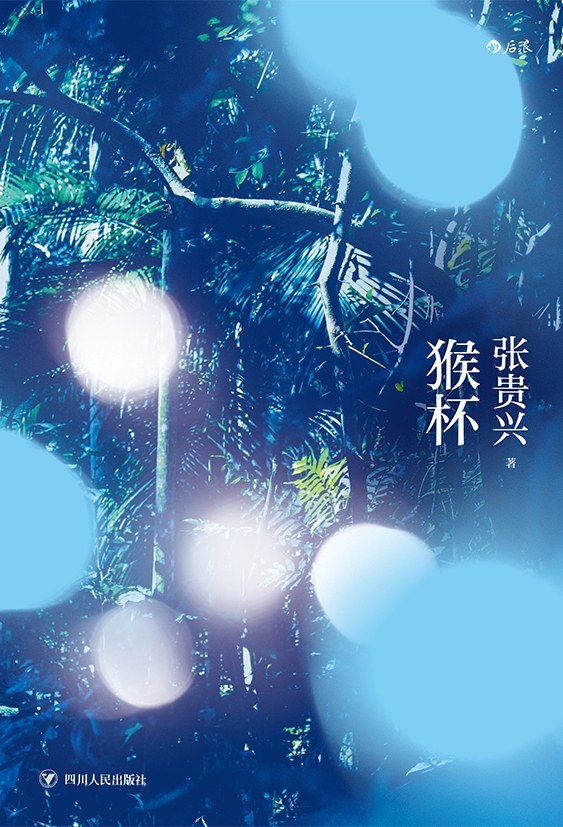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在新版《猴杯》的前言里写,故乡从前“鸟不生蛋”,而鸟不生蛋有鸟不生蛋的好处,现在生蛋了有生蛋的坏处,具体有哪些坏处,哪些又是你不能接受的?
张贵兴:坏处就是人类文明建设带来自然破坏,我不是反文明,但是我比较讨厌那种庸俗的、没有文化意涵的、粗暴的、利益至上的、掠夺式的、自私的、强暴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其实比野蛮更落后更可怕。
我知道我的故乡罗东是不断被外来政权剥削的地方,当地的人民要填饱肚子、要繁荣、要现代化建设、要经济起飞,这个城市不可能像欧洲城市那样优雅地成长。现在我的故乡虽然出现很多现代化的建设,人民的生活也更方便,但这种迅速的成长有一点像揠苗助长,太仓促了,而且没有得到人文的滋养,变成了没有血、没有肉、没有灵魂的土地。
现在故乡盖了一所大学,还盖了鳄鱼观光景点,在我那个时代绝对不可思议,咖啡厅酒店什么的都有了。我不能够接受那种仓促的畸形的成长,我情愿它回到那种蛮荒和落后的状态,至少那是充满原始生命力和爆发力的。我不是反文明,是不喜欢故乡变成现在这种非常庸俗好像土豪的样子;故乡的人也变得艳俗,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为了生活努力赚钱,先把肚子填饱再说。这同时也是很多地方要经过的过渡时期,目前这个困境还没有脱离的情形。
界面文化:那么你现在还会经常回婆罗洲吗?
张贵兴:从1976年离开到现在,我时常回去。这是我和李永平最大的不一样,李永平很少很少回去。只是我不会讲马来文,因为学校从来没有上过马来课,跟马来人接触的机会也很少,当然会讲几句简单的话,所以每次回去的时候,拿着马来西亚的护照,却讲不出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把马来西亚护照放弃了,以观光客的身份回去。
现在即使我没回去的时候,网络资讯也非常发达方便,可以看到当地的很多英文和华文报道。现在还有谷歌街景地图,有时我就看看街景图,看看故乡的道路和房子,还可以“去到”一些我都没去过的很偏僻的地方,谷歌的摄影是360°的,前后左右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就好像在马路上散步一样。这个街景图每隔三到五年就换一批,我就看看故乡都有什么变化。
界面文化: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家乡和其他地方,比如台湾地区,有所不同的?
张贵兴:很早,我念中学的时候,严格说我是从故乡的贫困和落后中逃出来的。故乡绝对不是穷山恶水,但是整天面对大自然,觉得好像永远被困在这里,感到恐慌。从中学开始,我就从杂志、报纸、电影包括琼瑶的小说里认识到台湾,加上有很多作家前辈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台湾升学,我读到作家们描写的大学生活觉得非常浪漫,比如杨牧,我看到他写的大学生活氛围非常羡慕,所以更有了离开婆罗洲的想法。我是带着仰慕朝圣的心情来到台湾的——像我们这批马华作家,不少人怀着这种朝圣的心情去台湾,那时我十九岁,是一个很纯洁的文青。
界面文化:你说的马华前辈模范作家主要都有谁?
张贵兴:林绿、陈鹏翔,还有温瑞安、商晚筠,也包括新加坡王润华和淡莹,这批作家很早去台湾,我们就陆陆续续步他们后尘,对写作有点野心抱负的都往他们(台湾)那去了。
界面文化:你进的是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那当时的文学氛围怎么样?
张贵兴:当初我进去的时候,以为英文系的文学氛围非常浓厚,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师范大学主要是培养师资的,我们不必交任何学费,宿舍也是免费,每个月还有一千多台币的补贴;大学毕业之后要去实习,大学四年,实习一年才能拿到文凭;还要再教四年的书,如果你不教书,就要把钱还给学校。
我们只有不多的文学课程和语言课程,台湾本地的大学同学都没有看过“五四”时期的作家作品,上课时老师会点名说,张贵兴介绍一下这位作家,知道多少讲多少,我很惊讶,为什么要禁“五四”作家的作品。在家乡念高中的时候,我就对文学比较有兴趣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鲁迅和钱钟书,我很喜欢《围城》,还喜欢巴金的“家春秋”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五四”作家对我而言不能说影响很大,但也是一种启蒙,因为我在蛮荒中看到华语书籍不太容易,还看了很多言情、武侠还有杂七杂八的书。台湾作家里我最喜欢的是陈映真,邮购了他早期的书,看到了《将军族》和《一件差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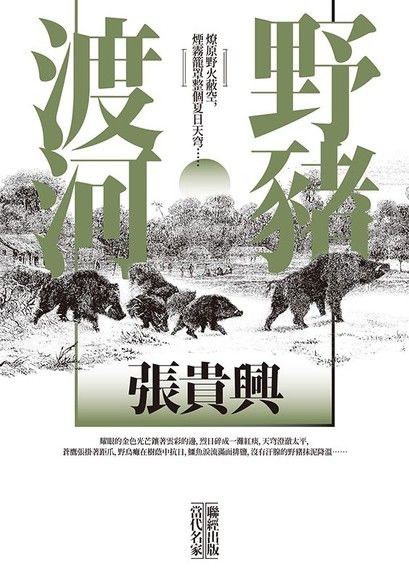
界面文化:出身于长江流域的学者朱琺重写越南汉文志怪故事,认为“荒腔走板”可能是南方文学的特性,南方书写与北方强势的儒家话语、正统的秩序不同,因此有滋生志怪的丰厚土壤,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贵兴:我们在南洋土生土长,中国?中国在我们的想象中只是一个意象、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们没有必要书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更何况再怎么写也写不过人家。在南洋土生土长,这正是我们的优势,同样,一个在中国的作家书写南洋也吃力不讨好。在我居住的婆罗洲,种族文化信仰宗教人种非常多样化,这个地方曾经是文莱领土,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来又独立。在婆罗洲曾经出现过两个华人建立的王国,一个是兰芳共和国,一个是戴燕王国,兰芳共和国名气比较大,曾想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清朝拒绝,得不到祖国的撑腰,这两个国家都被荷兰人消灭了。在南洋,被西方国家消灭的华人王国不止这两个。婆罗洲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传说,也有没有完全显露真相的历史。对小说家来说,传说和不明的历史真的太棒了,没有人知道真相正是小说家大展身手的时候,我被人家访问说得最多的是,当历史暧昧不明的时候,正是小说家进场的时刻。我很赞成朱琺的说法。
界面文化:朱琺这段话的侧重点在于,正因为受到儒家话语的干预和正统的规训更少,所以南方更具有飞扬的想象力。
张贵兴:对,事实上,以中文来说,我们没有受过很正统的中文教育,很多人对中国历史也不太了解,上学时初中念中国历史是用英文念简化的历史,什么儒家根本没有接触过,所以这种东西必然不会影响到。写婆罗洲的作家不太多,以前有李永平,后来有我,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界面文化:刚说到马华作家李永平,黄锦树认为马华作家的语言似乎停留在很陈旧的语境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贵兴:他说的也没有错,李永平1967年离开婆罗洲,离开以后就很少回去,所以书写的婆罗洲是英文时代的婆罗洲,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有浓厚的中国情怀或者“神州迷思”——他最后没有完成的一部小说是武侠小说,背景是明朝。
我认为晚期的李永平有点可惜,如果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婆罗洲,以他的才气,转变一个方向,必然可以书写更多的好作品。马华作家陈旧的中文语境,有的是不知不觉造成的,有的也是刻意造成的,他们要让自己的中文看起来更正统。李永平可能就是如此,因为他在刻意营造一种没有经过西化、翻译的中文,他想更接近他心目中的大中国。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毛病,不过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什么叫陈旧和正统。黄锦树说得没错,有的作家的确喜欢用陈旧的中文语境,因为典雅可以表现他们的笔力深厚、国学底子不同凡响。
界面文化:你离开婆罗洲来到台湾写作,从大学毕业以后发表作品成为作家,感觉台湾地区的写作环境怎么样?
张贵兴:有一点我确定,继续留在婆罗洲,我的创作会停滞不前,甚至就完蛋了,因为当地的生活环境会消灭一个人的野心和热心。但反过来说,作家是不是一定要离乡背井呢?一个不会反省、视野不够深远、创意不高的作家,即使离乡背井到火星,也可能写不出什么出色的东西。
台湾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1976年来台湾,1980年毕业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台湾地区只有2300万的人口,比广东少多了,但每个月出版那么多的书籍,不知道出版社是怎么存活的。网络时代亚马逊把书逼上绝路,乔布斯让苹果手机变成了阅读的终端机,还有谷歌把所有人类的书籍变成资料库——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出版社事业还是保持蓬勃的朝气和活力,我只能说是出版的奇迹。
在台湾写作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纯文学已经奄奄一息,所以更多作家会互相取暖打气。台湾有很多文学奖,奖金也非常丰盛,就会启发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写作。而写作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年轻作家如果获得文学奖,要知道文学奖只是开启写作的途径,不是写作的捷径。事实上台湾阅读风气也不是那么好,但出版社的文学氛围还是很好的。在台湾写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写小说,很多诗人经常抱怨诗在台湾不受重视,每年“十大好书”评选大部分都是颁给小说。当然我也替诗人觉得委屈,诗就是很受到忽略的,恐怕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