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一生亲历了雅典的霸权由盛到衰的过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给他带来深深的震撼和思考。他对人的苦难、城邦的衰变和毁灭有一种敏锐的体悟。

按:因中美争端,“修昔底德陷阱”被越来越多地讨论。但对漫长历史中“陷阱是否真实存在”这个焦点问题,并不是本文所重点考虑的,它关注的是,修昔底德所说的历史必然性从何而来。在了解了修昔底德历史写作的阶级性和党派特征,他秉持道德感的同时又对雅典霸权的非正义性深有体察之后,或许能体会他身处复杂的现实政治和剧变时代中的深层焦虑,这种焦虑、无力感,使其将战争、苦难、悲剧的发生和循环都视为人性狂妄所导致的必然。
文 | 白春晓(《读书》2020年8期新刊)
国人爱谈三国,西方人则易“言必称希腊”。他们搬出了修昔底德——“雅典人变得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于是,这也被推演为一条定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种结构性压力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对此,国内外已有诸多讨论,无需赘言。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九八八年,德裔美国古典学教授马丁·奥斯特瓦尔德就对修昔底德笔下历史中的“必然”进行过讨论。而要拿雅典和斯巴达的“段子”说“天下大势”,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乔治·马歇尔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普林斯顿为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所作的演讲。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填写的“创新之处”来评价,恐怕“陷阱”之说至少本质上算不上什么新东西。若真从学理上看,其实,这里有两条思考路径:“大势”“陷阱”是否存在,可用历史事实分析和说明;而观察者为何视其为“定数”、为“必然”,则还需考察他们的认知。那么,修昔底德为何对历史形成这种“必然性”的判断呢?下面我要提点一孔之见。

修昔底德说,他是从战争刚爆发时就开始着手写作的,并且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这意味着,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四三一年至前四〇四年)及战后一段时期他都在不断写作和修订他的文本,对其中许多语句进行反复改动,但仍然常常不能令他自己满意。加拿大的一位古典学者华莱士(W. P. Wallace)曾评论说:这种精益求精的结果使修昔底德的文字“给人一种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很强烈的压抑感”。柯林伍德更进一步地看出了问题所在:修昔底德的文风之所以这样是源于他内心有一种不安。不过,柯林伍德只将修昔底德的不安归因于其对历史规律的苦苦寻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修昔底德内心深处不安的根源。窃以为,修昔底德对人性的深刻观察是基于他自身复杂的心理体验,他独特的文风和聚焦于人类苦难的历史书写无不透露出一种内在的精神冲突。
修昔底德的心理压力和对写作的严苛态度,首先与他的出身、境遇和政治立场有关。他出身于雅典显赫的贵族家庭,并与色雷斯王室有血缘关系(他的父亲奥洛若斯很可能是色雷斯国王奥洛若斯的后裔,而雅典的重要将领米提亚德和客蒙父子也是修昔底德的先人)。他在色雷斯地区有金矿开采权,对那里的上层人士有影响力。从他的著作内容中可以断定,他受过当时极为优良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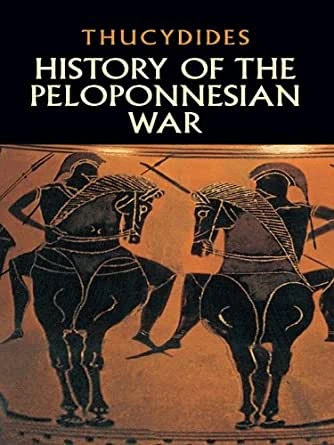
公元前四二四年,修昔底德被雅典人任命为将军,前往色雷斯地区指挥军队,驻扎在塔索斯岛。他自称,当他收到另一位驻守在安菲波利斯城内的雅典将军优克勒斯的求援后,便全力以赴驰援那里。但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抢先说服了当地人向斯巴达人投降。这导致雅典失去了安菲波利斯。虽然他保住了港口艾昂,并击退了伯拉西达军队的进攻,后来却仍然遭到了雅典人的流放,达二十年之久。
以往通常认为,修昔底德对这次战役的记述,抑制私见,叙事客观,“没有一字为个人辩护”。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修昔底德研究专家韦斯特雷克(H. D. Westlake)就称,修昔底德貌似客观的写作中有许多叙事技巧,它们被用来引导读者相信他对战败没有责任却遭到了放逐。例如,修昔底德介绍了伯拉西达部队的兵力,而对优克勒斯在安菲波利斯城内的驻军和他自己所率领的七条舰船上的兵力却未提及。这对时常关注参战人员人数的修昔底德来说是罕见的。事实上,优克勒斯的兵力很可能是少量的,根本无法坚守,处境困难。但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读者只会认定雅典人失去安菲波利斯主要是由于伯拉西达的谋略、优克勒斯的无能和安菲波利斯人的背叛,他本人则是尽力的。并且,他丝毫未解释当伯拉西达进攻安菲波利斯时,他为何不驻守在邻近的艾昂,而是在较远的塔索斯岛,以至于让伯拉西达抢先入城。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写作带有对自身军事能力辩解的特点——他要力图证明自己并非不擅长兵事,但时运不济,只得如此。因此,在他的历史书写中,时常出现人力所不能控的“运气”——这一因素往往左右着战事的变化、党派的斗争和灾难的降临。他试图将其描述为人类处境中带有规律性的状态,以此来为自身战败提供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缓解内心长期压力的途径。

不仅如此,他作为雅典瘟疫大规模流行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目睹了当时的恐怖景象,也为人们保存了一份痛苦的记忆。但是,他明知雅典瘟疫的暴发与伯里克利将阿提卡乡间的居民迁入雅典城内的政策有关,却出于对伯里克利的推崇和欣赏,在极力描绘瘟疫细节的同时,引导读者将其视为超出任何治疗和人力手段之外的“不可控因素”。他还在《雅典瘟疫叙事》之后,编排了一篇《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来为其政策辩护,将已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定性为“不幸的灾祸”,并通过伯里克利本人之口宣称雅典人因瘟疫而对其发怒是“错误的”。由此,读者很容易将他在安菲波利斯的败绩和伯里克利政策加重的疫情理解为所有算计之外的厄运所致。
而对于伯里克利之后的贵族派领袖尼西阿斯,尽管他在叙拉古的惨败是更加难以掩盖的事实,修昔底德却称赞他“整个一生都遵循着美德”。虽然他也批评尼西阿斯由于迷信月食而延误了撤退,导致雅典远征军的覆灭,但他仍对尼西阿斯抱有同情,将其视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新时代坚守传统道德的悲剧性人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政治立场相左的雅典激进民主派,笔下有时一点都不含蓄中立,而是直接表明他的厌恶之情。他将克里昂描述为“最暴戾的公民”,并称其在派罗斯的军事胜利是迫于雅典民众压力下的行动,甚至将其在安菲波利斯的阵亡也说成是“由于缺乏坚守阵地的意志,退走途中被敌人所杀”。如果联系到修昔底德本人的长期流放很可能与当时正掌权的克里昂有关,而且出身于旧贵族阶级的他对克里昂为代表的雅典“新政治家们”充满了敌视,那么他的这种“恶评”无疑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另一位激进民主派领袖徐佩波洛斯也被他称为“卑鄙的人”“将邪恶和无耻带入了城邦”,则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修昔底德并不完全反对民主政治,不过他认为只有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民主才是有序的,因为“伯里克利始终是民众的领导者,而不被民众所引导”,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而在伯里克利之后,他唯一赞赏的是公元前四一一年温和寡头派的“五千人统治”——“在他有生之年里最好的政体”。这些都不能不说与他的贵族出身和偏向雅典旧贵族集团的政治立场有关。他不支持僭主统治和专横寡头派的“四百人议事会”,更反对激进民主派的平民领袖。无论民主制或寡头制,他都赞赏稳定有序的政治状态,其实质是倾向于当时城邦内有产者们的利益。可以说,他的历史写作明确具有阶级性和党派特征(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因此,需要指出的是:修昔底德长期为自己及其党派造成的失误与失败寻找合理的记述方式和解释话语,从而造成了他的一种强迫心理,这是促使他对写作极为苛刻、屡改不停的一个原因。细致缜密而颇多暗示的叙事与精心编排、借他人之口以述己意的演说词都是在这一心理机制下完成的。
除了个人荣辱和派别利益外,雅典追求霸权并陷入失败是修昔底德长期观察与思考的对象,也是他焦虑的深层次根源。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扎戈林(Perez Zagorin)曾说:“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叙述的是有关战争的胜利、痛苦与悲剧;他的这部书或许应被命名为‘作为超级大国的雅典的伟大与衰落’。”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罗德(P. J. Rhodes)进一步指出,雅典的霸权是修昔底德笔下众多演说词的共同主题之一,这一主题是他无法摆脱的执念。一方面,他肯定伯里克利的政治才能,进而赞颂雅典人在其领导下所取得的霸权和辉煌伟业;另一方面,他既通过雅典的敌人(科林斯人),也通过雅典政治家们(伯里克利、克里昂)称,雅典人在对外进行僭主暴政般的统治,遭到其余希腊人的憎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这种霸权主义导致“大多数希腊人对雅典人的愤怒到了这种程度——有些人渴望摆脱他们的统治,而另一些人则恐惧沦入被他们统治的境地”。雅典人为了与斯巴达人争夺霸权所进行的这场战争又给希腊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并最终使雅典走向败落。罗德就推测,修昔底德时常讨论雅典的霸权是源于他对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困惑。

修昔底德的困惑主要来自对雅典霸权在正义性与持久性上的焦虑。在他笔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就镇压过纳克索斯、塔索斯和萨摩斯等盟邦的反叛。公元前四五四年后,雅典日益强迫提洛同盟内的盟邦缴纳贡赋以维持其霸权。不过,在这一时期伯里克利尚能领导雅典人对提洛同盟进行有序的治理,对萨摩斯等城邦的反叛进行必要但并不严厉的镇压(只是要求萨摩斯人拆毁城墙、提供人质、交出船只和分期赔付战争费用,并没有像后来雅典人对待密提林人和米洛斯人那样进行大批杀戮)。而在伯里克利逝世后,雅典的霸权主义更无节制,完全丧失道义感。在“米洛斯对话”中,修昔底德将当时雅典霸权的非正义性毫不隐讳地揭示出来:雅典人已完全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甚至觉得被憎恨才是力量的表现。在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中,资源、财富和权力始终对历史起推动作用,但这并不表示修昔底德对道德问题漠视。相反,在“雅典瘟疫”“克基拉内战”“密卡勒屠杀”等不少文本片段中,他都对人的恶行表示极大的关注,笔下或直接或含蓄地表示谴责。雅典霸权的扩张过程和其向非正义的蜕变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令他相当不安。可以说,修昔底德已明确意识到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但他不能对此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只能诉诸古希腊传统的悲剧意识——将雅典描述为一位有缺陷的英雄。
他一生亲历了雅典的霸权由盛到衰的过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给他带来深深的震撼和思考。他对人的苦难、城邦的衰变和毁灭有一种敏锐的体悟。他详细观察过雅典瘟疫流行时人的患病和死亡情况,又记录下雅典人在西西里远征前产生的“疾病般的爱欲”并导致最终在叙拉古的惨败。他感叹曾经辉煌并能够发动特洛伊远征的迈锡尼已沦为一个小地方,并想象过当时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与雅典分别衰败后的景象。修昔底德对雅典的霸权以及历史上所有类似的霸权都无法持久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他要从权力更替所带来的不断变化中寻求一种“不变的法则”(柯林伍德语),即一种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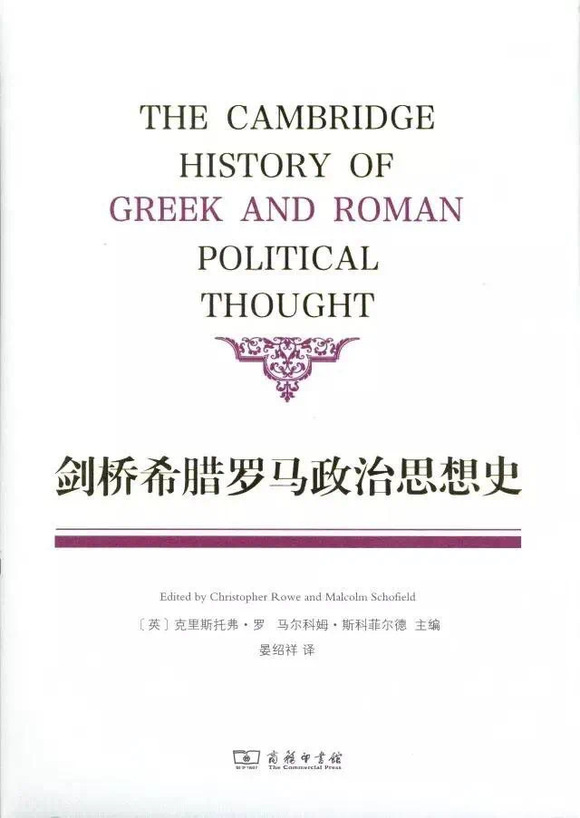
修昔底德选择的方式是历史书写。但在复杂的现实政治和纷乱的历史运动中探索正义性和持久性非但极为艰巨,还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而他又是理性主义者,正如《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上的评论——他对“梦、诸神和女性”保持着一种漠视和疏远(这一点与希罗多德非常不同)。这使他缺少普通希腊人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由焦虑逐渐变为对现实的深度失望。因此,他才会得出“战争是严酷的老师”的结论,并借伯里克利之口说出了他观察到的历史规律:所有事物(无论曾经多么成功与繁荣)本质上都是要衰落的,只能寄托于留诸后世的声名。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修昔底德是轴心时代的希腊文明中深刻感受到精神张力的代表人物之一(雅斯贝尔斯语)。他的这种内心紧张还需从文明急剧变化的角度来理解。
对于希腊人而言,公元前五世纪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公元前四九九年,爱琴海东岸的爱奥尼亚希腊人举行起义,反抗波斯。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激发了希腊人抵抗的意志。此后,波斯人发动了三次对希腊本土的入侵,均以失败告终。公元前四七九年,希腊人在成功抵御波斯大军的入侵后,波斯帝国没有再直接威胁过希腊本土。希腊,尤其是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元前四七八年,以雅典为首的爱琴海周围诸希腊城邦组成了共同抗击波斯人的提洛同盟,成员国有约两百个。而斯巴达的影响力主要在伯罗奔尼撒。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都得到进一步推动。雅典人依靠提洛同盟的贡金重建了卫城,还时常举行大型的节日庆典和赛会。伯里克利自豪地宣称:“我们整个城邦都是希腊的学校。”雅典逐渐分享了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与斯巴达扶持伯罗奔尼撒同盟城邦中的寡头派一样,雅典人扶持提洛同盟城邦内的民主派。希腊两大阵营逐渐形成。公元前四六〇年,双方发生交锋,此后时断时续的冲突延续到了公元前四四六年,史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四四六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联军侵入阿提卡,雅典被迫讲和,双方签订了“三十年和约”。和约事实上无法消除雅典和斯巴达互相的敌意。到了公元前四三〇年,希腊世界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全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十年双方互有胜负。公元前四二一年,在雅典主和派将领尼西阿斯的主持下,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和约。但到了公元前四一五年,雅典人在年轻贵族亚西比德的鼓动下,决定组织一支在希腊世界算得上空前规模的舰队去远征西西里,结果以惨败告终。斯巴达人此时却在波斯帝国的资助下建立了一支舰队。而雅典的盟邦早已不满雅典的霸权,纷纷起来反叛。西西里惨败后,雅典内部也不稳定,发生了寡头派政变。不过,战争又持续了几年。公元前四〇五年,斯巴达将领吕山德在色雷斯地区的羊河歼灭了雅典舰队。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人在海陆两方面的围困下,又失去了盟友和主要的粮食供应来源,被迫向斯巴达投降。这就是修昔底德所处的世界。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修昔底德本人体会到了多种焦虑,而且也是时代焦虑感的记录者。在他眼中,那是一个城邦之间空前的争霸时代——“从未有如此众多的城市被攻陷或荒弃”;那又是一个城邦内部剧烈斗争的时代——“所有致人死亡的形式都出现了……那还是一个新旧思想交锋、代际冲突的时代——“(远征西西里)是一件重大的事,不该由年轻人来决策和仓促处理。现在我看到这群被鼓动起来的年轻人围坐在这个人(指亚西比德)身边,我感到恐惧。我转而吁请那些长者的支持……不要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深陷到对遥远目标的痴迷之中。”
总之,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都在文明加速发展的同时陷入了深刻的紧张关系之中。血腥、悲哀和恐怖的事情不断发生。那时的希腊人普遍具有一种焦虑感,惊惧、猜忌、不安、担忧、嫉妒、暴躁等情绪弥漫于他们的世界。而这种情绪在雅典人中间最为明显——他们在追求荣耀和霸权的心态下,狂妄不断升级,最终遭受到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修昔底德选择当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叙事主题,因为他意识到这是希腊世界由兴盛转向衰败的大悲剧。而同一时期的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和智术师们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这一时代的精神困境。

关键之处在于修昔底德将这种时代现象看作永恒,将变化无定的“运气”归入“必然”之中,将苦难视为宿命:
只要人的本性不变,这些苦难就会发生并且将来还是如此,虽然程度上或深或浅,形式上也会有差异——正如每一个机缘变化所显现的那样。
因此,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将来会以类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发生。这就意味着,无法医治的瘟疫总要降临,蛊惑、煽动的政客总要出场,获得了财富和资源的城邦总要追求扩张、称霸,带来众多人口死亡的战争总要爆发。既然悲剧总是要发生的,运气好不好都只是暂时的。不过,英雄还是要尽力奋斗一场,比如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而这个过程还是值得记录下来并传之后世的,比如他本人的历史书写。于是,修昔底德用这种方式试图建构起一种“必然性”,来为他自己、他的党派和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找到一种有效的说明。
但是,“现时的辉煌与传至未来的声名”是否真的能成为“永久的记忆”呢?他的著作是否就因此成为“永恒的财富”呢?越到后来,他似乎越没那么自信。美国的一位古典学者弗洛里(Stewart Flory)就大胆猜测过:修昔底德由于在战争中看到了太多非理性的事情,而对自己在著作中一开始宣称的历史有用性产生了怀疑,最终放弃了写作,留下一部未完稿。我觉得,无论是否如此,感受到“必然”之后的焦虑感应该比直接接受“必然”所推导出的那个“陷阱”有更大的益处。既然把人推到“陷阱”里的是“狂妄”,那么人若悠着点儿或许还不至于跌入那个坑中。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