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挑战了禁忌,却也由禁忌催生。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这年头上网发言,总要担点被人抬杠的风险,既没有道理可讲,又不敢开口大骂,怕落下个“不文明”“没形象”的把柄。不过最近,诗人余秀华的微博成了一本“脏话反杠指南”。8月14日,余秀华在微博上写了一段向歌手李健表达爱慕的文字,不出所料,很快就有好为人师的网友批评此举是对别人的“打扰”,“喜欢可以放在心里”。与大部分公众人物的隐忍沉默不同,余秀华迅速以脏话回击,在受到“公众人物怎么不讲文明”的指责和“封博”警告后,更是愈骂愈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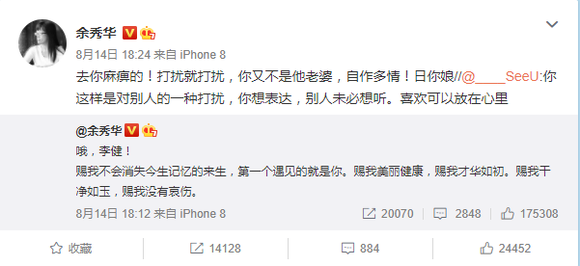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脏话。一百年前,鲁迅就曾写道:“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但不论是一百年前还是现在,脏话因其粗鄙下流,一直被视为透明的禁忌:我们不能把脏话拿到明面上讲,不能公开严肃地讨论脏话,虽然脏话无处不在。
人为什么会说脏话?脏话为什么总是牵扯到性?“国骂”为什么要骂娘?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使用脏话的频率真的天差地别吗?脏话的形成和延续绝非“约定俗成”那么简单,口出脏话,也不一定是所谓的“教养”“素质”问题。鲁迅在《论“他妈的!”》中提出,问候祖宗十八代,是庶民对“祖宗余荫”和“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反抗,这与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在《脏话文化史》中对脏话与社会禁忌关系的研究遥相呼应,两人对不同情境下脏话用途和具体含义的细分也有相似之处。
借用以上二者的研究,本文尝试将脏话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这并不是要为脏话“正名”,而是为了正视脏话以及脏话所折射的现实。鲁迅既认为“他妈的”是一种反抗,同时又警惕其卑劣,韦津利虽然对非诅咒性的脏话持较为轻松的态度,但她也犀利地批判了脏话系统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下流化。
即便是在学术领域,如果有人宣称自己要对脏话进行深入严肃的研究,这人听起来可能就不那么正经,借用文学批评家黄子平对鲁迅脏话研究的形容,这叫“学匪派”的思维方式。许多人认为,骂脏话是一种下流的直觉,它虽然难听,却翻不出什么新意。比如那个在英文中以F开头的动词,环球同此一骂,可见脏话不但粗鄙,还很呆板。就连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也认为,脏话咒骂是“最约定俗成、照章应卯的行为”,对社会研究而言,这种“套用公式”的行为没有任何价值。
露丝·韦津利为脏话著书立说,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她看来,骂脏话能够精准地达成意义,绝非套用公式,说出一个约定俗成的脏话词汇那么简单。同一个脏话词汇可以表达多种意思,造成不一样的效果。要分析人们骂脏话的动机和后果,需要把口语行为放置到特定的环境下去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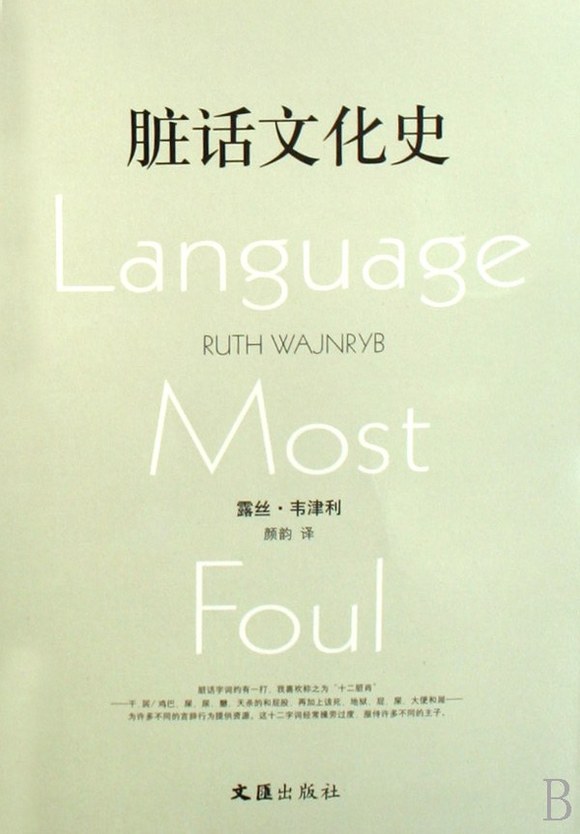
我们可以用鲁迅所说的国骂来想象以下三个场景:第一,某人不小心撞在了电线杆上,低声咒念一遍国骂,很显然,这句脏话不是针对任何人言说的,韦津利称之为清涤型咒骂,意在宣泄情绪、释放压力;第二,两个朋友到了约定的地点,招呼一句“哟,你来啦”,并在其中悠悠插入一句国骂,按鲁迅的观察,这是以脏话进行社交,效果几同于“亲爱的”;第三,如果两个人发生争执,当街怒喝一声国骂,并质问对方想做什么,这无疑就是恶言型咒骂了。
尽管脏话不雅甚至恶俗,但若认为所有的脏话行为都是冒犯性的攻击和诅咒,与实际状况不符。对有些人而言,“适当的”脏话不但没有损害人际关系,还是对相熟程度的一种确认,它可以软化气氛,消解礼貌所制造的距离感。在清涤型咒骂中,真正产生作用的是言说行为,脏话就像叹词一样没有语义。人们选择使用脏话,是因为其情感强度可能比一般词语更高,可以更有效地排遣压力、愤怒和焦虑。
韦津利引用的一则漫画很好地解释了脏话情感强度的来源。画中,一位老太太俯身询问小男孩为什么哭泣,男孩回答道:“因为我年纪不够大,还不能咒骂。”哭泣是人类情绪涌动,暂时溢出自我边界的表现。当社会把某些词视为禁忌时,这些词也就拥有了禁忌的象征力量,从而获得更高的情感强度,用于展现或者制造边界的破裂和摩擦。画中的小男孩认为,同样是说话,但只有说脏话才能代替哭,正是这个缘故。恶言咒骂也是利用脏话的象征力量来挑战听者。
虽然余秀华在微博上的脏话是针对特定的人而言,但它和纯恶意的咒骂仍有差别。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认为,有些恶言咒骂其实更倾向于清涤咒骂,只是有“倒霉的听众”恰好承受了怒火而已。被余秀华脏话辱骂的网友当然不是无辜的倒霉蛋,但她的回击的确起到了清涤作用,宣泄了自己因受无端说教产生的怒火。更有趣的是,对于许多旁观听众而言,余秀华的脏话有力地钳制了“键盘侠”,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快感。但细想之下也令人沮丧:网络世界越来越不重视说理,“杠精”已经掌握了一套温良恭俭的语言四处指点江山,除了看余秀华破口大骂,我们竟毫无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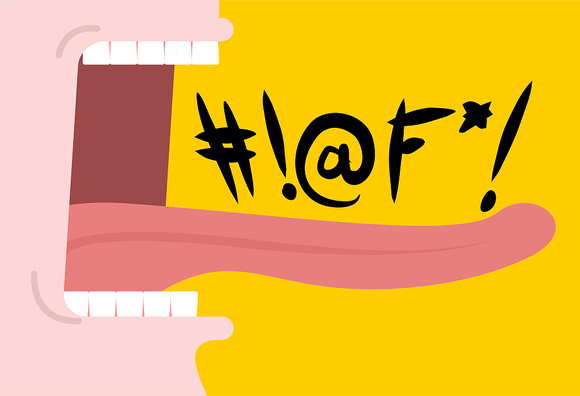
“一饭三遗矢”,赵王使者虽然没有直接用“屎”来骂廉颇,但读来也颇有侮辱性意味了——不光暗讽其年老无能,还特地挑选了排泄活动作为例证。排泄在许多文化里都是惹人厌恶的话题,我们在史书上读不到以“屎”骂人,所见的不过“竖子”“死公”“老狗”尔尔,大抵如鲁迅语,“士大夫讳而不录。”
讳而不录,是为了净化的缘故。但士大夫们或许不曾想见,禁忌的力量把他们眼中的肮脏之物捧成了伊甸园里的苹果,越是禁忌,就越有吸引力。唯一不同的是,排泄物本没有苹果那样的魔力,它能促成挑战社会权威的离经叛道,完全是“士大夫讳而不录”的结果。一出口又是大忌,想把嘴牢牢堵上,却发现它比以往更蓬勃。如此往复循环,排泄物就成了天生的脏话。脏话里多用性与性器官,也是如此。
文化观念上的禁忌可以解释上述现象,但父母祖宗既不污秽,又没有人“谈之而色变”,何以成为国骂中的关键呢?
禁忌的力量,不单来自权威不允许做什么,还来自权威本身。没有什么比“上帝”“耶稣”更洁净的了,但在英文中,这些神圣的词却频频作为渎神的咒骂之语出现。韦津利注意到,许多宗教都曾尝试禁止使用神明之名,犹太教将上帝之名写作没有元音的YHVH,没有任何人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发音,圣经十诫里也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上帝是宗教权威最核心的象征,为了绕开这个过于强大的禁忌,人们发明了许多意指上帝的委婉语(例如golly、gosh),这些词语却纷纷沦为情绪性的脏话,直至“上帝”“耶稣”也成为人们撞在电线杆上时最寻常的一句咒骂。

国骂的历史究竟如何,由于“士大夫讳而不录”,今人已不可得知,但总还有些许线索。《广弘明集》里有一段对话,“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论妇人不可保其贞洁、败坏血统正宗,谓人“何必姓王”,用下流话来说,就是骂人“孙子”,自称“爷爷”“祖宗”,高呼国骂。鲁迅以为,晋代以降,门第垄断社会,“祖宗”是高门子弟的唯一护符,“‘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摆倒了”,以血统来攻击高门贵胄,战略上“可谓奇谲”。即使是门阀衰落后,家世宗族在中国社会文化里仍然是权威的重要来源,用国骂攻击门楣的人,一朝得势,也要寻一个名臣雅士做先祖,修家谱,扮演新的“门第”。因而到了现在,国骂也依旧流行得很。
虽然如鲁迅所言,国骂博大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不专以“妈”为限,但为什么“妈”“姥姥”和“奶奶”更为常见?人们会骂“狗娘养的”,却没听过“狗爹养的”。一种解释大约如邢子才所讲的“妇人不可保”,认为女性可以在受孕一事上欺骗男性,对于父系社会来讲,女人不贞会导致家庭财产、权力的流失,要用血统正宗来攻击人,自然是从女性下手更容易。辱人母亲,就是当了别人的祖宗,把自己供在了别人家的香台上。
男人畏惧女人的性能力,所以要通过咒骂加以诋毁压制,听起来倒像是父权吃了亏,愤起反抗。韦津利讲了一个笑话:“公狗为什么舔自己的卵蛋?因为它舔得到。”
骂脏话近乎于特权,又是一种自我堕落。社会对男性和年长者骂脏话的容忍度更高,但无论男女,口出脏话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下等”。人们把底层社会身份同“下等”联系在一起,故而觉得工人农民说脏话是常理,受过教育的人说脏话就是自甘堕落。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里口出秽语,人们非但没有感到冒犯,反而夸他率性可爱,大概因为这本日记出版时,季羡林已经是个颇具声望的老人。如果在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给人看到这么多国骂,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讲他“有辱斯文”,配不上清华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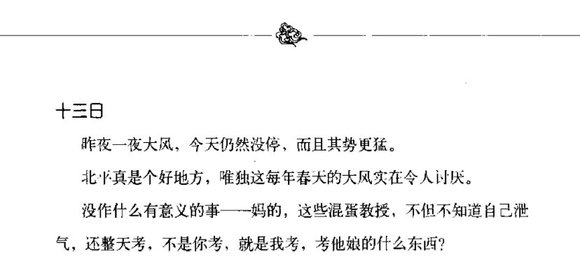
余秀华的脏话之所以有力,除了她对脏话语言的巧妙运用,还部分得益于她的女诗人身份。“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余秀华诗歌最初的走红,便是与中国诗歌传统中女性典雅、矜持形象的决裂。她出身农村,身有残疾,本就颠覆了人们的“才女”想象,在成为诗人后,又把某些人眼中“下等人的粗鄙”带到了诗歌的神圣殿堂。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与强调个人角色的社会相比,地位角色型社会更倾向于要求每个人依照地位角色要求来行动,维护纪律和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不管人们私下如何,面向公众时,脏话作为异端总要受到严格的把控,女诗人就应该表现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涵养,以及作为女性的端庄。但余秀华诗歌中赤裸的情欲、社交媒体上肆意的脏话持续违反着社会对这两个角色的既定期待,她通过触犯禁忌而身获禁忌力量的加持。
女性在社交媒体公开使用侮辱女性的脏话,以一种尴尬的方式打破了男性咒骂的特权。一些女性主义者主张,这种“夺回”可以通过误用、扭曲原意的方式抵消“丑恶事物的女性化”。Vittu在芬兰语中是个意指女性外阴的古老词汇,一些年长的人听到它仍然觉得是句咒骂,但在年轻人之间,vittu已经衍生用于称呼“烦躁”“不友好”或者表示惊叹的意思。“酷儿”(queer)一词原本有恐同的含义,但现在已被许多同性恋者用以自称,人们很少由这个词联想到恐同。
在中文里,两性生殖器用作名词性脏话时,似乎也有类于vittu的趋势,国骂的频繁使用也降低了它所能造成的震惊程度。不过,夺回式的误用是否真的能抵消这些脏话的恶意,值得怀疑。鲁迅在写《论“他妈的!”》时,终于还是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恐怕不只是“到底未曾拉过车”“有点贵族气”的缘故。任何人听来,原汁原味的国骂都十分恶毒。发明国骂的人是天才,却是个“卑劣的天才”(鲁迅语)。今日的世界还有无数的“等”,有阶级的“等”,有性别的“等”。倘使如鲁迅所言,有声和无声的国骂环绕四周,“还须在太平的时候”,那么不太平的时候,又是什么光景呢?
参考资料:
《脏话文化史》 露丝·韦津利 文汇出版社 2008-2
《论“他妈的!”》 鲁迅
《鲁迅的文化研究》 黄子平
https://mp.weixin.qq.com/s/1ARQ_osRWWPngXbYrx6zjg
《大胆示爱的余秀华,才是互联网的真朋克》
https://mp.weixin.qq.com/s/Gs6dd0UyD_Kn_d-JHsau2A
《余秀华的脏话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