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在指责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保守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保守主义回潮的因和果究竟是什么。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来源:图虫
记者 |
编辑 | 黄月
经典文艺作品遭到意义解构,被人以令人大跌眼镜的方式重新评判,成为了近年来屡屡在中文互联网内出现的怪现状。两则最新案例日前被网友发现并引发了新一轮热议。@WeLens 发布了一组抖音上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论截图,评论纷纷表示马文才才是那个应该嫁的对象,“祝英台和马文才是有婚约的”“小时候觉得马文才很坏,现在才发现马文才才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我喜欢马文才有钱有势最重要他爱我”。无独有偶,有豆瓣网友也在电视剧《红楼梦》的弹幕中看到了这样的评论——“宝玉应该努力仕途经济才能保护女孩子们。”
与此同时,通过女团节目《青春有你2》出圈的网红林小宅爆出与一个男生的亲密照,因她之前刚宣布跟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众多网友讥讽其“无缝恋爱”,怀疑她“劈腿出轨”。从祝英台应该嫁马文才、宝玉应该努力仕途经济到女明星被指“无缝恋爱”,这些评论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道德之网,其重重审判同时指向虚构和真实的两个世界。

平等个体之间的真挚感情能够超越金钱、家庭、权力等一切外在桎梏——这一长久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现代爱情观,在当下似乎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嘲讽。社交网络和视频网站评论区里的质疑者,以一套前启蒙时代的、浸淫着父权价值观的话语,挥舞起了道德裁判的大旗。年轻一代因此被指责太过保守,甚至有博主形容其为“数码牌坊,赛博猪笼,电子裹脚布”。
由于缺乏系统性分析,指向所谓“年轻人”的责备其实太过泛泛,我们还很难确定发表保守言论的网友的真实年龄分布。但网络舆论无疑正呈现出越来越保守的态势,在这一令人惊讶的趋势背后,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心理的某种重要变化。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试图分析浪漫小说/言情小说叙事的泛化,指出女性欲望、父权制和通俗文学之间的勾连;在第二部分,我们尝试将私人领域道德化的趋势,置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婚恋焦虑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收紧的大背景下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封建礼教’在过去是个贬义词,现在则是一部分网友要主动遵守的。”自媒体人萝贝贝如此感叹当下的网络环境。包括她在内的许多评论者都发现,异性恋关系的道德正当性成为了当下不少中国观众评判文艺作品的唯一尺度。他们的评判标准一方面极端理想化(强调“一生一世一双人”,男女双方都不得有任何感情瑕疵),另一方面又极端现实(对物质基础、尊卑秩序的无限强调)。这一评判标准制造了无数“弹幕三观警察”——有人指出《大宅门》中的杨九红是痴心妄想进入白家的无良妓女,《橘子红了》中的秀禾与老爷的弟弟相恋是不知廉耻的渣男渣女,《泰坦尼克号》和《乱世佳人》都是小三偷情的故事……
这种对异性恋关系既理想又现实的矛盾想象,与一种类型文学传递的情感结构与价值取向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浪漫小说。在中国的语境里,浪漫小说以“言情小说”之名成为了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百年现代史的背景下,言情小说及其爱情观曾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建立现代公民主体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斯坦福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李海燕所指出的:随着20世纪初浪漫主义自由恋爱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输入,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大行其道;在五四知识分子将“爱情”视作自由、独立、平等的象征后,浪漫爱情更是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中同等、公平的公民身份紧密捆绑,与儒家社会的等级秩序、人际关系和封建礼教形成鲜明对比。现代中国“浪漫爱情”之概念的形成,因此被打上了现代化和启蒙主义的烙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统摄公共和私人生活,再度压抑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追求。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开启、国家开始从私人生活中逐渐退场,那些曾经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不可抑制地喷薄而出,再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在中国图书市场风靡一时,她在作品中宣扬的“爱情至上”理念接续了上世纪初的启蒙式爱情神话,并因人们对革命时期压抑个人情感欲望的批判而增添了进步色彩。
而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也使得性别本质主义卷土重来——随着企业逐渐从社会福利和家庭照料中剥离,女性发现自己在公共领域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阻碍,“生儿育女,操持家庭”再度被强调为女性的天职,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进退维谷。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势必对亲密关系和理想婚恋状态有着更复杂的观感和考量。在1984年首次出版的《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 A. Radway)针对当代美国女性阅读浪漫小说的现象,对这一通俗文学题材的成规定式及其所反映的女性欲望展开了深入分析,她的许多洞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观众的浪漫爱情理想。

在1960年代女权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购买浪漫小说的女性却日益增多,那些恋爱故事多发生于英俊多金的男主角和大胆独立但娇柔脆弱的女主角之间。美国浪漫小说在1970和1980年代井喷式发展,全盛时期甚至占据了美国图书出版市场半壁江山。拉德威在位于美国中西部城市的一个中产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探究深受主妇喜爱的浪漫小说具备怎样的特征,又如何折射出了读者对自己生活的感受。
拉德威发现,主妇读者心中理想的浪漫小说大多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一个聪明且有能力的女主角与一个能够欣赏她的特殊品质、愿意以她想要的被爱方式呵护她的男主角,如何相知相恋携手一生。在理想的浪漫小说中,男主角被塑造成具有罕见中性气质的人,一方面强力阳刚,在男性群体中出类拔萃,一方面对女主角温柔体贴。作者常着重描摹男主角在遇到真爱(女主角)前后的变化——在她出现之前,他冷酷无情,对亲密关系不屑一顾;在她出现之后,他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珍重又专一。我们可以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浪漫小说的内核不仅延续至今,与当下中文言情小说“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主流叙事也极为相似。

“观众和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大体仍有一定的程式或规律性可循……之所以会出现相似的阅读习惯,主要是因为处于相似位置的读者习得了一套相似的阅读策略和阐释代码用于解读其接触到的文本。”拉德威指出,阅读浪漫小说是女性潜意识里反抗现实处境的一种方式,这种反抗基于如下前提:在父权制婚恋关系中,只有女性被要求向他人提供照料和情感滋养,她们自己却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因此感到身体和心灵的疲惫与空虚。由于不满于不对称男女关系造成的性别分工和情感呵护匮乏,女性诉诸于浪漫小说提供的幻想性解决策略,来获得某种情感补偿。
有趣的是,接受拉德威采访的女性读者都认为,浪漫小说中描述的人物或情节与她们所知的现实丝毫不符,但她们又非常强调作者严谨刻画故事背景细节的重要性。这一矛盾认知无意识地流露出了女性读者虽对现实不满、但依然期待某种完美异性恋关系和制度安排真实存在的微妙心态。在拉德威看来,阅读浪漫小说是女性的集体仪式,“她们从中获悉了父权制的本质,并了解了它对于身为女人,也即是说,身为一个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未掌握权力的个体的她们意味着什么。”
那些最受欢迎的浪漫小说无一不在传达一个讯息,即保持女性的主体性、满足女性的欲望与父权社会制度可以做到并行不悖。在这样的想象中,女性读者说服自己,男性气质对女性有百益而无一害(暴力和施虐甚至亦是“爱的证明”),克服由当前性别分工引发的恐惧,让自己相信“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理想爱情仍有可能存在”。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浪漫小说及其传达的浪漫爱情理想是女性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的一种应对策略,借由虚构作品中女主角的成功,故事的读者也获得了自我实现和权力彰显的满足感。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小说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借用了196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积累的话语资源主张女性赋权,比如强调女主角自信、独立等性格气质,并因此唤起男主角的爱慕;但它也有消极保守的一面,大团圆结局依然在强调女性作为恋人、妻子和母亲的男性附属身份,以浪漫的方式合理化这个让现实中女性感到不满的父权结构。
在当下流行文化工业迅速扩大的过程中,这类言情小说的叙事结构日益深入人心,从网络文学到IP热,言情小说的逻辑被大规模复制或转译,中国观众/读者得以从各个渠道(图书、影视剧、综艺节目、游戏)接触这套“人设化”严重的话语,成为了人们理解分析几乎所有文化产品的一个基础阐释框架。即使是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类主旨绝非浪漫爱情的严肃文学作品,也被一些读者从异性恋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并得出“三观不正”的结论。如果我们认同拉德威所说“浪漫小说及其传达的浪漫爱情理想是女性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的一种应对策略”,那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当下的浪漫爱情理想,反映了女性怎样的希冀和恐惧?
“三观党”“牌坊精”式的言论在近几年里频繁出现于社交网络,加之很多发言者页面显示的年龄较小,于是有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向传统价值观回归的标志。这也是周玄毅的微博引来颇多赞同的原因,他是这样写的:“我们这代人最大的荣光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劝自己的下一代人,不要那么保守。”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保守主义回潮和年轻一代资源丧失有着紧密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固化,上升渠道被堵塞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在国家提供的制度性安全网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人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家庭,这导致中国家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在接受播客节目“忽左忽右”采访时表示,这种新的家庭本位主义与其说是传统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回归,不如说是现实利益考量的结果——在生活成本飙升、房价高企的当下,90后、00后实现经济自立已经非常困难,再加上独生子女、密集母职、隔代抚养、养老等种种因素,都让家庭成为了个体最可靠和最后的堡垒,从中获取必要的经济和情感支持。
与此同时,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亦在加剧,特别是财富和经济资源分配日益向男性倾斜。在《他有房=她有房?多少女性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一文中,上海大学学者陈蒙和余芳芳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2015年的数据发现,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境遇、家庭财富继承方面的持续差异,阻碍了女性获得个人住房资产——近七成男性单独或与家人一起拥有个人住房,但只有不到一半女性为房产持有者。
在两性财富和经济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即使仅仅出于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考量,传统性别意识也极易复苏。2011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男女比例分别为61.6%和54.8%,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7.7%和4.4%。最新研究还显示了中国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在变大。上海健康医学院讲师李家兴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钱岳发现,虽然男女在工作领域的性别意识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为平等,但在家庭领域出现了较大分歧,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90后男性与之前世代的男性相比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弹。
社会分层结构固化、两性财富和经济资源分配不均、传统性别意识复苏,再加上婚姻不稳定性的上升和偏向保护有产者利益的现行婚姻法制度,都让女性在婚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让爱情越来越变成一场两性之间的博弈。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异性恋道德为何日益严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擦亮眼睛觅得一位可靠人生伴侣的重要性越高,他们在浪漫爱情理想中就越需要摈除“人生伴侣不可靠”的潜在威胁。在对异性恋关系和传统婚姻的想象中,稳定和安全(无论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二人关系意义上的)正超越真爱和自由,成为获得满足和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私人领域的观念保守化,除了个人经济利益的权衡计算外,还与国家意识形态收紧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从来不可能脱离政治干预。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文化政治”先例。
如同当下的影视剧,戏曲在帝制中国晚期是最通俗有效的文化媒介,它形塑并反映了大众文化与流行观念,也因此是政府严格审查的对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副教授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在研究清代北京戏剧市场的过程中发现,在17世纪昆曲全盛时期和19世纪“地方戏曲”皮黄崛起之间,北京戏坛不同剧种的竞争非常激烈。19世纪晚期,清廷选择接纳反映城市小市民审美和道德情趣的剧种皮黄,赞助其成为文化审美典范(皮黄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在这个过程中,承袭晚明江南文人审美的昆曲在北京由盛转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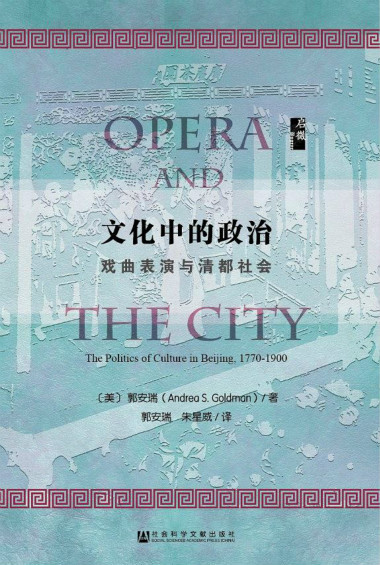
在《文化中的政治》一书中,郭安瑞通过分析“嫂子我”戏的流变,讲述了晚清朝廷如何在支持深受平民喜爱的皮黄的同时,让这种更道德化的戏剧样式日益被更广泛的城市观众接受。所谓“嫂子我”戏,指的是由《水浒传》中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三个奸诈女人的故事改编成的三部剧——《水浒记》《义侠记》和《翠屏山》。在分析18、19世纪昆剧和皮黄戏中“嫂子我”相关剧本时,郭安瑞发现,文本的文学性越强,就越流露出对反面女主人公的同情;文学性越低、目标观众群体文化程度越低的剧本,就越倾向于强调复仇和凶杀。
更具体而言,在观众群体主要由文人组成的昆曲剧本中,剧情叙事更倾向于唤起观众对敢于挑战礼教的女性的同情;而观众群体主要由文化程度较低的本地小市民构成的皮黄戏,遵循的是一种更以受委屈的丈夫及其兄弟为中心的叙事,形成了“女性出轨开头,男性报复结尾”的故事结构。
在18世纪,清廷对水浒故事有强烈的不安和忌讳。因为在一些版本的故事中,梁山好汉最后将反抗对象从宋朝转移至辽和金,由于清廷自认为金的政治遗产继承者,水浒故事被认为带有煽动性的反清思想。乾隆年间,清廷曾试图禁止出版、传播和表演水浒故事,严禁将之翻译成满文。然而同一时期,清廷依然根据昆曲中现有的众多水浒故事剧本编纂了一部多卷本大戏《忠义璇图》,其中就包括了《水浒记》《义侠记》《翠屏山》。
从这部官方钦定的水浒故事剧本中不难看出,清廷在挪用汉文化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在“嫂子我”戏中,兄弟情义和男性私刑被突出强调,但值得玩味的是,《忠义璇图》在最后16出将所有梁山好汉都视作假英雄而加以谴责,最后的剧目讲述的是不同水浒英雄在地府中的命运,比如身为梁山领袖的宋江被罚永世不得超生。在郭安瑞看来,这一点也反映了清廷的价值判断,“尽管淫荡、对婚姻不忠及引起的敲诈和谋杀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政治反抗被认为对公众利益更具破坏性。”
19世纪中期左右,包括咸丰帝、慈禧太后、恭亲王和醇亲王在内的清廷核心成员都喜欢上了皮黄戏,官方赞助极高地提升了皮黄戏种的艺术声望。紧跟宫廷趣味,京城精英对皮黄“嫂子我”戏的支持也有所增加。“19世纪中后期清廷对原本低俗的皮黄戏的支持促成了做工戏的暴力与政府提倡的女性道德规范这两者的怪异结合,”郭安瑞写道,“清廷对皮黄的支持提升了其文化地位,导致一种更为重男轻女及道德化的表演形式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并最终为更广泛更精英的城市观众所接纳。”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清廷的“文化工程”——将官方价值观融入戏曲,借由这一流行文化媒介向大众灌输儒家保守主义思想——对文化实践和大众观念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而身处期间的大多数人根本无从抵抗这种压力。以史为鉴,在指责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保守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保守主义回潮的因和果究竟是什么。当爱情这种人类天性中最原初、最本真的情感都被压抑、被嘲讽、被以身外之物衡量的时候,我们应该指责的绝不是一个发弹幕的年轻人那样简单。
参考资料:
[美]珍妮斯·A·拉德威. 《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译林出版社.2020.
[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1900-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美]郭安瑞.《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下一次拍《红楼梦》,可以考虑把男主改成贾政了
《英国病人》《钢琴课》“毁三观”?豆瓣短评里的道德景观与现实焦虑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08988.html
【专访】人类学家阎云翔:因为欲望,我们再无可能倒退回传统道德伦理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390680.html
播客节目“忽左忽右”:社会学者解读恋情与家庭
他有房=她有房?多少女性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 China Review特刊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http://www.china.com.cn/zhibo/zhuanti/ch-xinwen/2011-10/21/content_23687810.htm
学人说|女性向前,男性后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在扩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