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收入并非应对危机的补救性措施,有薪工作也不应该是安身立命的唯一良途。

来源:Matt Kenyon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经济严重受挫,各国失业率陡升。尽管入夏后有更多国家加入经济重启的行列,工作消失的危机却没有得到缓解。据国际劳工组织6月30日发布的第五版全球劳动力市场监测报告,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减少了14%,相当于4亿个每周工作48小时的全职岗位消失。与同一个月前发布的监测结果相比,全球工作时间继续下降10.4%——情况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
为应对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一些国家的政府尝试通过向民众发放现金来纾缓贫困、刺激消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自3月起陆续批准了各类经济补助和刺激计划,向符合条件的民众发放现金。这类举措再次将“基本收入”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越来越多政治人物、评论家、学者重新拾起对基本收入的兴趣,希望以此来刺激疲软的福利政策,改善贫富差距等问题。截止目前,英国跨党派联盟发起的全民基本收入请愿活动已收集到197万个签名,西班牙经济事务大臣纳迪亚·卡尔维尼奥也声明,西班牙正致力打造一项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措施,届时将有100万余个家庭受益于永久性的经济安全网络。
但严格说来,上述举措只是带有“基本收入”的色彩,与“基本收入”所描绘的图景还相去甚远。英国经济学家、“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创始人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他的新书《基本收入》中为这一概念做出以下定义:“定期(例如每月)无条件向个人支付的一笔适当金额。”也就是说,基本收入的目标是对所有人进行永久性的支付,它不以任何社会身份或是财力调查结果为前提,它是一项不可撤销的权利,而非仰赖当权者的“好意”。
“不分贫富都给钱的做法很愚蠢”“鼓励不劳而获”“降低工作吸引力”……即便是在亟需变革的时代,基本收入依然因其激进而招致了许多批评和指责,常常被视为异想天开的乌托邦。然而,当“不确定性”取代“风险”成为21世纪经济不安全感的底色时,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都会因薪资起伏、缺乏劳动保障、长期慢性债务以及失业等问题陷入困难时刻,气候变化、环境危机、全球化等问题又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正如今年的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巨大波动一样。尽管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与效力充满争议,但它的确在社会分崩离析之际对现行收入分配系统和工作伦理提出了挑战与关乎自由、社会正义的新构想——这正是我们面对新自由主义式不平等与意义消解时所需要的。
在借由基本收入的概念对当下的收入分配系统与工作观念展开反思之后,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追问,工作的消失真的是贫困的第一诱因吗?如果工作机会的设立只是以雇主的弹性需求为纲,以“好看”的就业数据为目的,它究竟能给劳动者带来多大的保障与安全感?当我们把工作视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时,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又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实现自己的追求呢?

工作场所与时间的不确定性,通常被视为零工经济的特点,但如果我们拓宽检视范围,不难发现,整个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零工化”:一名朝九晚五的教师需要把大量私人时间投入到“家长群”里;办公室白领在周末无视加班通知会遭到“不负责任”“不知上进”的他人和自我谴责;居家办公者的劳动者承担了公司转嫁的劳动成本,灵活的工作安排披着“自由”的伪装不断蚕食属于私人的空间与时间。
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模糊,是斯坦丁所说的“第三纪时代”(Tertiary Time)的一大特征。在他看来,“工业时代”的劳动受时间支配,是一种“打卡计时”活动,薪资计算相对透明,但“第三纪时代”的模糊状态却放纵雇主在对劳动质量的评测上更加“武断”,制定具有“误导性”的考核标准,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薪资,“食利者”(rentiers)则受惠于未经支付的劳动,从而累积更多的财产。
除了劳动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之外,“第三纪时代”劳动者需要面对的又一难题是稳定性的欠缺。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中,能够提供稳定收入和长期保障的工作越来越少,曾经意味着阶层晋升的“流动性”变得消极破碎,甚至潜藏着“向下流动”的危险。以疫情期间的女性零工为例,许多女工初来城市务工时,盼望的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积累起足以开展稳定生活的本钱,而非仰慕“向上流动”的神话。零工经济创造了职缺,却没有提供有效的就业保障,并且随时可以取消这些工作机会,致使平台工人成为动荡之时第一批滑向失业和贫困的人,在寻求安稳的途中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确定性”被斯坦丁总结为当今经济不安全感的根源。它与20世纪后半叶工业经济体的状况不同,当时的经济不安全感以“风险”为底色,相关机构可以对生病、失业、伤残等“概率事件风险”进行统计估算,并据此建立社会保险系统。可量化的风险可以用保险来应对,福利系统面对不确定性时则束手无策,因为无人能够预料到越来越频发的“偶发”事件以及各种冲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零工化”经济催生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危产阶级(precariat),生活中任意一个微小的意外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使之陷于贫困且久难恢复。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认为,基本收入能够提供或多或少的事前保障,帮助人们应对“不确定性”。斯坦丁指出,现存的福利计划中隐含了“贫困陷阱”与“飘零陷阱”。根据英国官方提供的数字计算,已领取政府津贴的失业人员一旦从事低薪工作,就会立即失去国家福利,面临高达80%以上的边际税率,他们的收入实质上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津贴发放的拖延也会阻碍申领人接受短期或非正式工作。作为“权利”的基本收入将有效规避上述两种陷阱,为底层人士提供持续性的经济安全感。
此外,多项研究显示,以财力调查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会迫使申请人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消耗在文书、排队、与官僚打交道上,并遭受污名化,许多真正有需要的人出于恐惧、无知等原因没有进行申领,自然无法得到补助金。相较而言,针对全民无条件发放的基本收入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减去财力调查环节也能为传统福利国家节省一笔巨额财政支出——毕竟,单以荷兰奈梅亨市为例,在该市每年福利支出的8800万欧元中,福利部门的运营费就花去了1500万。福利制度造成的行政官僚冗员问题一直为人诟病,同时也是基本收入支持者用以反驳“财政无力负担”的有力论据。
如果说此前我们对第三纪时代“不确定性”的观察和体验零星地散落在某些地区、某个行业和阶层,新冠大流行已经整合起了破碎的拼图,并将之置于我们眼前。来自遥远世界任意角落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叠加为我们身边沉重的现实,没有人可以期许侥幸。正如斯坦丁所言:
生活在一个开放式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的我们,要处理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超乎我们掌控但又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决策的影响还因破坏力强大的技术变革,及蓄意牺牲劳动保障以换取雇主经营灵活度的劳动市场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

2017年,芬兰发起了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计划”实验,在接受政府失业救助的公民中随即选取了2000名25-28岁的年轻人,每月发放560欧元的基本收入,这项收入不会因领取人重新就业而取消。芬兰社会事务与健康部声明,该实验的主要目标和促进就业有关,拟定实验计划的工作团队领导人也向媒体表示:“它将鼓励担心失去失业津贴或其他津贴的人接受一些短期的就业机会。”
遗憾的是,在芬兰为期两年的实验结束后,实验群体在就业方面的表现与未获得基本收入的对照组没有多大差别,基本收入不等同于促进工作的诱因。美国六个州在1968-1980年间的本地实验以及1970年代加拿大著名的Mincome实验数据则表明,基本收入将降低工作诱因。反对者们就此提出了不少批评,例如,基本收入不利于“充分就业”等进步主义政策,基本收入将导致工作消失,鼓励“不劳而获”的懒惰习气等。

针对这些批评,斯坦丁提出了一个尖刻的疑问:什么是“工作”?批评者们在长篇大论地哀叹基本收入将如何打击就业,重创经济,败坏人类“勤劳努力”等优良道德时,“工作”作为一个最关键的概念始终未经检视。不论是上述基本收入试点实验收集的劳动数据,还是将“不工作”视为道德堕落的批评,它们都默认了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对“工作”的标准定义——有薪劳动。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曾用女管家的例子来论证有薪劳动工作观的荒谬性。他假设,如果自己聘请了一名女管家,国民收入、就业人口等一系列“好看”的指标将会上升,不讨喜的失业率则会下降,而一旦自己与女管家结婚,她所从事的与之前完全相同的活动则会立即失去市场价值,“好看”的指标随之下降,失业人口增加,引发一部分数据爱好者的焦虑和谴责。
而在现实生活中,“女管家”式的角色大量存在,传统的家庭妇女、照看孙辈的老人,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无法计入“好看”指标的无薪劳动。尽管这两年家庭内部的劳动逐渐正获得认可和正视,但它依旧从属于一个无法与市场内有偿劳动并列的体系。人们在谈论“工作”时,脑中很少会出现家庭照料、社区服务等场景。
实际上,每个人一生中都要面临“女管家”式的困境。最直接的例子是“第三纪”经济体“一直在线”的工作文化——与现职有关但却没有报酬的劳动,被无限加塞到我们的私人时间与空间之内。当这种无限加塞与“奋斗”“拼搏”等鼓舞人心的话语相连时,资本对人的榨取被险恶地包装成自我修养和激励,工作被鼓吹为实现内在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唯一途径。

然而,这些工作真的这么有价值吗?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理论已经向我们展示,现有的许多工作无法给个人提供满足和成就感,也丝毫无益于社会福祉,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他在《狗屁工作》一书中举了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一名西班牙的公职人员曾六年未到岗上班,却无人发现,在这段时间里,他潜心钻研斯宾诺莎的著作,成为了一名相关领域专家,可见一些工作岗位根本不产生经济价值,也无法具备意义,形同摆设。疫情期间有网友调侃“如果再不上班,老板就会发现其实没有我,公司也能运作下去”,这一方面反映了劳动者面对雇佣关系不平等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对现职岗位的怀疑。我们难以设想一个没有医生、护士、环卫工人的世界会是怎样,但如果消失的是某些行政管理岗位或公关咨询职业等等,对社会而言似乎没这么紧迫。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预言,依赖自动化极大地提高生产率后,人类将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周仅需从事15小时的工作。将近百年过去,科技的发展诚然使人类社会总体的物质财富空前繁盛,但等待我们的却是让人丧失意义感的“九九六”式社畜生活。既然有这么多工作无法创造社会财富,达成“充分就业”等指标的做法就很难说是出自经济的考量。20世纪建立起来的收入分配制度瓦解后,国民收入愈发流向资本而非劳动,不论个体再怎么辛苦工作,都无法跨越结构性失衡的鸿沟。对个体和社会而言,工作所具备的经济意义都十分有限,“狗屁工作”存在的理由更多是政治性的——它是金字塔顶端的少数“食利者”(rentiers)维护现有秩序的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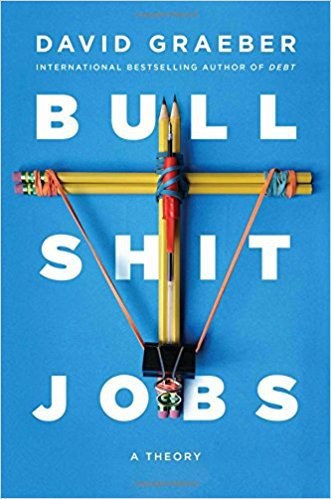
如果我们用一种更审慎的态度检视与工作相关的一系列指标,就很难去苛责基本收入无法促进就业了。在加拿大的Mincome实验中,有薪劳动量小幅降低的群体主要是养育幼童的母亲与在学青少年,他们停止或减少工作的原因,是在家庭经济负担减小后,希望花更多的时间照料婴儿或投入学业,真正减少的只是市场认可的“有薪劳动”,人们并没有因为获得补助而变得游手好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本收入的目的既不是让人们有钱得无所事事,也不是助推充分就业、经济发展,而是让人们“有机会可做自己希望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也只有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才能看清,基本收入不是对当下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的补救性举措,而是长期的匮乏、隔离、屈辱与愤怒所孕育的反叛的种子。它关乎社会正义、自由与安全感,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选择自己所热爱的而不致流离失所的机会,旨在让人们学会重新拥抱可供沉思的“闲散”——毕竟,20世纪虽然同样混乱不堪,乌托邦的理想却在每一块大陆上激荡,我们如今被迫“有闲”,却无力构想未来,只是一味地咀嚼那个已然逝去又乏善可陈的旧梦。
参考资料:
《基本收入》[英]盖伊·斯坦丁 著 陈仪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6
Bullshit Jobs. David Graeber Simon&Schuster 2018-5
《再不上班,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老板公司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