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新书试图探索如何制定标准来限制有害言论,同时保留合法的言论自由。

2017年8月,在夏洛茨维尔的维吉尼亚大学校园举行的“团结右翼集会”游行中,游行者手持火炬穿过校园 图片来源:Evelyn Hockstein /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2017年8月11日,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举行“团结右翼集会”(Unite the Right),抗议市议会拆除南北战争期间效忠于南部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雕像的决定。这些抗议者手持火把,高呼“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Jews will not replace us)”,与反对示威者对峙。第二天,紧张的对峙演变成暴力冲突,一个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开车撞向人群,造成了一名女性希瑟·黑尔(Heather Heyer)的死亡和数十人受伤。
对于此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而是宣称示威者双方均有“非常优秀的人”,这让这一事件成为了美国有害政治言论的又一个导火索。
随着从白人民族主义者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极端组织的意识日益增强,这起事件引发了新一轮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一些评论人士重申了现行法律的现状,他们认为,无论白人民族主义者有多么有害,只要他们不煽动暴力,他们就有权自由发言。
但夏洛茨维尔事件也为一个虽然微小但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尤其是在被言论规范、政治正确和抗议活动所主导的大学校园里。这种观点认为,针对弱势个人的仇恨言论不应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即美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译注)的保护。
在两本新书中,迈克尔·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和塔纳·罗森巴姆(Thane Rosenbaum)分别从双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场辩论中传统的宪法和哲学观点,很有想法,但最终未能找到解决方案。缺陷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很有意义,但如何制定标准来限制有害言论,同时保留合法(尽管不受欢迎或具有挑衅性)的言论自由,是相当有难度的。
在《为魔鬼平反:科学人文主义者的反思》(Giving the Devil His Due: Reflections of a Scientific Humanist)一书中,谢尔默略过了通常的宪法分析,转而将言论自由视为民主和知识的基石。他解释说,人们“通过言论和写作”进行交流,“因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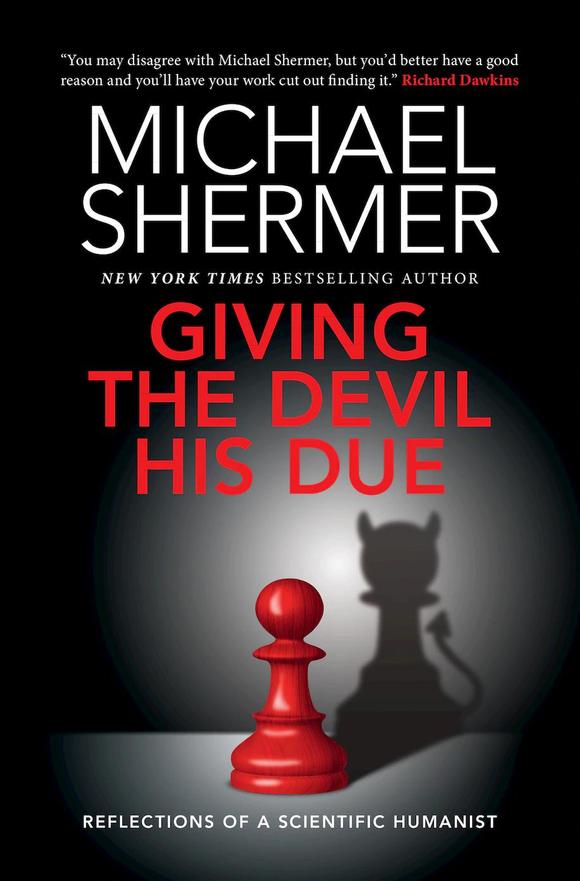
作为一个博学者,谢尔默在书中深入探讨了广泛的话题:考古学、神创论,甚至火星殖民。在一种言论的具体模式出现之前,它与言论自由的联系都是脆弱的。不管一种理论在谢尔默看来是多么古怪或不受欢迎——例如,他给“科学神教”贴上了“邪教”的标签——他都愿意讨论其优点。作为《怀疑论者》(Skeptic)杂志的主编,揭露伪科学但思考其优点是谢尔默经常做的事情。谢尔默相信,这种做法强化了他的论点,加强了他对一个主题的理解。他认为,“有时候我们都是错的。” 克服这种“人的易错性”的唯一方法,是“在广博的思想中”检验我们的主张。从本质上说,谢尔默是将科学论证中思想的工具应用到政治舞台上——即不受限制的思想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假设可以得到持续的检验。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对科学和政治来说都是不可侵犯的”。
这种观点引人注目但并不完美。
与科学家不同,鼓吹暴力和满嘴污言秽语的偏执狂对这种民间思想交流不感兴趣,这一点罗森巴姆在《拯救言论自由……在它自毁前》(Saving Free Speech . . . From Itself)中进行了论证。在身为法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罗森巴姆看来,仇恨煽动者们将宪法第一修正案扭曲成了一种进行压迫的武器。“我们一再将敌对行为与言论自由混为一谈,” 罗森巴姆写道,“宪法第一修正案为那些实施暴力并将其伪装成政治表达的人提供了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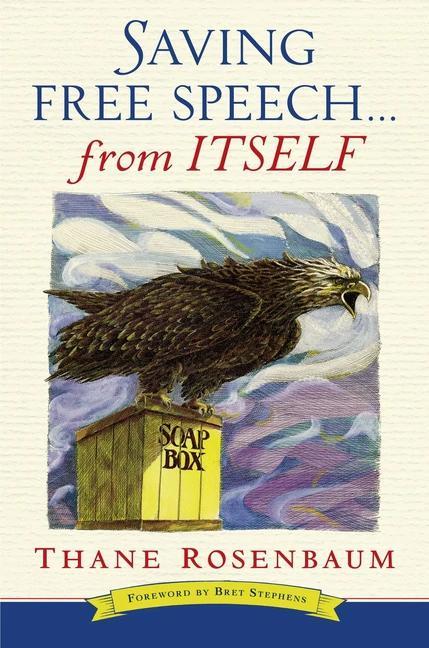
罗森巴姆提出的两个解决方案之一与批评者的观点相呼应。他呼吁如果言论通过威胁和恐吓特定的目标受众,或者当言论被用来剥夺弱势群体的尊严、自尊和社会地位时,应该对那些有意造成伤害的人进行严格的限制。
更为新颖的是,罗森巴姆认为因仇恨言论而造成情感伤害的受害者,应当有起诉权。罗森巴姆认为,这种“心理伤害的强度与身体所遭受的伤害是同等的”,而且这些伤害可以通过脑部扫描来测量,心灵伤害的受害者应当有权寻求法律的帮助,就像身体伤害的受害者一样。
罗森巴姆还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想法不会受到欢迎。他哀叹道,“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任何对第一修正案的批评都会立即被视为煽动性言论。”这种现象部分原因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判例所导致的。法官没有限制那些散播有害言论的人,对待这些言论者——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纳粹崇拜者——就像对待爱迪生或爱因斯坦一样。”
谢尔默的观点中是美国对言论自由根深蒂固的热情,而罗森鲍姆的逆向思维也提供了许多明智的建议。
但将这两种观点放在一起来看,言论自由的困境仍然没有解决:为了保护人们不受仇恨言论的影响,谁才能决定什么言论是受宪法保护的,以及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做出决定?美国最高法院做过类似的判决,但结果徒劳无功。为了区分被禁止的淫秽出版物和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艺术言论出版自由,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大法官恼怒地宣布:“我看到就知道(什么是淫秽物品)。” 20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一长串涉及色情内容的审查案件,大法官们备受社会保守派的批评和嘲笑,最终放弃了“明线规则(bright-line test)”的发展。时至今日,任何试图建立规范政治言论标准的努力似乎都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除了难以建立可行的标准之外,历史一再表明,压制那些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的声音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多年来,妇女参政论者、民权活动人士、反战抗议者和LGBT权益倡导者不仅受到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的审查,还受到“善意”批评者的审查。这些反对者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或发现他们的革命思想具有攻击性、威胁性或不爱国。
也许没有什么比麦卡锡主义更能体现这种做法了(麦卡锡主义是指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不忠、颠覆、叛国等罪,也指使用不公正断言、调查方式,特别是对持异议者和批评者进行打击——译注)。二战后,美国对苏联侵略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这也为起诉政治言论、作家和教授以及广泛的自我审查铺平了道路。或者想想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学生激进主义的回应:“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言论自由,都不能成为让不满分子、垮掉的一代人、和让肮脏的言论倡导者扰乱学术或社会的正当理由。”里根在1966年竞选州长时曾如此宣称,他说这些学生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并抱怨说,“政府应该抓住领导者的脖子,把他们赶出去。”
作为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遇到了在谢尔默和罗森巴姆的两种观点中的困境。道格拉斯说,“在立国先辈们看来,没有什么权利比言论的权利更神圣。” 就在道格拉斯说这番话的几天前,一群暴徒关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废奴会议,他们担心该会议会冒犯南方各州,然后考虑脱离联邦。一大群“绅士”高呼“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 ——而不是激进分子或麻烦制造者——阻碍了废奴会议,道格拉斯警告说,“任何一人,如无言论自由,无论年轻或年老,无论多么高尚,多么卑微,被武力压倒,都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情。” 与美国目前的不和谐状况相似,道格拉斯对言论自由困境的回应,在今天的美国和内战前夕一样引起了共鸣。
本文作者Michael Bobelian在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教授新闻学,著有《最高法院之争:亚伯·方特斯、厄尔·沃伦、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和最高法院的建立》(Battle for the Marble Palace: Abe Fortas, Earl Warren, Lyndon Johns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upreme Court)一书。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