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作者十分真挚,记述童年往事的自传也大多千篇一律,毫无真实性可言。”

按:自传(autobiography)和回忆录(memoir)有着传统上的差异,“自传完全聚焦于作者本身,而回忆录则关注其他的人或事物。”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存在差异,1876年的一本《通用词典》认为,自传留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写自传的时候不一定要像写回忆录一样精确陈述事实。无论存在着怎样微妙的差异,这二者无论是在作者、出版商那里还是在读者眼中,基本都被认为是对作者人生做出了真实描述的书。
在图书馆里,回忆录和自传书架并不凋敝零落,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有着非说不可的国外,有那么多的生命中有那么多教训和真理可供学习。而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是大量增加的词汇、想法和情感,还是认知外界的过程,还是孩提时代在脑海中对社会产生的连续印象,我们其实几乎记不清什么。因此,就算作者十分真挚,记述童年往事的自传也大多千篇一律,毫无真实性可言。”
那么除了故意的谎言和虚伪的删减,回忆录和自传是否会因人记忆的不可靠而失去根基?在《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一书中,美国文化评论家本·雅格达带读者分析了回忆录和自传与作者真实一生之间的距离,以及这距离产生的丰富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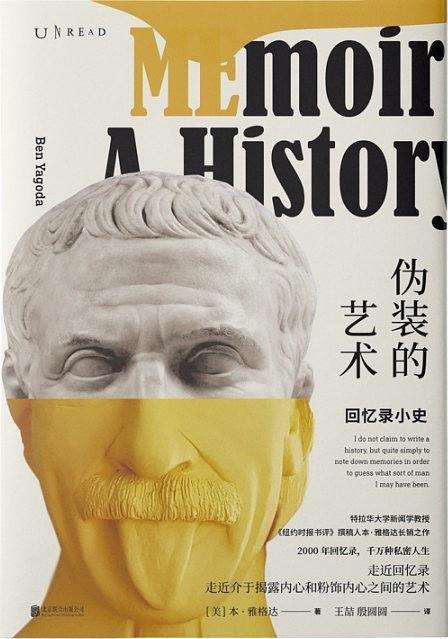
文 | [美]本·雅格达 译 | 王喆 殷媛媛
回忆录中的虚假还远不止刻意的谎言和虚伪的删减。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几乎没有一件曾打动我心弦的事是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经历了那么多接二连三的事之后,很难避免把时间或地点张冠李戴的情况。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赖以佐证的日记或文件,也没有能帮助我回忆的其他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些像刚刚发生那样,在记忆中十分清晰,但也有遗漏或空白,我只能用与我的记忆一样模糊的叙述来填补。所以,有的地方我有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切的材料之前,我可能还会出错。但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的叙述是准确且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做到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后来,卢梭还反复提到,虽然某些叙述可能存在谬误,但这无关紧要:“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所做的,我也不会记错,我在这里写下的主要就是这些......我许诺交出我心灵的历史,而为了忠实地写出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记录,我只需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遵循内心就够了。”
卢梭一如既往地很有先见之明。如他所承认的,也如一个世纪里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人类的记忆远远不能被当成值得彻底信任的机制。传统认知把记忆当成检索系统,就像能回放的录像带,或是能调取记录的电脑。在这种模式下,记忆的能力受限于大脑的容量:当某条信息被更新的或更紧迫的信息挤出去之后,它就会被遗忘。只有在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扭曲或虚假的记忆。
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观点就是记忆是反复无常的。他探讨了我们是如何被波动的情绪捉弄的,以及我们的精神防御系统是如何(在他所谓的压抑中)除去痛苦经历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持续的研究,后来的心理学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们发现记忆本来就不可信赖:记忆不仅会因缺漏而变质,还不可避免地会被曲解和捏造。记忆本身就是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它将“真实”的记忆、对世界的认知、从各处收集来的线索以及对过往记忆的回忆拼凑在一起,看似有凭有据地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妙笔一挥,把内心的设想粉饰成了真实的场景。正如心理学家F.C.巴特莱特1932年在开创性的著作《记忆》(Remembering)中所说:“记忆显然更接近重建,而非单纯的复制。”
而且,重建的过程受制于各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失的部分越来越多。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奥弗曾向一群高中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他们生活的问题,三十四年后,他又让这群人去回想他们的早年生活并回答同样的问题。两次实验得到的结果相去甚远。这群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在成年后回忆说宗教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很重要,而在他们青少年时,有近70%的人这样回答;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记得曾受过体罚,而在他们青少年时,有近90%的人回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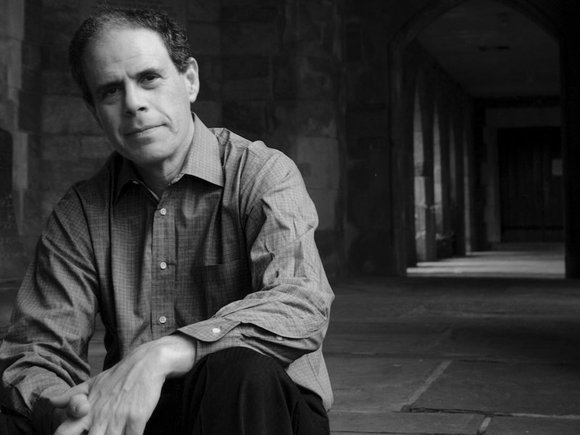
导致曲解和谬误的还不仅仅是时间。事件发生后,如果我们试图记住得到的提示或建议,甚至是不易察觉的暗示,记忆就会迅速滋长。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塔斯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很多开创性研究。她和几十名年轻人多次面谈,并要求他们回忆“在购物中心迷路的经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在商场里迷路过,但面谈结束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都表示“想起来”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向被测试者播放了一名男子进入一家百货商店的监控录像,并告诉他们,不久后,这名男子杀害了一名保安。接着,研究人员向被测试者展示了一组照片,要求他们从照片中辨认出歹徒——其实这些照片里的人都不是。在一些被测试者(错误地)选择了其中一张照片后,研究人员就告知他们选对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施克特在调查之后写道,这些被测试者“声称他们对自己的记忆更有自信了,对歹徒的印象更清晰了,对他的面部细节也记得更清楚了”。施克特指出,如果这些人出庭做证,他们对自己记忆的信心“对陪审团来说将是极具说服力的”。
这种对自己记忆的信心对自传的读者来说也一样极具说服力。除了警察和检察官(或心理学家)的诱导性提问之外,暗示还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回忆录这种东西本身就与不带任何主观倾向的记忆截然不同。在每一个事件、情节或人物的背后,是对某个人的一生的诠释。其中隐含的信念是,人的一生可以被写在纸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个好故事。最终展现出来的则是各种来自内心的暗示。即使有精确的记忆这种东西存在,在这般压力下它又如何不动摇呢?
心理学家C.R.巴克莱在总结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认为,大多数自传中的记忆是“为了维护自身和过往的完整性而进行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但不准确的……人们通过这些看似可信的重建来传达生活的意义”。另一位围绕记忆进行了实验并有大量著述的心理学家乌利齐·奈瑟尔是这样说的:“我们可能记得一整件事,也许印象清晰得足以推断出一些更具体的特征,但我们不记得那些特征本身。这就是记忆容易被不经意地曲解的原因,也是虚假的东西也常常看似‘正确’的原因。我们永远无法充分地评判‘历史真相’,因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太过丰富,任何人的记忆都无法完全保存。但以一种相对准确的方式记住一些总体特征,就相对容易。这样的回忆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尽管其中一些细节并不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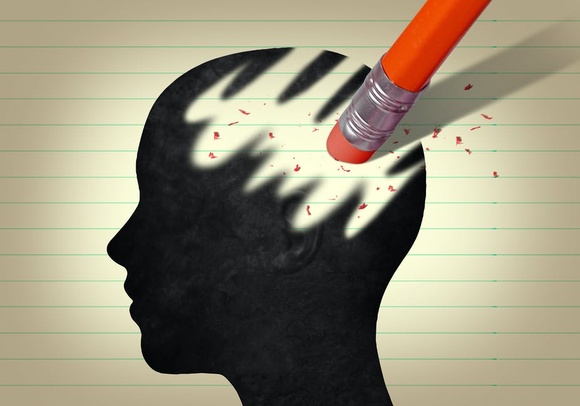
关于记忆的缺陷,著作最多的是心理学家丹尼尔·施克特。自传和对过去的回忆都被他称为“偏见”的谬误——我们的记忆总是不经意地曲解过去。他在《记忆的七宗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中列出了记忆被曲解的五种类型,它们都是经过多项研究后总结出来的(需要着重强调这一点):“一贯型和善变型指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观念,重新塑造或美化自己过去的经历。事后聪明型指的是人们用现在的知识去分析过去的事情。唯我型是说在对现实的感知和对记忆的精心编排上,自我扮演着重要角色。模板型指的是记忆在人们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人们对这种影响未必很清楚。”
以上几种类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会让记忆变得更引人入胜或更戏剧化,与充满随意性的现实生活相反。在一项研究中,一群研究生被要求在参加某次重要考试前把他们的焦虑程度记录下来。一个月后,再让他们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这时他们都夸大了自己的焦虑。这种夸大在那些通过测验的人身上最为显著。显然,“我真的很焦虑,但我通过测验了”这样的故事值得写进回忆录,而“我没怎么担心,就通过测验了”的“事实”就没什么好写的了。
即使在最戏剧化的事件中,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几十年前,精神病学家创造了一个术语——无论是个人事件(如父母去世、孩子出生)还是公众事件(如总统遇刺),人们对重大事件的回忆都被称为“闪光灯式记忆”。最初,人们或多或少会假设,这些记忆持久且鲜明,应该是准确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奈瑟尔和一名同事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坠毁后二十四小时内采访了一群大学生,不仅询问了坠毁事件本身,还询问了他们听说此事时的情景。两年半后,他们再次采访了这群大学生。尽管他们可以非常生动地回忆坠毁事件,并对自己记忆的准确性相当自信,但总体来说,他们的记忆很糟糕。总共七个问题,大部分人只答对了不到一半,且这四十四名学生里有十一名回答全部错误。更让人吃惊的或许是,即使把他们自己当时的回答给他们看,他们也想不起来。对此,奈瑟尔写道:“最初的记忆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记忆就像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人们却对其准确性自信满满,这样的矛盾似乎是人类共有的特征。显然,大多数自传作者(卢梭的谦逊是个例外)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的记录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哪怕其中包括对半个世纪前对话的逐字复述。实际上,记忆与叙述之间本来就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叙述讲究细节,而记忆在细节上着实不尽如人意。让我们再以一项心理学研究为例。奈瑟尔在实验中问一群大学生:“你们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他们在描述具体事件时比概括总体情况时能力差了不止一点半点。不仅如此,在被要求叙述具体细节时,他们“似乎感到了困扰”。奈瑟尔写道:“记忆不会特意关注独立事件,而记住持续状况或典型模式则很自然。为什么不呢?反正长远看来,后者重要得多。”
然而,自1907年埃德蒙·戈斯的《父与子》(FatherandSon)出版以来,大量非政治家、非世界名流的回忆录喷涌而出。这些作品主要是由“独立事件”而非“持续状况或典型模式”组成的。(政治家和名流的回忆录另当别论。)而且,这些独立事件并不只是作为插曲存在,它们出现在一页又一页无穷尽的对话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话比大段阐释更易读,更有力。然而,确切的词语比具体事件更难记住。我不能准确地复述我妻子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对我说的话,半个世纪前我的一年级老师说过什么就更不用谈了。罗伯特·德·罗克布吕纳是少见的认识到这种局限性的回忆录作者,他在《我童年的遗嘱》(1958)中写道,他只能在脑海中准确地重现童年时听过的几个单词,比如他母亲曾坚决地说:“是明天!”(然而,他不记得这个“是明天”说的是什么事了。)可以说陡然间,科学依据、法庭证词和《纽约客》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的准确性,在自传中不复存在了。
自我暗示也是个问题,它的影响不亚于警察或检察官提出关键问题时所施加的压力。写自传这件事,与回忆这种无主观倾向性的行为完全不同。在对各个事件、情节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表面下,是对自己一生的诠释。隐含更深的是,作者希望证明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这件事具有合理性,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个有价值的好故事。此外还有评论家乔治·古斯多夫所说的自传作者的“原罪”:当人们已经知道了某段过往经历所产生的结果,就难免会对那段记忆产生曲解。哪怕精确的记忆的确存在,在这般压力下它又如何能不被动摇呢?

因此,事实是,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人生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想把它写成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样子,你就会开始降低真相的标准。19世纪,卢梭的后继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其中包括司汤达,他说:“我没有说我在书写历史,我只是记下我的记忆,以便别人猜测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路易斯·古斯塔夫·瓦珀罗在1876年的《通用词典》中,界定了记忆与真相之间的差异,还针对三种类别(自传、回忆录、忏悔录)提出了新奇的分类法:“自传留有大量的想象空间,回忆录精确地陈述事实,忏悔录完整地说出真相。”英国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在19世纪后期热衷于倡导生平写作的莱斯利·斯蒂芬走得更远,他预测说往后的评论家会庆幸记忆和确切事实之间存在差异:“与其他类型作品不同的是,自传可能会因其中的失实陈述而变得更有价值。”
到了20世纪初,自传已经濒临崩溃。它承受了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还是易犯错误的记忆,以及“真相”的混乱本质。思忖至此,一个认真的作家怎样才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呢?20世纪初,马塞尔·普鲁斯特做了一个极佳的选择,那就是让自传在想象的加温下慢慢升腾,最终被塑造成小说。另一种选择是承认目前的困境,然后往前看。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率直、无畏且超前,像是美国版的卢梭。他写道:“这就是他记忆中的旅程。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实际的经历没有教育意义,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亚当斯在1905年写下了这句话。几乎同时,马克·吐温也在写自传,他同样承认并接受了回忆的局限性:“我时常想起,我弟弟亨利刚刚一周大时,闯进了门外一堆柴火里,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坚信这种幻觉,认为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这就更了不起了——因为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当时还那么小,连路都不会走......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我自己六周大的时候,曾伺候祖父喝威士忌,但现在我已经很少提起这些了;我老了,记性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了。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但现在我的机能正在一天天衰退,可能过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我以为自己记得的也许反倒都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伪装的艺术》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