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对病毒的讨论。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对病毒的讨论。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陆续有公共卫生学者和科学家警示病毒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可能,但直到三月,当欧洲成为疫情重灾区、美国确诊病例一周内飙升至2.5万时,幻想作壁上观的侥幸与漠然才被大面积破除。
人们逐渐意识到,新冠并非只活跃于遥远的“彼地”,它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性”病毒,无人可置身事外。在呼吁警惕疫情暴露的种族主义问题、仇外情绪之后,西方左翼思想界对病毒的反思也愈发深广,受资本控制的医疗资源分配、求助伦理道德以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都激起了大量讨论。
英国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在《雅各宾》发表的文章《新冠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指出,作为近年资本主义内核的消费主义驱动力衰退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盛行于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将公共卫生问题引入更晦暗的深渊,而所谓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一种假象。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资本主义的局限》(本文中文版由澎湃新闻翻译发表)中同样探讨了资本垄断下公共医疗卫生与个体权利的脆弱性,既有的阶层、地域与性别区隔也被病毒感染的随机性所掩盖。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左翼思想界爆发的“百家争鸣”不是一种零散的关注,在病毒的阴影下,资本、性别、种族、国家政治等议题几乎都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现代性的总体性扣问和批判。欧洲公共知识分子齐泽克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 本文由《三联生活周刊》独家引进发表)一文中指出,我们熟悉的世界已停止运行,“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在现行的世界秩序坐标中,我们无法应对这些“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新冠大流行似乎迫使人类走出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和安逸,在死亡的威胁和一切不平等、不确定中重新拾起对未来秩序的想象力。在左翼知识分子对新秩序的构想和呼吁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频频出现,或许正如巴特勒所说,疫情在西方世界“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人群中依旧有着“对激进平等的集体渴望”。
美股十天内熔断四次、各地餐饮业、旅游业大范围停摆、货品供应链断,全球经济都笼罩在衰退的乌云下。在哈维看来,经济衰退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呈现出“急剧失控”的态势,而其最终结果或许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市场需求减少这么简单,消费主义驱动力的减弱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螺旋式无尽资本积累”模式的内在崩溃。
哈维指出,2007-2008年后,消费主义经历了爆炸式增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主要依靠消费主义驱动。例如,国际旅游业在2010年至2018年间急速扩张,国际旅行访问次数由8亿增加至14亿,带动了周边机场交通、酒店的建设以及餐饮、观光的蓬勃发展,吸引大量资金流入。
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我们看到大量国际商务与私人外出计划取消,许多蜚声国际的电影节、艺术展和体育赛事相继停办,酒店与餐厅全行业遭遇了几乎前所未有的萧条。《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有关东京奥运会的文章称,如若本届奥运取消,对已经身处衰退边缘的日本来说可能会是一场“经济灾难”,而现阶段的阴晴难测已经使奥运生态系统陷入“等待状态”,给那些指望着奥运消费带动经济的企业和个人造成损害。
哈维将这类消费形式定义为“基于事件”的体验型消费。当事件在疫情的威胁下被逐一取消时,这些前沿的消费主义模式也被迫降温,而大量属于工薪阶级的“补偿性消费”渴望也正在减退。如此情势下,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所面临的不再是由某地火山爆发或地震带来的短期消费水平波动,而是主宰富裕国家的消费主义资本经济的溃烂。

除去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维在文章中指出,在许多所谓的“文明”世界,当局往往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提供减税和补贴资金,结果金钱流向了大型企业和富人的口袋,政府在面对公共灾难的紧要关头反倒两手空空,公众被直接抛入危机之中,四顾茫然。他们不能指望掌握资金和技术的制药巨头承担公共卫生工作,对它们来说,预防不是重点,治疗才是获益的关键,因为“我们病得越重,他们赚得越多”。
如果说对消费主义过度依赖产生的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运作,那么上述新自由主义的弊病则是资本运作与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甚至生态背景层层嵌套后的结果。《财新》杂志文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化的错吗》介绍了欧洲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观点,他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真正走向自律,带来“繁荣、平等和个体的尊严”。在新自由主义下,个人以原子化的面貌出现在劳动市场中,而这个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嵌套仅有一副单调的“消费”面孔,人们——尤其是底层人群——不得不以牺牲个体权利为代价来适应资本,被仓皇卷入“撒旦的机器”。于是我们看到,底层劳动者被迫在感染与失业间做选择,一些中产阶层居家办公,照常领取工资,而富人特权阶层则坐着他们的私人飞机奔向相对安全的私人领地。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哈维等人道破了“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虚伪假象。尽管病毒不会区别对待我们,但资本所塑造的世界中既有的诸多不平等仍在病毒感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谁可以在家工作?谁又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在无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哪些人可以负担起隔离期间的费用?哪些人购买了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这些都是巴特勒所说的“悬殊的不平等”的铁证。正如哈维指出的那样,疫情中被置于危险“前线”的人群是高度性别化、种族化以及族裔化的。例如在美国,照顾感染病人的护士通常是女性,经济下滑后可能遭到解雇的首先是非裔、拉美裔人士和妇女。

此外,美国城市理论学者迈克·戴维斯在《雅各宾》上发表的文章《在瘟疫年》(本文由澎湃新闻编译发布)警示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据研究表明,60%死于1918大流感的人口居住在旁遮普、孟买和印度西部其他地区,食物短缺造成的营养不良,遍布贫民窟的细菌造成的高感染率和重症病发率,使得该地区成为病毒肆虐的重灾区。戴维斯认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致命的悲剧很有可能在当今非洲和南亚的贫民窟和重演。“我们与你同在”之类的口号永远不可能弥合地区之间的鸿沟,相反,它透露出一种虚伪。
旧的世界似乎正在瓦解,新的秩序还未形成。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捕捉到了当下这个动荡时刻的幽暗与不安。在他看来,“传染”的概念使每个人都成为了潜在的危险分子,播撒猜忌的种子,人们愿意为了“安全理性”而牺牲人际关系、工作、自由以及信仰,除了“赤裸生命”之外,我们的社会“别无所有”,团结被切割开来,“邻人不复存在”。
齐泽克所说的“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与阿甘本的“安全理性”陷阱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对“为求活命而不择手段的无情措施”保持高度警惕。不过,齐泽克批评道,原有社会关系的连接方式被打破没有造成价值幻灭、令人彻底绝望的景象,人们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基于“互相尊重”的新型团结方式,并不全然出于对自我“赤裸生命”的保护。旧世界崩塌的同时,新的规则也在诞生,事情远比它看上去的那样更朦胧。
同时,齐泽克也将“潜在危险分子”的问题引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角度。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对个体不当行为的指责,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有意或无意的“危险分子”,当下这种强调个人责任的做法实际上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以致于我们专注于谴责个体而忽视了“如何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大问题。
对新秩序的呼吁成为西方思想界在探讨病毒问题时的一个主题。在旧世界,思想家们从阶层、地域、种族、性别的不平等中看到资本对医疗卫生,也即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严格控制,由金钱和一系列社会身份组成的21世纪“适者生存”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出了“可哀悼的生命和不可哀悼的生命”,从“不值得保护免于疾病和死亡的人”中筛选“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免于死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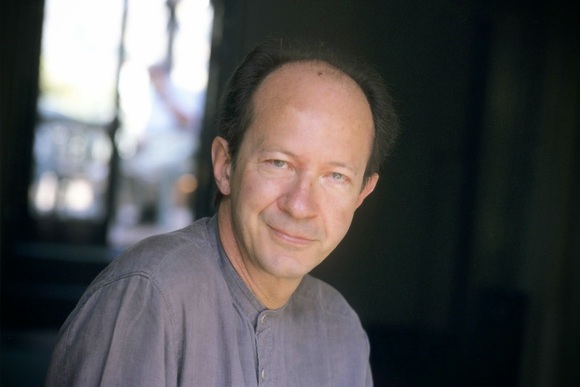
有趣的是,不论思想家们具体持怎样的态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都频繁地出现在他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哈维在谈消费主义资本经济危机时说道:“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出资刺激大量的消费,这或许需要对美国的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化’,而不称其为‘社会主义’。”齐泽克同样表示,一旦身陷危机,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连特朗普也不例外。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援引《国防生产法案》,允许政府指导私营产业以应对疫情。就在几周前,齐泽克自己使用“共产主义”一词还遭到嘲笑,而现在“特朗普提议接管私营产业”的标题直接出现在新闻之上,颇具讽刺意味。
与哈维和齐泽克相比,巴特勒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似乎更加明确。作为全民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for All)的支持者,巴特勒认为,全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的主张在美国“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我们必须等待这一想象在这个国家成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承诺”。在她描绘的“激进平等”世界里,不论经济能力如何,任何人都应当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生活所需物质。而这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与致力于国民医疗保健的其他国家一道,建立起跨国团结,实现国际性的平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