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需要我们更审慎地制定规则,落实计划,甚至改变城市规划的现有方案。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无论是2003年非典疫情还是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食用野生动物都被普遍认为是新型传染病爆发的罪魁祸首,随着近些年野生动物保护观念的提升,民众对取缔野味消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日前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出台,被认为是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该《决定》规定,不仅在野外生活的野生动物不可食用,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也不可食用(鱼类等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围)。《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它在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首次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让取缔野味市场获得了法律依据。
然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认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只是开始,许多问题仍亟待厘清,此次水生野生动物未列入禁食范围,就是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复杂性的一个证明。
王放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任美国美国史密森学会博士后,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野生动物种群动态、种间关系和适应性等。王放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科普教育、政府沟通和推动政策落地的工作。从2019年12月起,包括他在内的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发起了“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公众在上海参与以貉为代表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工作。在他看来,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正在出现从保护个体物种到维护整体生态系统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政策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民众对野生动物及生态系统的认识也有待提高。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更是有落入对野生动物过度恐慌防范的危险。
日前,王放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指出,野生动物的存续事关生态系统的平衡,也事关我们每个人——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如何与它们共生共存,需要我们更审慎地制定规则、落实计划,甚至改变城市规划的现有方案。在他看来,如果仅仅因为眼下的疫情而提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长远来看生态安全就依然还不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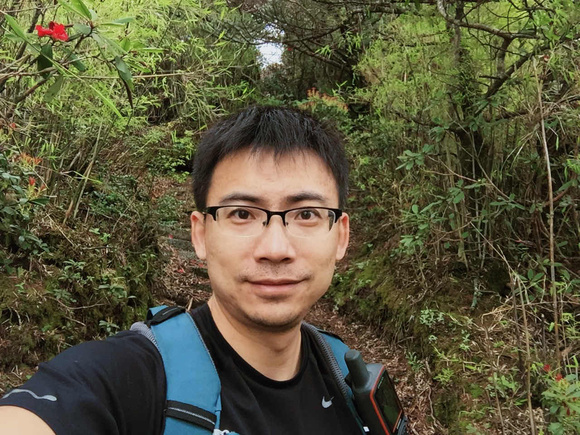
界面文化:中国人爱吃野味是否是新型传染病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虽然新冠肺炎的原始传播路径目前还未明确,但有不少人相信是有人食用蝙蝠导致的,网络上还出现了一种批评:“如果蝙蝠真的能吃,老祖宗早就把它驯化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王放:首先,我认为中国人特别爱吃野味这个概念并不是真正成立的。实际上,整个人类发展演化史中野生动物都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食物来源,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存在“吃野味”。一两百年前,欧洲人照样是在打野生动物,美国人也是什么动物都吃,当然主要白尾鹿这些动物。不管是印第安人、因纽特人还是澳大利亚人,大家都在吃。但确实是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其他地方的人慢慢地对食用动物有了越来越严格的定义,但我们国家好像一直没有跟上。
其次,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两三百年,当时的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消耗量远没有今天那么大。那个时候没有枪、钢丝套、电网和毒药这些现代化的打猎方式,所以历史上我们对野生动物的消耗数量有限,影响范围局限在居民点周边的有限区域,这也是为什么100年前中国的野生动物分布不会像今天这样那么稀少。并不是在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上人们整天吃野生动物、用熊胆和穿山甲入药,这些其实都不存在。
广东人吃野生动物,或者我们看到的武汉也有野生动物市场,这种大规模商用都是最近几十年伴随着枪、钢丝套、电网还有快速运输才大规模产生的。我觉得我们对野味确实有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但这个食用量其实是最近几十年才激增的。这是我对这件事本身的一个澄清或者说重新定义。
吃野味带来的影响确实比一般人感受到的要深得多。一般人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吃了一块肉,但从野生动物在山上活动到我们吃到这块肉的链条是非常长的。你需要漫山遍野放套子打猎,之后去山上捡回来宰杀,然后需要运输,在运输过程中有些活体捕捉的动物会产生尿液、粪便和各种各样的空气和水污染,然后市场里几十种动物关在一块,又有交叉感染,这些地点就好像一个病毒细菌培养场一样,病毒大量传播、突变和复制,最后还有后厨的宰杀。所以吃野味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事,但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几十人、几百公里的运输,影响的面积可能是几百、上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其他环节带来的影响要比食客吃的过程复杂深远得多。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文化习惯对野生动物的摧毁性作用,比如穿山甲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
王放:不管是虎骨入药、穿山甲入药还是熊胆入药,这些都是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才大规模商业化的。以前这些都是很小众的偏方,是只有极少的人才能用重金尝试的,它们从来不是中药的主流,也从来不是老百姓用药的主流。

在现代科学看来,穿山甲的甲片所含有的成分就是β角蛋白,和我们的指甲成分相同。所谓穿山甲可以穿山,所以就可以疏通我们的乳腺和呼吸道,甚至可以治疗肿瘤这样的传说,我认为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被抛弃。但一个巨大的危险是,在人们转变观念之前,野生穿山甲就已经灭绝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通过法律来严格禁止。
界面文化:我们要如何确立可食用肉类的安全标准呢?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只允许食用养殖动物是否可行呢?
王放:《中国畜禽资源遗传目录》规定了可以作为食用资源的猪、马、牛、羊、鹅、鸡,也包括了梅花鹿这样的特种食用肉类和貉这样的皮毛用动物,所以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清单的。它其实可以作为白名单来使用——在这个名单上的动物就是可以吃的。但在以前,确实没有一个完整的法规来规定什么动物能吃,什么动物不能吃。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清单,这个清单上好像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动物;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说除了这个清单以外的动物都不能吃,我们没有说出来这句话。
界面文化:所以就有一种“无法可依”的局面?
王放:这个话比较重,我觉得至少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没有法?是有法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或者畜牧业的法,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一块的,但每部法好像都有些漏洞。所以我觉得说“法律不完善”“法律存在空缺”是成立的。
界面文化:此次疫情期间,我们了解到蝙蝠可能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天然宿主,这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非典期间人们对果子狸的防范与恐慌。在这17年间,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出现了什么变化吗?
王放:我觉得还是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跟全球对生态系统认识的变化有关。最早中国开展系统性的科研保护工作是在1980年前后,当时我们关注的就是大熊猫、金丝猴、白鳍豚这几种动物。一方面,人们觉得濒危物种涉及国家形象,我们需要把这些物种保护下来。另一方面,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整体感受还是它是一种资源,我们在做资源管理。所以那时我们给保护动物取的名字,除了重点保护动物之外,其他的保护动物叫作“有科研、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动物”(简称“三有动物”),这种对野生动物的认识还是以人类判断的价值为导向的。
但最近17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把国土划出了一个又一个保护红线和生态主体功能区划,试图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区、保护重要的森林功能区。我们还把目光从一个个物种转向了生态系统:我们在看生态系统的平衡,在看生态系统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水资源、维持农业生产有什么重要作用。我觉得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关注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了。
但从公众层面来讲,我倒不觉得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讲,野生动物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存在,有些可爱,有些吓人,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真正直接的关系。感兴趣的人会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人还是觉得特别遥远。可能除了这次疫情之外,大部分人平常并不会觉得野生动物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界面文化: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表示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将增加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内容。你提出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三有动物”的界定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当下的情况。为什么“三有动物”一度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有促进作用,但现在却不合时宜了?
王放: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之所以说“三有动物”的名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因为最早我们只关注这些濒危的珍惜动物,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等。后来人们发现有很多动物虽然没有那么濒危珍惜,但也是重要的。“三有动物名录”出现后,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动物,比如说麂子、野猪、松鼠等等以前大家觉得可以随便去搞的动物都被保护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起到了特别积极的作用。
之所以说今天不适用,是因为中国的“重点保护动物名单”在2003年更新至今已经17年了,“三有动物名单”则从诞生至今从来没有更新过。所以这个名单首先非常陈旧,很多动物发生了变化,但名单没有得到更新。其次,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也在改变。最早我们觉得一种动物是濒危的,需要保护;后来觉得有价值的动物需要保护;今天我们觉得需要保护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需要达到平衡,需要维护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讲,绝大部分,或者说每一种野生动物对于维护生态系统都是有用的。所以这时我们单划出一部分野生动物有价值、一部分没价值,就显得和法规的核心目的相抵触。
比如说“三有动物名单”,超过1000种动物是不在这个名单里的,但它们中很多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很重要。蝙蝠这个类群是哺乳动物的第二大类群,它对害虫的控制、对植物的传粉、对农作物的生长都有完全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编制重点保护动物和“三有动物”名单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一类群,而这个缺失是巨大的。再比如说旱獭和鼠兔也都不在“保护名单”和“三有名单”里,不管我们是去摸、去吃还是去毒杀,都是没有法律依据提供保护的。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觉得“三有动物”可能到了结束历史使命的时候,该让位于一个全面保护的阶段了。
日前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阶段意见,鉴于立法过程比较长,先迅速通过一个决定,规定几件特别简单的事,虽然现在没有立法,但大家全都照着办,具有法律效用。这八条规定中,直接规定了全面禁止食用保护动物、“三有动物”以及一般野生动物。这个决定直接放弃了“三有动物”的概念——在吃动物这件事上,以前我们说保护动物和“三有动物”不能吃,现在说保护动物、“三有动物”以及一般动物不能吃,所以在吃这件事上已经放弃“三有动物”的概念了,只要是野生动物就不能吃。

界面文化: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提出《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九个意见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那些可以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则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你之前对此表示反对。
王放:他们后来澄清说是措辞不当,他们想的还是虫害防治这些事,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用词错误。“生态灭杀”这个词还是一些地方法学教授的修法建议,这个其实不太能代表官方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修法过程中一个积极的社会讨论。
界面文化:就目前来看,法律法规层面和学界的认知层面已经出现了时间差。在你看来,未来法律政策的制定能追赶上学界的共识吗?
王放:我觉得有希望。大家认识到了修法不是一个只看当下的事情,而是一个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生态安全的事。所以不管是最近全国人大、习总书记的讲话,还是民间团体、大学或修法建议,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一致的倾向,就是大家在谈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在谈一个长远的事情。如果能够把目光放长远的话,多个物种的保护、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全面保护都会被提上日程。但如果我们只看眼下的疫情,只是增加一些不吃野生动物的规定,那这件事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但现在看来大家还是着眼于更长远的生态安全,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吧。
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水生和陆生动物之间尚存在割裂。昨天人大的八条决定里提到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其实指的是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我理解一旦加入水生动物就会有很多偏差,比如说大家要抓鱼、抓螃蟹、抓虾吃,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也确实是——捕捉常见物种就是天经地义的。但还有大量水生生物的濒危程度超过陆生生物,所以水生生物如何立法保护就变得很困难,全面保护水生生物看起来就是不现实的。
再比如说你提到的养殖动物。有些动物是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里的,比如说梅花鹿的特种养殖、乌苏里貉(一种皮毛兽)的特种养殖,但还有一些动物就不在这个清单里,比如说竹鼠。大家都知道“华农兄弟”,以他们为代表的竹鼠养殖户要怎么办?竹鼠不在畜牧业的清单里,同时竹鼠也是“三有动物”,所以按照现行的严格规定,好像竹鼠养殖行业就会死掉。处于同样情况的还有豪猪、大鲵,这些动物已经有相对成熟的养殖技术,也有了人工种群,但它们好像突然变成了不能食用的动物。这些养殖场接下来该如何存在,现在看起来还非常未知,是全部倒闭呢,还是尽快修改畜牧业的白名单?大家还在观望。
还有如何定义野生动物。养殖场里被活熊取胆的那些动物,是不是也是野生动物?我认为是,但养殖场的人可能就认为不是。这些如何定义,都是有很大的认识空缺的。可能需要各行各业坐在一起非常认真、诚恳、激烈地讨论才能得到共识。
界面文化:“保护野生动物”,乃至“野生动物”本身是不是大规模城市化后才出现的现代概念?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王放:从现代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在欧美,人们确实经历了一个荒野大开发,工业革命后征服森林和草原的过程。大约在100年前,美国出现了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作者)这样的自然启蒙先锋人物,他们呼吁人去体会自然的美好,观察野生动物,感受野生动物的美,所以美国一大批国家公园是在1920-1930年建立的。这是人们已经体会到了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威力之后,才重新发现野生动物的美好,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国家这个过程稍微晚一点。中国在1960年代建立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开始保护野生动物。最初的自然保护区保护的目标就是大熊猫。但这个过程出现了变化,人们开始欣赏野生动物,开始觉得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但这个变化够吗?我觉得还不太够,不同国家可能局面非常不同。
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年,我觉得野生动物对那个国家的人来讲是生活里特别正常的一部分。每个人的院子里都会有松鼠,大部分人家周围都会有白尾鹿。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鹗的鸟巢,鹗是一种会抓鱼吃的大型猛禽。我特别吃惊的是,我旁边一个美国家庭里四五岁的小孩看到鹗的时候都会大叫“Osprey! Osprey!”我就想,如果是在我们国家,大家看到会说“大鸟”“老鹰”,但美国小朋友会对这个东西定种,好像动物是他们从小到大生活中的一部分。
界面文化:你在公众号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既不是完全美好,也不是全然糟糕。请与我们的读者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王放: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之一,而且它会一直存在。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城市生物多样性,其实城市之所以形成,就是人和野生动物被这个地方的水土所吸引,都往这个地方聚集的过程。以北京为例,北边是燕山,西边是太行山,有潮白河,有海河流域,有冲积平原,所以这么一个区域千百年来就是最重要的鸟类栖息地和迁徙地,也在100多万年前开始有不同的原始人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不管是直立人还是智人。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是如此。成都一边靠着山一边是平原;南京有丘陵,有河湖网络。所有城市的形成过程都是动物和人的共同选择,我们并没有比这些动物来得早,也没有比这些动物来得晚。所以生物多样性从来没有消失过,就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发展的。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一定会有很多好和不好的地方。没有生物多样性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粮食,没有这么多的蔬菜,比如我们在江浙一带吃到的荠菜、青菜、各种油菜,都是我们国家植物生物多样性的结果。
城市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区域一定是害虫比较少、蚊虫传染病比较少的区域。所以整体来讲,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会一直存在,另一方面比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安全和稳定的。但是生物多样性的确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城市爆发狂犬病,那刺猬、貉或者松鼠身上都有可能带病毒。如果我们的城市生态越来越好,松鼠会越来越多,松鼠多了就会去破坏小区,就会去偷猫粮狗粮、啃我们的轮胎、传播传染病。这样的例子其实在这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其他国家城市里一直都存在的。大家慢慢会接受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界面文化:人类该如何界定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呢?我们的行动应该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王放:我们肯定要采取主动行动,但行动的模式是不同的。特别简单地说分两种:第一种是在荒野之中。荒野之中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保护区,建立国家公园,留出自然保护地,因为荒野之中的土地可能主要还是为野生动物、水土保持、森林维护而设立的。荒野之中我们人要少做一点事情,把土地还给野生动物和自然,相对来讲会被动一点。
但在城市里和城市周边,这些土地是为人类的使用而规划的,所以城市里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更主动。比如说城市里规划出大量的人类用地之后,我们主动规划一些城市绿岛,专门为城市动物建立一些监测和法规,做一些特殊的城市规划,比如说怎么建绿地,怎么选择绿地里的植物,怎么铺设河道,怎么通过技术方案来维持城市基本的生物多样性。所以其实对城市的维持更多是从城市景观的角度——人在城市里活着不可能没有树,不可能没有草,不可能没有水,如果没有的话人会特别焦虑。
但在建设城市生态景观的时候我们捎带考虑一下城市生物多样性,剩下的内容交给动物自己来适应,可能这个是我们对城市动物的管理方案。我们建一个对人更好的生态城市,具体动物怎么办,交给它们自己来适应,同时我们坚持去监测,去调查这些动物的状况。毕竟城市动物很少有保护动物,也很少有传统来讲特别珍贵濒危的动物,更多是一些比较皮实的、生态位比较宽的物种。
界面文化:在经历疫情后,很多人对动物的心态已经出现了改变。我们需要警惕哪些行为和心态?
王放:我觉得最大的警惕就是恐慌以及极端化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大家知道了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我们就去把蝙蝠赶走或者杀掉。甚至我们到了谈野生动物色变的程度,在城市里投毒杀掉黄鼠狼和刺猬,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危险来自于,其实这些野生动物一直都存在,而且它们在尽一切可能减少跟人的冲突。当我们制造冲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杀不干净,另外一方面在冲突之中我们会引起非常非常多的危险。不管是正面冲突增加传染病的扩散,还是我们在环境里投毒带来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反正每一种我们都要花十倍百倍的损失去弥补。
界面文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人类是否不应该介入任何一种生物的灭杀?
王放: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去管理很多生物,最典型的例子是入侵物种。巴西龟从国外到了中国的水域;罗非鱼遍布整个珠江流域;紫茎泽兰、飞机草这些植物漫山遍野都是,我们需要干掉这些入侵物种。然后比如说有鼠疫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对疫区的鼠患进行控制的。再比如说城市里如果机场周围的鸟类过多,我们会驱赶,可能也会涉及局部的扑杀。还有农田的虫害、蝗灾等等,很多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控制野生动物的。

界面文化:关于入侵物种,这两年网络上有不少“中国吃货”的段子,说我们可以去吃掉丹麦生蚝、美国亚洲鲤鱼。这有可行性吗?
王放:很难。我们国家这么多入侵物种,我们也没把这些动物吃掉呀。福寿螺、小龙虾,我们是吃的,它们是我们国家危害最大的入侵物种之一,但是我们也没去把这些入侵物种生态灭杀掉。因为去野外抓的话又费时间又费精力成本,所以合理的市场机制就是建立养殖场养殖小龙虾,又肥又美,产量又高。真正野外逃逸的动物我们还是让它们逃逸。我们吃那么多烤罗非鱼,但我们吃的还是养殖场的。整个南方流域里罗非鱼吃掉了我们本土的小鱼小虾,造成了本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但是还是没法抓捕干净。所以“吃货治理”只是大家的一个开玩笑,千万别当成是一个真的治理方式。
界面文化:那中国现在在应对入侵物种的时候有哪些具体措施?
王放:主要是捕杀,但其实还是不成功的。我们在全力控制大量入侵物种,但只是处在不过度泛滥的状态。比如说我们控制得比较多的水葫芦、飞机草,上海的互花米草遍布整个崇明东滩,本土的水鸟、植物都无法生长了。大家还是处于探索阶段吧,在探索不同的方法勉强遏制,每年都需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一旦有一两年不工作,就会泛滥。入侵物种的控制是个全球难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管理方法。
界面文化:目前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变暖,这对生物多样性是很大的威胁,很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身为保护生物学学者,你对此有哪些思考?
王放:以前人们忽视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复杂影响,科学界也是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而很多公众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全球变暖是不是发达国家的谎言”的状态。但是今天人们发现,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太深远了。比如说全球变暖带来的暖冬会让瘟疫爆发——不管是这次的新型肺炎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些传染病,如果全球不变暖,如果冬天更寒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如果冬天更寒冷的话,可能越冬的蝗虫会死掉,就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蝗灾。
比如最近的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最大的影响不是变暖了几度,而是极端气候的增加。极端气候的增加会带来夏天持续的高温,这样在欧洲可能就会有很多人生病或死亡。极端气候还会带来很多奇怪的现象,全球变暖导致气流和洋流的变化,直接影响是飞机变得更颠簸了,忽上忽下的感觉更强烈了。所以气候变暖真的不仅仅是气温上下改变的事,而是全方位的影响,更多的影响其实在未来才会更多地观察到。简单来说,它的波及面要超过十年前科研界的认识很多很多,它是影响我们每一天的衣食住行的。
界面文化:你目前正在参与“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组织公民科学家团队在上海对城市野生动物进行调查。请与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项目的最新发现?
王放:我们有三个很震惊的发现:第一,每个人都知道“一丘之貉”这个成语,但貉长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甚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种动物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上海超过60个小区都有貉出没,在市中心里也有,它在南京、苏州、杭州、无锡等地都存在,分布非常广泛。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第三,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貉的系统研究。我们仅有的研究是养殖场里怎么取貉毛,怎么给貉看病喂抗生素,但是貉在自然环境下如何生活、和人如何互动、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有传染病,完全没有研究。
所以公众没有认识,但它分布又非常广,随时随地在跟人产生接触,而我们又对它完全没有研究,这三件事是我们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太快,我们已经丧失了对野生动物的概念,甚至千百年以来老祖宗们形成的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文化习惯都已经没有了。
王放:是的。我觉得大家对野生动物的疏离感,一部分原因也是真的认识不到野生动物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种感觉太远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关系是特别切实存在的。比如成都、绵阳这样的城市会面临水患和极端气候威胁,如何去应对这种潜在的洪涝灾害呢?最大的应对方案就是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它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大熊猫的栖息地,大熊猫生活的地方和成都只有车程几小时的距离。
我们说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是真的去把野生动物抓起来,给它们喂食物,或者一只一只地关心它们。大家做的就是保护这些森林水源,这些森林水源同时也是在保障中下游的农业生产,是在保证人们不受灾。如果没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话,可能很多江河上游的森林被砍伐,最后出现的是夏天的极端天气,让更多人中暑,让河水变得浑浊,让农产品减产。这个纽带是特别近的,但是如何让人感受到?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界面文化:你在一个TED演讲中介绍过你在参与四川大熊猫保护工作期间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要重视人在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实现人与动物的共生互赢。我相信这一原则在城市野生动物的管理保护中同样适用,但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你对此有哪些观察结论?
王放:你说的对。在荒野里事情会容易一些,每一个保护区都有社区科,每个保护区恨不得有1/3到1/2的工作是跟社区搞好关系,帮助社区发展生产,给他们带来清洁能源。如果是周边的社区居民高兴了,能够通过更好的方法赚到钱,动物就能被保护下来,大家都高兴。这已经被摸索出来是一种特别成熟的模式了。但是在野外这种利益分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保护区和社区:保护区管理着国有土地,社区是私有和集体土地。城市里有工厂、单位、社区,还有交通用地、农业用地、生产用地、商业用地等等,非常复杂。城市动物变化也很快。以我们实地工作的经验来说,城市里就是有人不喜欢野生动物,他们的一些要求也有合理性,比如会认为野生动物产生噪音、粪便污染草坪等等。
怎么解决呢?一方面我们在跟城市管理部门合作,希望还是有一些法规作为底线。不管城市的人想法多么复杂,不能违法,比如你不能自己去投毒,不能去下套子。另一方面我觉得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我们以及其他机构在做一些科普宣传,比如说野生动物直接给人带来传染病的几率是非常低的,野生动物的存在是有可能不干扰人的,比如蝙蝠这样的物种。
但可能更重要的方面是,既然城市人的想法那么复杂,我们需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做更多的努力。比如说如果一片绿地和居民楼之间无遮无掩的话,确实刺猬、黄鼠狼与貉跟居民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多,居民会看到、会害怕,这些动物也没有地方藏身,它们也在紧张之中。如果我们的垃圾没有更好地保护起来,它们会去翻垃圾堆,带来污染和冲突,也增加了患病的可能。所以可能我们需要设计更好的城市景观,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些灌丛,让动物能藏起来,减少和人的直接冲突;如果我们的垃圾桶都是带盖子的,每天定时去回收,就能减少动物去翻垃圾堆的几率;如果我们检疫部门能定期检测野生动物的疾病,我们就能告知居民它们是否带病,并进行处理。可能还是要通过城市设计来解决,但这确实很复杂。

界面文化:你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进入城市后展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否也需要去适应野生动物?
王放:野生动物的适应性和适应速度经常超过人的想象。比如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浣熊的智力就显著提升了,城市里的浣熊获得了3D导航的能力和更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它们会去识别交通,它们的导航系统从平面的变成了立体的,还能识别不同的城市建筑物。
中国也一样。以上海的貉为例,貉在野外是一种山地动物,是一种生活在丘陵地带岩洞里的动物。但是随着上海的发展,它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原物种,然后又变成了一个把栖息地从山洞挪到了废弃下水道、通风口的动物。它吃的食物从山间溪流里的螃蟹、小虾变成了城市里各种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城市里的垃圾、人们喂的猫粮、城市草地里的昆虫,甚至城市里的小鸟、老鼠等等,它们还会去偷吃养鸡场的鸡鸭,冬天还增加了很多淀粉食物——它们吃大量的草根来补充淀粉。所以这种适应性是特别惊人的。
城市里的黄鼠狼主要活动时间从白天变成了夜晚,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它们的攻击性在不断降低。攻击性降低的过程就是它们对人类活动的适应过程。可能在自然条件下,人进入它们繁殖巢周围,进入它们的栖息地,它们会驱赶和示威恐吓的行为,但在城市环境里它们就忍了。
其实城市里的人一直在适应野生动物。我们去上海一些小区探访,很多小区的居民都知道貉的存在。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貉,他们管这个东西叫“獾子”。但是他们也知道你不去招惹它,它就不会来招惹你,所以大量居民其实是容忍的。野生动物的主动适应也是在促成居民的容忍——它们在尽一切可能减少跟人打照面的可能,也在尽一切可能减少跟人的直接冲突,这个过程就让人去适应它们也变得容易了一点。如果真的是野外的动物,还是有一点凶的。包括上海的狗獾,在野外是一种很凶的动物,如果直接接触的话,它会恐吓人、撵人,但在城市里就变成了一种相对温和的动物。前一段时间上海本地新闻吵得很凶:奉贤有一所国际学校,因为十几只狗獾在那里,不得开工。因为狗獾是上海市的保护动物,它也是一种以前生活在荒野、但今天城市里也存在的动物。
界面文化:“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会持续多久?最后会形成怎样的结论或怎样的结果呢?
王放:只要我们团队还在上海,我们就会把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这件事做下去。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是一个完全没有终点的事情,它的管理是不存在一个终极、完美状态的,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今天有一个传染病,明天可能这个物种突然就爆发式增长了,后天气候变暖,一大堆城市动物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相应来讲,我们的监测和管理也永远不能停止,解决方案是在不断调整当中的。
几乎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都面临这个情况。比如纽约周围的浣熊、白尾鹿、负鼠的监测是从将近100年前开始的。在柏林、巴塞罗那这些地方,从20年前人们就开始关注野猪,但是不管多么关注,野猪的问题还是持续存在。每年人们都提出新的方案,探索新的尝试。
中国城市也一样。不管是北京建设奥林匹克公园,建一个个城市绿地,还是上海的环城绿带或其他城市的生态建设,城市生态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过程中城市动物的变化速度和方向都是难以预测的。有些动物会更多,有些动物会更少,所以只要我们团队还在上海,这个工作就永远不会停止。它可能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是在正常的科研工作完成之后,利用周末、晚上或者节假日的时间去做城市生态调查。
界面文化: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才刚起步?我现在很难想象中国的城市规划里会有这么一个模块说我们要去关注城市的野生动物,要关注城市的生态构建。
王放: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城市动物研究是有的,但数量很少。大家更多还是从传统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件事,比如说杭州有多少种鸟,上海有多少种青蛙、多少种蛇。
现在的研究还是缺乏把眼光放到整个城市化进程上。如果城市化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比如长三角一体化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那在一体化的过程中整个长三角的生态系统会怎么变?它怎么影响人?有没有生态安全的问题?这样的长期、大尺度的工作几乎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