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明星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携新作《资本与意识形态》回归,他在书中主张不平等的根源来自意识形态。

托马斯·皮凯蒂在法国经济部参与研讨会 图片来源:Eric Piermont/AFP/Getty Images
新闻出版界早已形成这样一个传统:任何书名带有“资本”二字的作者一定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而著作能卖出成千上万册的经济学家就是“摇滚巨星”。托马斯·皮凯蒂凭着长达600多页、销量高达数百万本的巨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赢得了这两项殊荣,可实际上,他本人跟这些毫不相关。皮凯蒂着眼于自由派改革家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他口中“资本”概念更接近于一种账户分类(“财富”的代称词),而非马克思所指的剥削力量。
和温和叛乱派雅尼斯·瓦鲁法克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怪诞经济学不同,皮凯蒂不管在舞台上还是文字里都显得谨慎又无聊。他痴迷于数据,尤其是百分位数。他不仅千方百计地从各种不太可能的地方挖掘数据,比如18世纪纳税记录和伯克贵族群体,还对一手数据的收集机制深感兴趣。
当长达1000页的《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一书出版时,天花乱坠的宣传再次袭来。右翼出版社为该书“90%的遗产税”的建议激动不已。《资本与意识形态》9月在法国面世时,专栏作家马修·莱恩通过《电讯报》表示,“托马斯·皮凯蒂回来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危险。”或许是皮凯蒂温和文雅的态度令人仓皇失措,又或许是因为他所指出的,美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1950至1970年代,恰好与遗产税最高将近80%、收入税甚至更高过于此的时期相重合。
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相比,《资本与意识形态》恐怕更具野心。前者重点关注过去200年里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趋势,而后者则是一部几乎涵盖一切的历史典籍。从年代跨度而言,该书以封建制度及前现代时期经济宏观综述起步,以“黄马甲”导致的困境结尾;从地理范围而言,该书着眼全球,在对欧洲、美国的分析之上又加上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金砖四国)。此外,他还详细论及奴隶制和殖民主义。

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承担起如此大规模历史使命的作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奸诈政客。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整套关于历史变迁的清晰理论,能将大量证据编织起来。正如《共产党宣言》著名的开篇所言:“迄今为止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国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便一直致力于探寻几个世纪以来在形成中的历史模型。
关键点在于,若要试图找到串联起这些历史线索,就需仰仗于某种理论。但皮凯蒂极少用到宏观理论,这恰好是他一直以来的魅力所在,并且毫无疑问地强化了他面向大众市场的吸引力。迄今为止他所谈到最接近历史原理的是公式R>G(投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他曾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引用该理论解释为何财富比收益增长更快,以及为何随着时间推移不平等性更为明显。即便如此,他也坚持认为这只是针对现有数据的观察,而不应被理解为普遍适用的“法则”。皮凯蒂为我们呈现出的历史似乎并无“马达”,之所以出现收益和财富的系列变化,只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希望和被允许这么做。
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的假定颇为道德:不平等是不合法的,因此需要意识形态来做出调整和克制。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历史均证明,在任何时期、所有文明当中,寻找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财富分配方法是永恒主题。”社会对收益、财富和教育分配得越为广泛,就能获得越为繁荣的发展。因此,推翻后退的意识形态是实现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
随着时间推移,突出自由民主的情感支撑也暗藏风险,因为各年龄层都已受到温和的皮凯蒂精神的刺激。它提倡运行良好的公共领域应根据理论充分的论据和佐证来决定财富分配,而非根据统治和机会主义。经济历史学家可能会有所回避,但强制人们去直面所有经济模型里的公平(以及不公平),一定能够带来某些红利。
皮凯蒂在书中用了大篇笔墨来描述过去千年中占据主导的“不平等政权”。“三元社会”(比如封建主义)被划分为牧师、军队和工人阶级;起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成为主流的“所有权社会”,使收益和财富集中到地主家庭和新资产阶级群体手中;“奴隶社会”则提供了最极端的不平等模型(约1780年代的海地是有史以来最不平等的社会)。“殖民社会”则是军队力量、中产阶级所有制和奴隶制的结合体。
即便有时会导致难以避免的过于宽泛,皮凯蒂坚持提倡将视野放大到自由西方之外,并直面其中最糟糕的历史罪行的主张依然令人敬仰。 但欧洲,尤其是法国,还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对于皮凯蒂而言,这并非因为黑格尔信仰在欧洲的独特地位,而是因为大量数据存在于此,就像醉汉在街灯下找钥匙一样。这就是说,《资本与意识形态》对欧洲的政策辩论起到了介入调停作用,更提醒法国当局:法国大革命不只是为自由与博爱而战。

这本解读自由西方社会内部“不平等政体”的书,部分内容重温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观点。尽管法国大革命公开声称平等主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财富和收益的不平等依然是贯穿19世纪的主题。战争和日益激进的课税政策致使不平等问题在20世纪前半叶急剧凸显,也为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民主政体奠定了舞台基础。
战后政体运转的种种迹象表明,高水平边际税率(指在增加一些收入时,增加这部分收入所纳税额同增加收入之间的比例)是合理有效的,但在皮凯蒂看来也有致命的潜在风险:将导致教育领域的极不平等现象。教育不公不仅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皮凯蒂认为比财富分配权更重要),还会加剧(高校)毕业生与非毕业生之间的政治分化,到1990年代,工人阶级在政治选举领域几乎毫无发言权。
他很可能是对的,考虑到气候危机和其他因素,当前的不平等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皮凯蒂对过去40年的解读,与其说是研究了资本释放(多数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这样认为),倒不如说是研究了失去势头的先进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遭遇的挫折引发了一种关于政治传递公平能力的新宿命论。全球主义逐渐侵蚀着国家边界,“超级资本主义”则激发了1914年以来全世界对财富前所未有的的关注。在后社会主义犬儒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富人并不需要任何辩护,对“精英管理社会”也不甚关注。他们在财务手段上的暧昧不明(皮凯蒂称部分手段为“惊人”)意味着其根本不需要公共防御。
这些战后趋势最终导致今日西方政体多被两种竞争阶层所主宰,具体反映在两党选举制度上:支持开放市场的金融精英,和代表文化多元的教育精英。但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作为社会公平基石的累进税制的信任。在这些民主政治基本选择项的支撑下,本土主义者政党迅速繁荣发展起来,并站到了教育、经济不平等的对立面,但其存在的基础前提则是更为收紧的国家边界。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愿意同时保护国际主义和重新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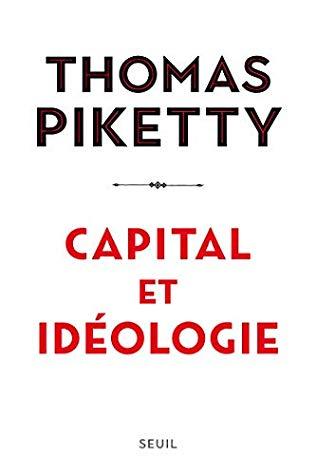
皮凯蒂最后给出了力求应对本土主义者挑战的试验性策略提案。包括一些颇为大胆的想法(比如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基于个人选择的教育预算),但大部分想法都止步于参与式管理、进步性课税、欧盟民主化和收入保障等数十年来激进自由主义派反复提及的思路。显然,提出政策比落地执行要简单得多。考虑到气候危机和其他因素,当前的不平等必然无法长期维持,新政策亟待提出。基于“不平等政体向来无法长期持续”的假设,皮凯蒂更愿意采取相对积极的视角。尽管在《电讯报》上的言论很吸引人,皮凯蒂“参与式社会主义原理”也并非全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
《资本和意识形态》是一场着眼于社会科学的惊人试验,对简单比较提出了公然反抗。就其野心、强迫性的证词和奇妙性而言,它与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距离比与马克思更近。书中既有关于平等本质的笼统概论,又有如同财政研究院那般强操作性的指导,而且这些文字通常都出自同一段落。有时似乎显得很幼稚,但却颇具挑衅,就好像在说:如果不平等本就没有正当理由,那为何不改变它呢?
什么力量能驱使人们写出这样的书呢?如果说皮凯蒂有一个核心的政治方法论信仰,那便是公共数据极具解放性的力量:当人们掌握了有关社会结构的充足信息,就会坚持追寻更大的公平,直至得到确切保证。在公共领域功能失调引发的分神和愤怒之下,对经验研究启蒙般的信任仿佛来自另一时代。它还必将造就一栋独特的、绝对无法忽略的学术“大厦”。
(翻译:刘欣)